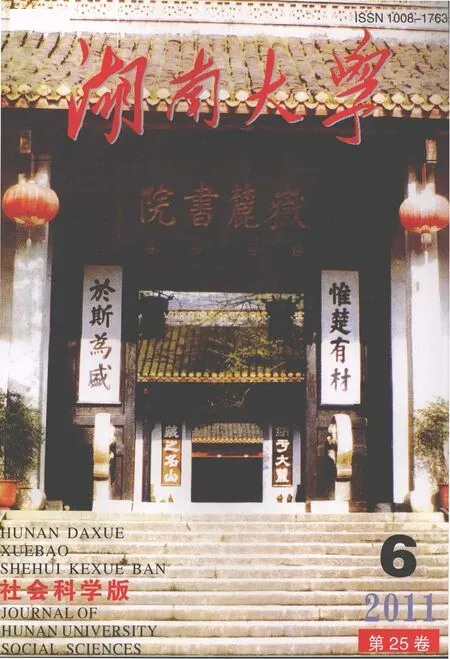苏洵奇崛幽峭的古文风格*
毛德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苏洵奇崛幽峭的古文风格*
毛德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苏洵文风,不仅体现出纵横驰骤的奔放,也体现出奇崛幽峭的深峻。这种奇崛幽峭的特征既表现在文章内在的思想内涵上,又表现在文章外在的语言形式上。在文章创作上追求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的苏洵,不仅为文苦心经营,思致深刻,而且讲求风骨,笔力遒劲,语言上也追求新奇警策,不落凡俗,从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古文艺术风貌。
苏洵;奇崛;幽峭;风格
读苏洵之文,人们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其纵横之风,其实,除了纵横驰骋的文风之外,奇崛幽峭也是其极为显著的特征。王安石谓张籍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此语论苏洵之文亦十分恳切。从生涩险怪,雕琢艰深的时文中脱离出来,苏洵大肆其力于古文,发挥古文的自然洒脱,奇迈挺拔,形成了自己奇崛幽峭的独特文风。茅坤称:“不敢遽谓(苏洵)得古六艺者之遗,然其鑱画之议,幽峭之思,博大之识,奇崛之气,非近代儒生所及。”[1]其奇崛幽峭的文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苦心经营,思致深刻
苏洵文章历来以雄放洒脱见称于世,其在文学主张上也好尚自然。但自然并非随便作文,并不是不讲求文章艺术。自然本身便是艺术风貌的一种,很多时候,它与其他艺术风貌并不矛盾。所以它也并不决然反对对文章的刻画经营。故张谦宜称:“刻苦锤锻之文,与天趣流行之作本非二致,学者其细参之。”[2]而吴德旋也曾谓:“古人文章似不经意,而未落笔之先必经营惨淡,如永叔《与尹师鲁书》,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錬,何以能如此古雅?”[3]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然”也是一种苦心经营的效果。这种情况在苏洵的文章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初读苏洵文章,会感觉其雄奇奔放、洒脱自如,但细细品味,便会感受其中匠心独运,思致深刻。
(一)构思巧妙。苏洵于文章苦心经营首先便体现在其构思的精巧上。如其《上王长安书》,此文乃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入京应试,途次长安时给王拱辰的上书。书之主旨乃是希望得到王长安的礼重。但在苏洵写来,却是丝毫不放倒身价。将一篇本是求重之文写得如此自重,这就要归功于苏洵的苦心经营。文章只在最后用极少的笔墨提及此书缘起,“洵从蜀来,明日将至长安见明公而东。伏惟读其书而察其心,以轻重其礼。幸甚幸甚!”其余篇幅均不及自身,但不及自身却又偏偏处处与自身相关,于此可见苏洵经营构思之巧妙。孙琮谓:“明允本意,只是要王公重士。故前幅先将士贱、士贵,二段立论,见得士之宜重。后幅写士贵之故,由于其徒互相引重。士贱之故,由于其徒互相排挤。究之重士即所以自重。贱士即所以自贱。本意要王公重士,说来若反为王公自重计者。虽占地步语,然却是公平之论。使人读其书,自不得不加以礼,真是识力绝人。”[4]苏洵以此书晓谕王拱辰须当重士,因为重士也是自重。如此一来,则对他苏洵也须礼重自是不言而喻了。主意在于求重,但写来却处处是当重,这样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却又不降低自己的身价。实在是绝妙的构思,绝妙的文字。茅坤云:“运险峭之思以为鑱画之文,故其锋锷不可向迩。”[1]其匠心苦心当与李斯《谏逐客书》相媲美。
(二)寓意深刻。前面我们说过,苏洵的文章多是有用文字,往往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寄意深远,所以发人深省。如《六国论》便是针对宋代厚币以赂契丹之举而发。文章开篇便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然后考究六国之亡乃在于割地赂秦,割地赂秦不但损耗了自己的国力,还连带导致不赂秦者也因此失去外援,无法独全。接下来再从反面用意,不赂秦则六国尚可以不亡,以此反证赂秦之失。最后引古证今:“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强调赂敌政策之不可行,讽谏当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六国覆辙,也就是不要对契丹一味妥协退让,因为赂敌政策无疑是“抱薪救火”,自取灭亡。文章虽然总结六国故事,但用意却在当时宋代的外交政策,可谓用心良苦。过珙云:“前幅推原事秦之弊,后幅为六国筹画一番,归到正旨作结,盖宋是时岁输币以赂契丹。老泉原是借六国以讽宋,读者须玩其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5]
同样深刻寄意的还有其《苏氏族谱亭记》。此是借记族谱亭立说以示训诫。但文章却不仅仅只是简单铭记而已。其意乃是借记谱亭以讽乡之望人,扬善抑恶,训诫族人,教化乡里。过珙云:“此亭记非谱序也,特从老人坐于亭,述其生平之言为法戒,而刻石于亭以记之,始终只是在亭字上生情。妙于起手一段,先以善者兴起,后以恶者惩劝。呜呼!读其文者,修身齐家之念可油然生矣。”[5]可见其意不在一亭一记,也不仅在讽刺乡之望人,而在更深更远的训诫族人,教化乡里。但这种以书事体的形式进行讽喻,感化的方式显然比普通的立言训诫更为有效。所以蒲起龙说:“用书事体,作谱亭记,比于空文垂训者,倍加竦惕。”(蒲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三)
(三)情思婉转。不惟这些用意深刻的文章,即便是那些随笔性的文字,亦可以见到苏洵的无限思致。如其《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此文乃就其二子苏轼苏辙的命名而写意。文章前后87个字,但就是这短短87个字,却将二子命名的深思厚意写得无限宛转。茅坤谓:“字仅百而无限宛转,无限情思。”[1]杨慎称:“字数不多,而婉转折旋,有无限思意,此文字之妙。”(杨慎《三苏文范》)楼昉云:“字数不多而宛转折旋有无限意思,此文字之妙。观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与《木假山记》相出入。”[1]王惟夏曰:“以轼、辙命二子名,一愿其为世不可少,一愿其免于祸。不显、不晦、不任、不让,意固深远矣。而行文婉至,不满百字,足近道德五千言。”[4]老泉是否能逆料二子终身且不说,短短一篇文字中,却能写出无限叮呤,无限反复,将父之慈爱,父之深情写得如此动人,诚非易事。一方面固是真情所至,另一方面也是技巧使然。
二 笔力遒劲,骨格挺拔
八大家中,苏洵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代表,虽然其自称晚学无师,但“取《论语》、《孟子》、《韩非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的修为,使他的散文创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得到了升华。令其古文创作显得笔力遒劲,骨格挺拔。而这种风格特征一方面得益于其地步占得高,另一方面得益于其用笔坚老。
(一)立意高远。虽然终其一生,“爵不过九品”,但苏洵于读书人的节操看得极重,绝不肯为了求仕屈节逢迎权贵。即便是对其极为敬重的欧阳修他都不愿降低身价。他虽然曾向张方平、韩琦、富弼、文彦博、田况、欧阳修、余靖等人上书希望得到引荐,但言辞之间丝毫没有任何卑贱之意。如其《上田枢密书》,此书为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入京后写给当时的枢密副使田况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田况的援引。但文章开篇就反客为主,将自己的上书求荐归结为不肯弃天亵天:
(1)个人追忆法。把过去的自己当成一个分析的对象,追忆以往的情绪情感和行为,去识别当时这个情景自己是如何认知如何反应的,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情感体验,是否合适,应该如何反应更合适。对自己过往的感受加以识别和分析。这需要办公室工作人员养成经常回头看的自我反思的习惯。
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叟不得夺诸舜。发于其心,出于其言,见于其事,确乎其不可易也。圣人不得以与人,父不得夺诸其子,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亵天。弃天,我之罪也;亵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亵,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则弃天、亵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讥。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而为人忧乎哉?孔子、孟轲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与以有为也,我亦知之矣,抑将尽吾心焉耳。
文中之意是说,我之所以上书求知,不为个人私利,只是不肯弃天亵天,尽吾责尽吾心而已,至于用与不用,责不在我。言下之意,责任在不知我,不用我者身上,而不知我,不用我便是逆天而行,将受到天下后世之讥。如此一来,他将本是个人的私事抬到天下之公事的地步,将本是难以启齿的要求说得义正词严,将本需委曲求全的言辞变为轩昂磊落,确为古今求知的奇文。故唐顺之云:“此书本欲求知,却说士当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绝,豪迈不羁。”[1]孙琮则将苏洵的上当事书与韩愈的此类上当事书进行比较,说:“昌黎上当事书,语语悲婉。老泉上当事书,语语气岸。如此文,本欲田公知我,却处处不作求知语,反若田公不得不知老泉者,此是何等地步,何等力量。读之可喜可愕。其地步处,在以天之与我自负;其力量处,在不肯以亵天弃天自居。地步占得高,自不暇作乞怜语;力量见得大,自不肯作求媚态。真是增长人志气文字。”[7]韩愈以儒家正统门人自居,耿介刚直,风骨凛然,但他上当事书尚且写得语语悲婉,而苏洵则没有任何卑谦自怜之意,其间虽有时代环境的原因,但苏洵自矜其贵之意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还不止一处,再比如他的《上余青州书》。上书之意不过是求见一番,目的和《上田枢密书》并无二致。但此番行文,却与《上田枢密书》截然不同。文章极力称赞了余靖的人品功绩,但其意却不在刻意奉承,而在将其与世俗求富贵之人进行对比,通过抬高余靖的人品地位来抬高自己的求见地位。他在文章结尾表明意图时称:“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将自己求见之心表为“不得不见”,则是自己之所以求见,完全是为了结识当世高贤,以慰己心。这样既抬高了对方,又不降低自我,实在是难得的妙文。故孙琮感慨:“青州一书,老泉主意,不过欲求见一番,却先将青州人品,表出在富贵贫贱之外。盖表得青州地位高,则今日自己求见地位亦高。至欲表青州地位,却先将子文抬高于前,又将世俗扫倒于后。盖抬高子文,正是抬高青州,扫倒世俗亦正是抬高青州。究之抬高青州,纯是抬高自己求见地位。行文磊磊落落,气岸不群,真有振衣千仞之势。”[4]
确实,我们从苏洵的文章中深切感受到了他布衣之尊的矜贵,所以嘉祐五年得官后,他上书欧阳修希望其仍以宾主之礼对待自己:“今洵已有名于吏部,执事其将以道取之邪,则洵也犹得以宾客见。不然,其将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此洵所以深自怜也。”(《上欧阳内翰第五书》)而正因为苏洵这种读书人强烈的风节观,使得其为文章必定先占地步。地步占得高,文章自然骨格挺拔,卓然不凡。
(二)用笔坚老。除了立意高迈之外,苏洵文章用笔坚老也是一大特色。苏洵在经历了对时文的扬弃之后,晚年致力于古文创作,所写议论文,摒弃浮华,回归古直,文笔坚挺,老辣苍劲,读后令人振奋不已。故茅坤曾以“鑱画”、“鑱削”进行形容,说:“(苏洵)不敢遽谓得古六艺者之遗,然其镵画之议,幽悄之思,博大之识,奇崛之气,非近代儒生所及。”[1]“苏文定公(苏辙)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1]足见其险劲。这一点从其《六国论》便可以体现出来。
苏洵及其子苏辙均著有《六国论》,但将两者进行比较,各自不同文笔的特点就非常明显。
两篇文章均采取了开宗明义的方式,于首段便提出中心论点。所不同者,苏洵之文一下笔便径奔主题,“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字样,力重千钧;而苏辙之文则表出主题较为婉曲。“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愚读”、“窃怪”、“为之深思远虑”、“以为”、“未尝不怪”等用语令文章论点的提出显得十分深宛曲折。
在接下来的论证中,苏洵先是通过驳论的方式进一步申明中心论点,“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用反驳“六国互丧”说提出“不赂者以赂者丧”的观点对“弊在赂秦”的论点进行佐证。然后具体论述诸侯不惜土地赂秦导致国家败亡的失败之举,其间又通过设问的方式对“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的原因进行辨析,指出其原因在于“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归根结蒂还是在于变相赂秦所致。在将赂秦的弊端表述清楚之后,作者摩空设势,再论不赂秦则可以不亡的事实,应证赂秦亡国的观点。最后笔锋一转,借古讽今,点明主旨“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字数不多,但正反相生,虚实相间,开阖反复,详尽老到,气势纵横。
从这番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苏洵之文虽略少细腻周至,但笔锋老辣,遒劲有力,开阖起伏,顿挫转折间,自有一股高迈奋迅之气,读后令人神飞魄动。
三 发言精警,不落凡俗
苏洵作文,务求“得乎吾心而言”,曾巩说他“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老苏先生哀辞并引》),可见在古文创作上,苏洵是极力追求独抒己见的。尽管这种独特的观点和议论也令他遭受非议,但不落空言,不蹑故迹的创作方针使他为文屡有令人惊奇之论,形成了“幽峭”的文章特色。张谦宜云:“峭,文势之孤立也。如孤峰悬厓,可仰而不可攀。不轻出手,不轻下字,思之思之,刻苦而后得之。或句峭,或字峭,通篇不过一两处,如人面之有鼻,是特高于颊辅者。若满面俱是鼻,便不成人形矣。”又云:“峭字最不易言,闲意莫留他,闲话莫用他,出手要有势,却不要平熟势;脱口要有致,却不要软滑致;掉运须有情,却不要甜俗情,汰除再四,摆弃排奡而忽遇之。”[2]可见“峭”是凝虑苦思,摒弃凡俗的结果,和“幽”一样是独辟蹊径的,所不同的是它还要求有“可仰不可攀”的孤高,要令读者读来印象深刻,而绝不至轻易滑过。
(一)观点新颖。我们读苏洵之文,屡屡为其新奇之论,独到之识所折服。如《易论》:“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礼论》:“圣人以其微权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乐论》:“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书论》:“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诗论》:“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春秋论》:“圣人以其权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惩以劝”。这些观点莫不闪烁着作者思索的光芒。其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再如《管仲论》认为齐国之乱,责在管仲,因为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谏论下》提出以刑劝谏,《史论上》论经史之别,认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二者体各不同却又相互映衬,《史论下》论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作史之失,以为“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晔之史之传,若《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失其人。”“寿之志三国也,纪魏而传吴、蜀。”这些问题都是包含着较大失误的。如此等等,都是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不言,将充满个性的观点充分展现出来,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难怪雷简夫、张方平、欧阳修等人都称赏不已。
再看其结合自身遭际体会所写的《养才》一文则更是令人掩卷沉思,慨叹不已。文中提出对待奇杰之士当用非常之举,不能完全以道德进行勉强。他称“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贵贤贱能。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遗焉。”这不仅是针对宋代现状而发,也是针对整个封建社会用人标准而发,在德才之间,苏洵提出要突出才的重要性,要以非常手段对待这些奇杰之士,这样才能使之更好地为己所用。当然苏洵并不是完全忽视道德,他只是认为可以通过尊宠的方式使之自律而不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令其臣服。认为要效法古之养奇杰的举措:“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放肆而后为乐。”并对当下“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的现状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只会令奇杰之士“越法、逾礼而自快”,即便“绳之以法”、“随之以刑”也不会有好的结果,那样会使他们“北走胡,南走越”,而使朝廷痛失有用之才。结合当时的现状,诚为有识之论。
(二)言辞警策。除了观点新颖独到之外,对言辞的刻苦锤炼,也使苏洵文章的语言表现充满力度,给人以警策之感。如“贫之不如富,贱之不如贵,在野之不如在朝,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知之矣。”(《上张益州书》)“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义必有利而义和。”(《利者义之和论》)“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明论》)“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谏论下》)“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谏论上》)“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权书序》)“夫使圣人而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远虑》)等等,这类文字,在苏洵散文中随处可见,虽未必一定都堪称定论,但从其论证的角度看,确实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这种名言警句式的词句,在其《心术》、《法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两篇乃逐段自为一节,每节自成一论,其间充满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如《心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
《法制》: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
夫能静而自观者,可以用人矣。吾何为则怒,吾何为则喜,吾何为则勇,吾何为则怯?夫人岂异于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观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途之人皆可以将。
《心术》论治心之重要,《法制》论用兵之法度,所论虽自《孙子》中来,并非都出自独创,但一经苏洵斟酌取舍,发而为文,其间仍闪烁着他思辨的光芒。而排比,对仗的句式也增添了其令人警醒的效果。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苏洵之文无论在立意上还是构思上,无论在篇章上还是在词句上,都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实践了自己“得乎吾心而言”和“不得不为”的理论主张,从而也形成了自己奇崛幽峭的散文风格。
[1]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M].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张谦宜.絸斋论文[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吴德旋撰,吕璜.初月楼古文绪论[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老泉全集(卷一)[M].清康熙刊本
[5] 铜板精印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卷九)[M].广州大成书局印行
[6] 楼昉.崇古文诀[M].文渊阁四库全书
[7] 孙琮.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卷二十五)[M].礼菴定本
On the Unusual and Prominent Artistic Style of Su Xun’s Ancient Articles
MAO De-she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The literary style of Su xun,not only manifests the free and easy of willful,but also manifests the profound of unusual.This kind of unusual and prominent article style both displays in the article intrinsic thought connotation,and displays in the article external language formally.Su Xun,who Pursues taking the best and establishes a new school in the article creation,not only painstakingly plans for the article,thinks sends profoundly,moreover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the style is powerful,in the language also pursues the novel and unique,not ordinary,thus displays the uniqu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rt style.
Su Xun;unusual;prominent;style
I206.2
A
1008—1763(2011)06—0078—04
2010-11-16
毛德胜(1977—),男,湖北罗田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