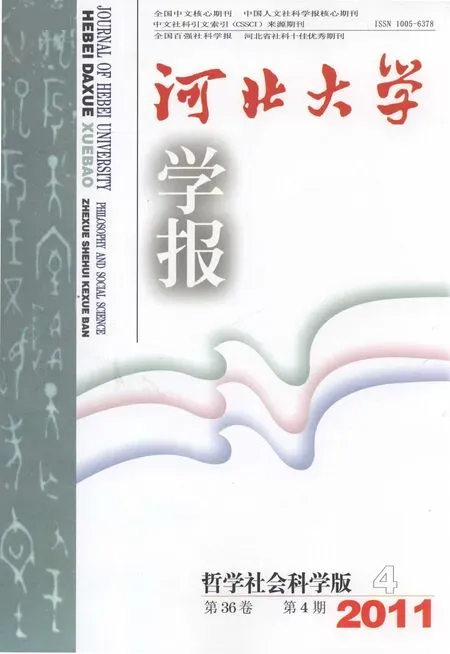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张军华
(广东商学院新闻传播系,广东广州 510320)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张军华
(广东商学院新闻传播系,广东广州 510320)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传媒影响力;传播效率;传播公正
众所周知,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究其成因,它既与当前人们对传播活动效果的日益重视相关,又与传播学界大力倡导的“影响力论”紧密相连。但由于我们在理解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影响力逻辑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令人忧思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传播实践中广泛流传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为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传播价值属性的回答。也正基于此,我们应当摒弃这种简单和片面的传播效率论,从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入手,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一、“影响力论”的提出、理解偏差及其误区
2003年,喻国明先生发表了《影响力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一文,在我国传播学界和传播业界都产生了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是从传媒经济的“二次售卖”规律出发,指出了以往人们把传媒经济视为“注意力经济”的局限性,并提出应当用“影响力经济”来概括传媒经济的本质特征;随后,作者从媒介传播活动三个环节的资源配置和运作模式,进一步阐述了传媒影响力的产生和建构过程及其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传媒之于市场的价值大小关键在于它通过其受众所产生的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产业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它的受众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行为,并进一步地影响社会决策和社会发展进程。进而言之,传媒影响力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为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所打上的“渠道烙印”[1]。应当承认,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力,与作者对大众传播的效果机制的深刻洞察密切相关。可以说,大众传播实践中通常充满了传、受主体间的相互博弈过程,谁在传播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整个传播进程也通常朝着有利于它的方向发展。也正因如此,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影响力逻辑不但成为传播业界普遍奉行的不二法则,而且在传播学术界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流)性的理论话语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虽然在某一些方面充满了真知灼见,但把它作为一种普适性的传播逻辑,“影响力论”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从其本质上讲,大众传播活动乃是社会成员之间借助信息传递实现的社会交往行为,它应当以主体间平等的沟通和对话为基础。但是,“影响力论”的核心旨意是强调传播主体对接受主体的主动控制,从而获得传播效果最大化和最优化。说得更明确些,传媒影响力之所以超越于传播注意力,就因为前者使传播主体更有效地控制接受主体。大众传播为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打上的“渠道烙印”,无非是对接受主体如何借助于传播内容控制(作用于)接受主体的委婉表达。其次,作为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影响力论”以大众传媒的市场价值为基点,把传播者对媒介受众的控制视为主要运作方式,以最终实现其媒介信息传播的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样,在日常传播实践中,传媒影响力往往会被简化为对传播活动效率的直接量度。而实际上,传媒影响力不应当以传播效率为唯一考量指标,还必须且应当包含着对传播价值导向的评价。最后,“影响力论”强调对社会主流人群的影响,即所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应当看到的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与普通大(民)众的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其舆论影响力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而且在很多时候,大众媒介传播不但很难真正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反而经常为这些社会主流人群的价值导向所影响和控制。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创意性文化产业,传媒产业生产之所以区别于一般产业生产,就在于它不仅仅服从于经济生产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受到文化产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制约。所以,以影响力逻辑来界定和诠释传媒产业的本质特征,势必在理论与实践上造成一系列的误解和混乱。但有必要申明的是,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影响力论”之于大众传媒运作逻辑揭示的某种深刻性。实际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大众传播活动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在于它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大众传播活动之所以显得越来越复杂,则是因为其影响力逻辑已变得日趋神秘、曲折和隐晦。因而本文认为,传媒影响力的确应当成为当代大众传播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当代大众媒介传播的影响力逻辑。
二、效率和公正:传播价值结构运动的现实矛盾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大众传播活动必然包含着两个基本的价值诉求,即传播效率和传播公正的辩证统一。从其内涵上来看,效率(efficiency)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一般把它解释为“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或是指“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在物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它是指物体所放出的功或能与输入的功或能之比,引申为所耗能量与工作效果——投入与产出——之比率。所谓“公正”则是公平、正义、公道的意思,从微观上把它理解为“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去待人处事的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在宏观上把它界定为“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2]。对一次传播活动来说,传播效率往往是指传播主体投入的物质资源、体力心智与其传播接受(阅听)效果之间的比率,主要体现为传播活动接受(阅听)效果的规模数量大小;而传播公正则通常是指传播接受(阅听)效果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品质,尤其是在发展方向上的正负性质和善恶特征等,它着重考察传播活动中的主体间互动关系是否属于“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在日常传播实践中,二者分别运行在传播价值结构的不同层面上,并由此决定着大众传播活动的结构特征与媒介景观。
从其内在逻辑来看,效率与公正表征为一种相互支撑和彼此贯通的关系,二者在传播价值量上并没有绝对的轻重之分。当我们进行传播活动效果分析时,既不能简单地认为传播效率高于传播公正,也不能武断地把传播公正凌驾于传播效率之上。一方面,离开了效率的公正是一种“虚伪”的公正,即所谓“迟来的正义通常是非正义的”。公正的实现本身包含着对提高效率的追求,效率的支撑是公正得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介入效率生成的一般过程,公正能降低其结构性的资源损耗,从而不断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因此,起点和过程的公正不但不影响效率,而且是最大地促进了效率的提高[3]。但问题是,在日常社会实践中,效率和公正之间却常常呈现出显著而深刻的矛盾冲突,而且其矛盾冲突已成为当代人面临的最深刻的现实困境之一。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正”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研究中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
众所周知,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相对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同一性而言,主体间的利益差异性通常属于一种极为普遍化和常态化的存在形式。所以,从其现实动因上讲,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在日常传播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源自于传、受主体间的价值诉求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主体往往侧重于信息传播行为对接受主体的控制(影响)作用及其强弱程度,即传播效率的高低;相反,接受主体则更加侧重于特定的信息内容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及其有效性如何,即传播公正与否。换言之,当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能满足公众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才能形成相互支撑和有机统一的关系;而当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背离公众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则会呈现出彼此矛盾冲突的紧张关系。也正基于此,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必然而且客观地存在着,它实质上是大众传播活动中内在价值结构矛盾的外在表征。
毋庸讳言,在日常传播实践中,基于这种内在矛盾冲突带来的问题已经是有目共睹和不容忽视的:大众传媒基于某种特定利益动机的推动下,粗暴地践踏和打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固有平衡,甚至以虚假的信息传播恣意扰乱广大公众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和判断,等等;这些纷杂无序的传播景观不但时有发生而且屡禁不止,更为重要的是,在经过其美学效果机制的修饰和润色之后,这诸多传播现象往往以一种既新潮时尚又合乎情理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因此,作为社会公共信息平台,传媒影响力的形成必须而且应当包含着效率和公正这两个重要价值维度,并使之存在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构性平衡之中。一方面,只有处理好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有效降低大众媒介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损耗;另一方面,只有使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才能够真正实现大众媒介传播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良性互动。质而言之,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随着大众传媒转型在广度与深度上的不断拓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种结构性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
三、当代媒介转型语境中的“影响力逻辑”重塑
在《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一书中,英国著名媒介文化家史蒂文森指出,大众媒介的转型是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最显著、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4]。简单地讲,大众媒介转型是指基于多种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大众媒介传播在运行方式和运作逻辑上发生的诸多变化。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它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显著而重要的结构特征,是因为以往任何时代中大众媒介的转型,对人类社会生活都未能产生今天这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具体来说,与以往的时代相比,当代媒介转型集中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而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当代媒介转型打破了传统媒介生态格局的固有特征,进一步加剧了以受众市场争夺为核心的传媒竞争态势。从表面上看,传媒竞争的加剧将迫使传播者更加重视媒介受众的信息需求,即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变为以受众为中心;但实际上,由于激烈的传媒竞争使媒介生存境遇变得更加的残酷,因此,在大众传播实践中,以受众需求为中心往往只是传者赢得传媒竞争的手段,而不可能真正成为媒介信息传播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日常生活对媒介信息传播的依赖性不断提高,大众媒介传播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必然千方百计地加大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和控制。与此同时,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尤其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传媒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民传播”的时代,这样,媒介话语权控制必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也更加复杂。
在《影响力经济》一文中,喻国明先生经过深入分析论证后明确地指出,作为一种特定的传播“渠道烙印”,传媒影响力通常是由传媒的物质技术特性和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两个方面构成的。进而,他又用“常量”和“变量”之别描述了二者对传媒影响力之发生和建构的不同作用;最后,他就如何提高传媒影响力的问题开出了一剂于操作性和战略性兼备的处方单[1]。应当承认,这种影响力逻辑既体现了作者的深刻洞察力又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而且对传播实践而言更具有极强的战术(操作)针对性。但本文认为,这种影响力逻辑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上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一方面,从传媒影响力之发生和建构来讲,与其说它由传媒的物质技术特性和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构成,不如说它受制于大众传播的信息内容特质和媒介策略特征,即传播什么与如何传播。其中,信息内容特质指媒介传递的信息是否符合真实性和时效性的要求,对受众的生活是否具有某种实际效用以及是否契合于受众的价值立场,它在传播效果意义上表征为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媒介策略特征则是指大众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机制,即假定以某种信息内容为共同的传播对象,但基于大众传媒采用的传播策略不尽相同,也可能对受众产生出不同的媒介传播效果①实际上,在《影响力经济》一文中,关于传媒社会能动性的运作过程特征也正好是从这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的。。
另一方面,在传媒影响力的发生和建构中,把传媒技术特性归之为“常量”也显然不太符合传播实践的真实情形。实际上,当代传播研究正日益重视有关传媒技术特性问题的讨论,就因为它作为媒介传播策略的重要构成要素,对媒介传播效果的生成已开始产生出越来越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影响力经济》一文中,喻先生也提到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的论述,但是却用社会“媒介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而一笔带过。殊不知,并不仅仅是关于“媒介即信息”的论述,麦克卢汉还在很多场合中以信息的“内爆”等概念,深刻地揭示了传媒技术特性之于媒介传播效果生成存在着某种关键性乃至颠覆性的影响作用。
进而言之,传媒影响力的发生和建构本质上反映了媒介传播策略与信息内容特质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其中,媒介策略特征通常与传播效率的变化状态相关联,而信息内容特质往往体现为传播公正性内在蕴含的价值诉求。在日常传播实践中,由于信息内容特质总是直接关涉到社会利益分配过程,因此,人们往往会基于不同的目的而介入媒介信息选择机制,使传媒舆论导向趋利于自己特定利益的获取与维护。在这种情况之下,影响力逻辑并不可能真正诉求于传播公正性的价值之维,相反,在大多数时候它可能更加倚重于媒介策略特征的发挥。也正基于此,在当前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合理地重塑传媒影响力逻辑的价值结构,已经成为摆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复杂的现实任务;我们必须在深刻理解前述传媒影响力逻辑的片面性基础上,以传播公正性作为大众传播活动的核心价值要素,重新塑造传媒影响力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文化品格,并由此有力地推动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因为从根本性意义上讲,一种理想的传媒影响力逻辑离不开对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双重价值追求。
四、结 语
总体来说,与一般商品交换中的二次售卖过程不同,传媒影响力的发生与建构往往渗透着某种特定的利益价值导向,进而与不同主体间的社会权利分配过程勾连在一起。实际上,伴随着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日趋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势必进一步加大媒介传播控制权的激烈争夺,使传媒影响力逻辑发生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尤其是在当代媒介转型的语境中,传播策略机制对传媒影响力逻辑的调控作用更强,相对于复杂而高效的大众传播机器而言,广大媒介受众的“对抗式阅读”(斯图尔特-霍尔)往往显得格外的微不足道。因此,基于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大众媒介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但首先必须合理地重塑传媒影响力逻辑的价值结构。这无疑是一项极其复杂而且非常艰巨的系统建设工程。
应当承认的是,在任何社会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偏向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现实情形。但是,作为指导大众传播实践发展的“战略性纲目”,传媒影响力逻辑必须努力保持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结构性平衡,使二者产生出一种彼此贯通、相互支撑的综合作用力。为此,传媒影响力逻辑的重塑之道首先必须从传播理念上认真厘清过去存在的种种理解偏差,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在实践中的危害性;同时,还应当使之能真正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论思想资源,进而有效地融入大众传播规范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否则,在当前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传媒影响力逻辑的重塑将沦为一种抽象的空谈清议和理论务虚之中。也正为因如此,本文并不是一次简单地向“影响力论”发问或媒介传播批评,而是旨在以此为由头提醒人们必须从学理层面上深切关注当代传播规范的相关问题了。毕竟,在当前传媒实践中,传媒影响力逻辑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传媒业界所奉行的某种富有“战略性纲目”意义的操作规程和媒介攻略。
[1]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J].新闻战线,2003(6):24-27.
[2]李晓明,辛军.诉讼效益: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点[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1):3-12.
[3]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J].战略与管理,2001(2):47-53.
[4]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The Media Influence:between Media Efficiency and Media Justice
ZHANG Jun-hua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Guangzhou 510320,China)
In modern communication practice,the media influence logic seems to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However,because of some deviation and misreading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matter,it gives raise to many worrisome problems.By analyzing this matter based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paper,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edia influence logic,which is popular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is often simplified to be a unilateral law of media efficiency,and avoid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media justice deliberately or unwittingly.Therefore,we must discuss deep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efficiency and media justice,to understand comprehensively the media influence logic in modern communication,and directeffectively th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a healthy way.
media influence;media efficiency;media justice
G206
A
1005-6378(2011)04-0106-05
2010-12-10
2010年教育部社会基金项目《当代媒介转型中的传播规范问题研究》(10YJD860002)
张军华(1966-),男,湖南省慈利县人,新闻学博士,广东商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郭玲]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高校法律翻译教学的机制
-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及其展望
- 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及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