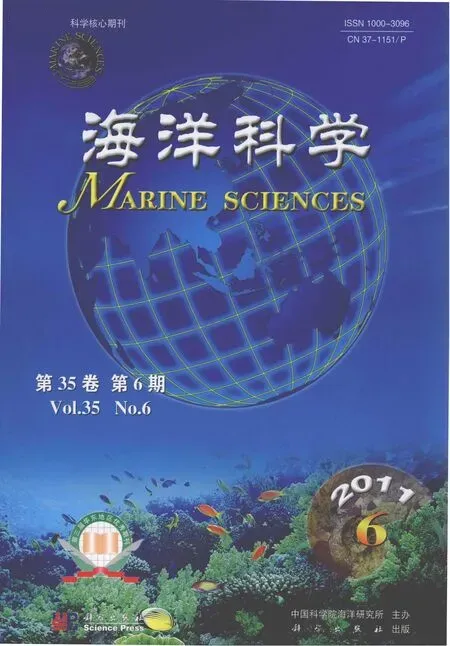中国海多毛纲动物研究现状及展望
周 进, 李新正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200090; 2.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71)
中国海多毛纲动物研究现状及展望
Analysis and outlook for polychaete studies from China’s seas
周 进1, 李新正2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200090; 2.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71)
根据广泛收集的文献资料, 结合作者近年来从事多毛纲动物研究所积累经验, 综述了中国海多毛纲动物研究现状, 旨在分析和总结其中所存在问题,推动中国海此门类研究。分析结果显示, 中国海多毛纲动物研究多集中在分类学领域, 在此基础上其他领域研究也陆续开展; 综合研究水平和国际相关研究对比, 尚存差距。迄今为止, 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共报道57科, 仅有不到一半的科(约24科)有过较为系统的分类学研究, 大多数科的研究仅停留在种类零星记录水平。浮游多毛类研究较底栖种类更为薄弱,已有报道数量较少。多毛类分类学研究的薄弱直接影响到海洋生态学和其他相关研究。已有的生态学研究中所记录的种类存在一定数量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现象, 甚至某些水域中所记录的优势种均属错误鉴定结果。根据国内研究现状,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海多毛类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近岸种类的系统鉴定;据此基础, 高级分类阶元之间亲缘关系、地理分布特点等基础研究以及多毛类在海洋环境污染中的指示作用、经济种类养殖推广等应用型研究也应是学科发展趋势和未来研究重点。
1 多毛纲动物简介和研究意义
多毛纲(Polychaeta)隶属于环节动物门(Annelida), 其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 高于同门另外两纲(寡毛纲和蛭纲)。其中, 海水种类较多, 咸淡水和淡水种类较少。多毛类营浮游生活, 成体底栖(极少数科种类终身浮游)。多毛类动物在中国近海沿岸水域极其常见, 其成体是海洋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四大类群之一(多毛类、甲壳类、贝类、棘皮动物)。在野外大型底栖动物采样时, 几乎每个潮间带或潮下带站点均可以采集到此类动物; 且其物种多样性和栖息密度往往远高于其他无脊椎动物类群, 部分站位中种类数可占到样品总种类数60%。
多毛类动物是近海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它们产生了形形色色适应于不同环境的形态特征和生活史策略。因此, 研究该类群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次, 多毛类是一群古老生物, 幼体浮游期较短, 成体多底栖生活且活动和扩散能力很弱,所以也是探讨生物地理亲缘关系的合适材料。另外,从多毛类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网所处位置来看, 多毛类位于地球生命金字塔底部。多毛类摄取底质中的营养物质, 同时也为鱼虾等海洋经济动物提供了丰富饵料, 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开展多毛类动物研究和发展我国海洋渔业密切相关[1]。近年来, 在一些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水域内, 如密集养殖水域、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口,底栖甲壳类、贝类等因缺氧已难觅踪影, 而多毛类尚能维持一定的物种多样性和栖息密度。其中部分种类, 如小头虫(Capitella capitataFabricius, 1780)、毛轮沙蚕(Ophryotrocha puerilisClaparède &Metschnikov, 1869)、枫香树奇异稚齿虫(Paraprionospio cooraWilson, 1990)、白腺缨鳃虫(Laonome albicingillumHsieh, 1995)等却能大量繁殖,因此可以把这些特殊种类种群的数量变动情况作为判别海洋污染程度的指标[2-4]。此外, 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所形成的多毛虫管化石的沉积物, 可以作为寻找天然氧和石油的一种依据[1]。
2 研究现状
2.1 中国海研究现状
2.1.1 分类学研究
中国海多毛类动物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学方面。虽然该类群动物在我国近岸海域较为常见, 但和中国海其他常见海洋无脊椎动物门类(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相比, 多毛纲动物的分类学研究进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多毛类动物多营底内生活、大部分个体较小且与人类直接接触不多、多数种类经济价值不高以及鉴定工作繁琐等因素所致。
中国海多毛纲分类学研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9世纪。早期研究主要是少数国外学者针对中国近岸采集标本所作的零星记录, 多为沙蚕科种类。如Grube[5]报道了采自我国广东省的中华疣吻沙蚕Tylorrhynchus chinensis, Chamberlin[6]记录了采自广东省稻田可食用的中华沙蚕Chinonereis edestusChamberlin, 1924。中国海多毛类动物分类学研究真正开始于 20世纪 30年代, 高哲生[7]发表了“青岛近岸之多毛目环节动物”。此后, 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伴随着一系列海洋生物调查逐步开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海洋生物调查包括 1958~1959年的中国近海海洋普查、1959~1962年北部湾调查、1975~1976年东海大陆架综合海洋调查、1980~1985年全国海岸带和滩涂综合资源调查、1989~1993年全国海岛调查、1980~1982年和 1985~1987年中美合作对长江和黄河的河口水下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进行的联合调查和近年来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即 908专项)等。在此期间, 中国海多毛类种类陆续被整理和报道, 并发表了一定数量新的物种。从具体研究内容来看, 沙蚕目和叶须虫目研究地较为透彻, 此两目种类已以中国动物志(无脊椎动物, 第九卷、第三十三卷)形式发表[1,8]。从研究海域来看, 黄渤海底栖样品采集量较大, 分类学研究相应地较为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前, 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此时, 中国海多毛类动物分类学研究始终有一支稳定、且数量可观的分类学人才队伍作保障。期间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 和国外同行专家也有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而此时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类似, 均将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重点放在沿岸水域种类的准确记述上。总体来看, 建国后至20世纪90年代, 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保持着较高水平, 和国外相关研究之间差距也不是很大。1995年世界多毛类动物研究大会在青岛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学者在世界多毛类研究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此后十多年间, 由于诸多客观原因, 加上对分类学研究普遍重视不够的大环境, 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队伍逐渐萎缩。虽然研究工作不断发展, 但进展缓慢。近年来, 现状仍无明显好转, 直接面临着几乎没有一个全职工作者从事多毛类分类学研究的局面。三年一度的世界多毛类研究大会代表了当今多毛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而在这样的学术会议上鲜有中国大陆科研工作者身影。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约10年的时间里, 是国际多毛类分类学研究迅速发展时期。而中国海相关研究在此时期内未有充分发展, 实际上拉大了与其他国家间差距。以中国海邻近海域为例, 至21世纪初, 日本水域和俄罗斯近岸水域所分布的多毛类种类已有较为系统记录, 常见种类组成清晰明了。此两处水域和中国海同属西北太平洋, 特别是日本海域,其多毛类种类组成和中国海相似性很高, 很多模式产地为上述两处水域的种类近年来在中国海也陆续被发现。相对而言, 根据中国海为模式产地发表的新种则较少。
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有非常多的工作亟待开展。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应有约60科, 1000余种。然而, 仅有数量不到一半的科(24科)有过较为系统的种类记述, 大多数科的种类仅有零星记录, 如竹节虫科、小头虫科等, 部分科属的分类学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杨德渐等[3]曾对中国近海多毛类种类做过总结, 是如今中国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其中共记录356种, 后续研究显示尚需做进一步增补。此外, 近年来分类学研究表明, 已有中国沿岸多毛类种类记录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错误鉴定, 甚至是一些种群数量很高的优势种。如本文作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反复比对检查标本,认定以前我国文献记录的海稚虫科奇异稚齿虫属中奇异稚齿虫Paraprionospio pinnata(Ehlers, 1901)实际包括 3种, 即扭鳃奇异稚齿虫Paraprionospio inaequibranchia(Caullery, 1914)、枫香树奇异稚齿虫Paraprionospio cooraWilson, 1990和冠奇异稚齿虫Paraprionospio cristataZhou et al., 2008。其中冠奇异稚齿虫为一新种, 扭鳃奇异稚齿虫和枫香树奇异稚齿虫在中国海属首次记录。枫香树奇异稚齿虫主要分布于黄海, 其分布南界为 121°30′E, 34°30′N, 扭鳃奇异稚齿虫分布于南海, 其分布北界为 114°00′E,21°45′N, 冠奇异稚齿虫分布区域较广, 从长江口到南海的沿岸水域均有分布。奇异稚齿虫是分布在智利、南加利福尼亚、西墨西哥(可能还有安哥拉)的种,在我国海域未见分布[9]。又如, 我国北方近岸极其常见但长期被记录为鳞腹钩虫Scolelepis(Scolelepis)squamata(Müller, 1806)(海稚虫科)的标本经重新鉴定, 已确定为一个新种, 即红纹腹钩虫Scolelepis(Scolelepis)daphoinosZhou et al., 2009; 鳞腹钩虫分布于北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水域, 在我国海域未见分布[10]。类似这样例子还有一些[11-14], 在此不一一列举。上述问题说明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需要更为科学系统的深入, 不仅要依靠已有研究基础,更需要扎实有效、创新性的工作。
近年来海洋生物调查采样频率较高, 除国家海洋调查专项外, 海洋生态学研究, 特别是底栖生态学研究也会大量采样; 此外, 每年大量的海洋工程建设环境评价项目也会采集到大量的海洋底栖生物标本。由于多毛纲动物是大型底栖生物中习见种类,因此其样品的采集数量非常可观。这些都为中国海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础, 然而, 在相当多的研究中, 多毛类标本的鉴定仅是为了满足具体项目(非分类学研究项目)需要, 很少真正地应用到分类学研究中来。而且多数标本鉴定后并没有规范保藏, 造成了样品不可恢复的破坏, 也是对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
目前国内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多将成体标本作为研究材料。实际上, 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应包括另一重要部分, 即浮游多毛类。包括生殖期浮游(群浮或起浮)多毛类、多毛类幼体和终生营浮游生活种类(盘首蚕、眼蚕、浮蚕和盲蚕等少数几科)。多毛类幼体处于高速发育阶段, 形态学特征变化快, 种类鉴定十分困难, 需要以室内的连续培养观察作为基础。成体浮游多毛类样品固定时容易变形, 生殖期个体形态特征特殊, 这些情况均会造成分类学性状难以观察,给分类学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我国关于多毛类幼体的分类学研究开展较少, 大多数从事多毛类分类学工作的学者并未在此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仅有少数研究成果见诸报道[15-20]。多毛类幼体鉴定时往往笼统地归为浮游动物大类中。
在传统分类学研究基础上, 少数学者对多毛纲中某些科属间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 如吴宝铃等[18]利用支序分析方法探究浮游多毛类眼蚕科九属之间系统演化关系, 韩洁等[21]综述了多毛纲动物系统学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国内少数学者将分子证据引入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中。如利用特定片段序列结构(如18S rDNA和COI)来揭示种间遗传距离, 利用延长因子 la的编码基因(EF-1a), 线粒体编码基因 16S rDNA以及其他核基因(组蛋白H3,U 2s nRNA, 28S rDNA)等序列来探讨系统发生关系[22]。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引入丰富了多毛类分类学研究手段, 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果。但应该注意,分子生物学技术仅是解决分类学问题手段之一, 应以形态学研究结果为基础和佐证。大部分多毛类种类间形态差异明显, 分类学特征稳定、实用。对于这些种类的甄别, 传统形态学研究方法可以胜任, 而且更为便捷、奏效。而对于形态学特征非常相似、传统分类方法难以解决的种类复合体或疑难种类研究, 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作为重要辅助手段进行尝试。
2.1.2 生理生态研究
作为海洋底栖生物习见类群, 关于多毛类动物分布格局、优势种生态学特点等文章较多。从采样海区来看, 覆盖了黄渤海、东海、南海各大海区; 从生境来看, 既有特定海域潮间带多毛类分布特征,也有潮下带栖息状况[23-35]。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多毛类生物学知识, 也是分类学、动物区系发生和系统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多毛类是海洋污损生物重要组成部分, 部分学者据此特性开展研究。如王建军[36]记述黄渤海污损生物43种, 严岩等[37]记录南海北部近海污损生物48种。此外, 关于多毛类生理学研究, 也已有一定数量的报道, 主要集中在沙蚕科种类上。如丘建文等[38]研究光周期对搓稚虫生长和生殖的调节, 石小平、赵清良[39]研究了数种典型生态因子对双齿围沙蚕早期生活史的影响, 朱明远等[40]研究沙蚕科性信息素的种间作用, 杨宇等[41]研究多齿围沙蚕群浮特性和温度之间关系, 朱明远等[42]报道了温度和月相对多齿围沙蚕群浮的诱导作用, 周一兵、王宏[43]研究大连湾双齿围沙蚕卵子生成周期和温度、光照时间的关系。唐森铭等[44]针对典型海洋污染物对多毛类动物影响,开展多毛类环节动物对柴油污染效应的模拟生态研究。
2.1.3 多毛纲经济种类养殖
多毛类多为高蛋白食品, 部分种类, 如疣吻沙蚕, 其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 维生素B1也特别丰富, 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因此, 养殖和围捕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多毛纲动物中做为采捕与养殖对象的多为沙蚕科中个体较大的种类, 如多齿围沙蚕、双齿围沙蚕、疣吻沙蚕等。吴宝铃、丘建文[45]评估了青岛多齿围沙蚕的生产量。部分学者撰文综述沙蚕或其中部分种类的育苗技术、养殖方式及其利用开发现状[46-49]。
2.2 世界其他典型水域研究现状
中国海属西北太平洋水域, 此区域内的多毛类研究现状呈现出明显不均匀性。日本海及其邻近海域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开展地最为透彻。至20世纪末期, 该水域内分布的常见多毛类种类已系统整理并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发表[50-54]。此外, 俄罗斯水域(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也有较高水平, 部分科属已有深入研究, 特别是该水域内浮游多毛类分类学研究, 水平较高。
东太平洋和西大西洋是多毛类分类学研究较为深入水域。此海域内多毛类分类学研究历史悠久, 又经过许多学者数十年来不间断的持续研究, 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学科先锋。由于研究人数较多, 部分学者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个科或几个科。如美国学者N. J.Maciolek专门针对美国沿岸, 特别是北大西洋水域海稚虫科进行深入研究, 详细整理了种类, 且发表相当数量新种和新纪录种[55-62]。
澳大利亚附近海域也是多毛类研究水平较高区域之一, 分类学领域一直活跃着相当多数量的学者,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63-66]。
在形态学研究基础上, 多毛纲动物系统学[67-68]、解剖学[69-70]、生物学[71-72]、分子生物学[73-74]等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
3 多毛类分类学研究中应注意问题
3.1 需要特别注意的分类性状
传统多毛纲动物分类学研究中使用性状主要包括: 口前叶(prostomium)、围口节(peristomium)、触手(antenna)、触须(palp)、项器(nuchal organ)、疣足(parapodium)、食道(stomodaeum)、循环系统(circulation)、刚毛(chaeta)和分节器官的结构及其分布特点等。这些经典性状有很强科学性, 且实用合理。而部分较少受关注的性状在多毛类种类鉴定时也应引起重视。(1)变形刚毛: 变形刚毛特征是多毛类种类鉴定重要性状之一。该特征包括变形刚毛形状、数量、起始位置等。变形刚毛形状十分多样化, 如巾钩刚毛(单齿、双齿、三齿、多齿等)、足刺状刚毛、矛状刚毛、刷状刚毛等。然而在实际鉴定过程中, 由于变形刚毛较小, 需要取下疣足, 制成临时水装片后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过程较为繁琐, 很多鉴定中根本不观察刚毛这一重要性状, 因此, 极易造成错误鉴定。观察变形刚毛这一性状应先将整个标本放在体视显微镜下面, 初步观察疣足背叶和腹叶有无变形刚毛, 确定变形刚毛起始位置, 记录变形刚毛数量, 观察大体形状。然后再取出典型疣足, 制成临时水装片在显微镜下观察详细特征, 以常见的巾钩刚毛为例, 观察巾钩刚毛包括多少小齿, 有无开放的巾, 巾钩弯曲程度等。同一种类不同个体标本均需要仔细检查, 记录好变形刚毛数量, 不同地理种群样品之间变形刚毛数量变化范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2)腹褶形状和数量: 以往多毛类种类鉴定时多注重背褶的形状和数量, 而腹褶由于着生在腹面,且大多数多毛类种类无腹褶, 故此结构往往容易引起忽视。而本文作者在多毛类分类学研究时发现, 腹褶形状、有无可作为一个稳定、实用的分类学性状,以作者已发表的 2个新种为例, 即冠奇异稚齿虫Paraprionospio cristataZhou et al., 2008和太平洋稚齿虫Prionospio pacificaZhou & Li, 2009, 前者第9、10节上存在明显腹褶, 后者第 9刚节上有明显腹褶,且此类腹褶结构不论在大小个体上均明显存在[9,75]。(3)体表色素: 酒精固定的标本中色素细胞容易破裂,因此大部分酒精固定的标本均是灰白色。然而实际上, 许多多毛类种类活体体表色素细胞十分多样,往往很鲜艳, 应是种间重要差别之一, 只是在固定标本中难以观察。然而部分色素细胞可以保持很长时间, 如黄海潮间带和潮下带浅水区广泛分布的红纹腹钩虫Scolelepis(Scolelepis)daphoinosZhou et al.,2009区别于同属其他种类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口前叶后缘、体前部背面、体前部疣足之间均有明显的斑块状红纹, 红纹特征也是此种命名时的主要依据[10]。可以预测, 在其他种类固定标本中, 也可能遇到类似情况。(4)触手结构: 触手在标本采集、固定过程中容易脱落, 故观察固定标本时很难看到触手结构, 已有种类形态学描述时也少有触手特征描述。但随着分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形态学描述应包括的性状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 结构也越来越精细。触手做为多毛类捕食的重要工具, 其形态学特点应是种间差别的重要体现, 这部分内容应包含到常规形态学描述中去。国外已有专门针对触手结构研究, 进而从中发现数个稳定分类学性状的例子[76]。
3.2 分类学研究所需设备
传统分类学研究主要根据外部形态特征和部分解剖结构, 这些结构多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所需设备虽然比较简单, 但对显微镜和体视显微镜的质量要求很高。多毛类标本由于采集后多用酒精或甲醛固定, 经常造成蜷缩, 因此在观察头部、疣足及体表结构时往往比较困难, 需要有一定实验操作技巧和较好的耐心。分类学研究属基础研究, 难有数额较大的基金支持, 而一台质量上乘的显微镜则价格不菲。因此, 观察设备往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种类鉴定工作。根据实际经验, 作者认为体视显微镜的质量在多毛类鉴定中最为重要, 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显微镜。因为体视显微镜多用来观察标本整体, 立体效果非常重要, 对显微镜景深要求较高, 否则观察标本时极易造成只有一个平面清晰而其他平面异常模糊的局面。而显微镜多观察水装片, 所有样品均在同一平面上, 大部分显微镜均可胜任。体视显微镜外接绘图仪也非常重要, 因为观察过程中可能随时要对重要性状进行描图, 做好原始观察记录, 以供比对。分类学论文发表时也需要有手绘线条图, 线条图往往比照片, 甚至是扫描电镜图片更能反应分类学特征,也因此更受国内外同行专家青睐。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也是分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虽然扫描电镜没有线条图便捷、直观, 但其优点同样明显, 特别是针对非常精细的结构。多毛类中有相当多结构观察时需要借助扫描电子显微镜, 常见的如鳃、触手和变形刚毛等细微结构。随着分类学研究的深入, 鳃上诸多显微结构, 如鳃小片形状、纤毛结构等逐渐被观察描述, 并被认为是可靠稳定的分类学性状。触手也是如此, 有无触手鞘以及触手基部是否着生纤毛等也被认为是重要性状。这些精细结构的描述和表现由于体视显微镜放大倍数不够, 线条图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须辅以电子显微镜照片。
3.3 多毛类分类学人才培养
解决中国海现行多毛类研究中所存在问题须从多方面努力,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培养更多此类研究人才。多毛类分类学研究是海洋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应受到重视。种类鉴定工作也应由训练有素的分类学工作者来进行。现在很多研究或调查中的种类鉴定往往是大量沿用已有文献记录来解决, 很少有作者原始研究, 错误鉴定记录往往因此传播很大范围, 以讹传讹。近年来, 海洋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和《中国海洋生物名录》[77-78], 这些专著汇总已有分类学资料, 可以方便相关研究人员引用, 意义重大。但在出版此类专著同时, 也需要大量基于原始数据的分类学研究论文, 后者作用同样明显。
在多毛类研究基础较好国家, 部分学者往往是毕其一生精力于某一个科或某几个科研究。可以想象, 这种模式下的研究结果才更为科学和深入。实际上, 由于多毛类种类繁多, 形态学变化较大, 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想把整个多毛类进行透彻的分类学研究非常困难, 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思考。
4 展望
多毛纲动物在中国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目前对此重要类群的研究远远不够,许多方面研究十分薄弱, 某些方面更是空白。因此,中国海多毛类研究的空间巨大。出现上述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从事多毛类研究的学者太少, 而少数学者不可能同时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因此, 解决上述问题根本在于相关研究人才培养, 只有研究队伍的壮大, 问题才能有望得到解决。
4.1 分类学研究
在所有多毛纲动物研究中, 分类学研究应是基础, 分类学研究不仅是分类学本身发展的需要, 也可为其他研究, 如生态学研究、生理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目前国内已有的生态学研究中所记录种类存在相当数量同物异名、异物同名等现象, 甚至某些生态特点较为典型水域中所记录的优势种均属错误鉴定结果。种类鉴定工作是分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按图索骥, 这首先因为多毛类种类多样性很高, 形态变异性较大。其次, 多毛类鉴定特征非常繁杂。一个典型种类鉴定需要观察20余个性状, 且部分性状观察时操作十分困难。如矶沙蚕科某些种类鉴定时, 除了观察口前叶、围口节形状、巾钩刚毛结构等较为常见的性状外, 还需要对样品口器进行进一步的解剖观察, 确定其齿式结构。另外, 部分性状的观察需要长时间经验的积累;否则, 仅对照参考资料上文字描述和绘制的线条图很难进行准确把握, 如多鳞虫科中不同口前叶形状的区分(背鳞虫型、栖鳞虫形、哈鳞虫形等)、竹节虫科不同类型头板和肛板结构等。此外, 由于中国海多毛类研究起步较晚, 基础较为薄弱, 分类学研究时可供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匮乏; 且部分记录种类仅是在生态学文章或调查报告中出现, 并无详细的形态学特征描述和据典型特征所绘制的线条图, 这些记录在实际种类鉴定中也很难引用。
中国海多毛类研究依然有很多任务亟待完成。仅是中国近岸常见种类的准确记录, 便需要大量工作。根据作者近年来从事多毛类分类学工作实际经验和国内研究现状, 可以预测, 要清晰记录中国近岸水域分布多毛类种类至少需要 20年或更长的时间。
4.2 多毛纲高级分类阶元亲缘关系分析
中国海沿岸水域所分布多毛类种类的厘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多毛类研究的重点, 然而随着分类学研究的深入。多毛纲高级分类单元间、及其和邻近无脊椎门类如须腕动物、腕足动物等之间亲缘关系研究也是多毛类研究重要组成部分, 这对于了解无脊椎动物的系统进化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未来关注重点。此外, 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应更多、更广泛地补充到传统分类学研究工作中。
4.3 其他方面的研究
在分类学研究基础上, 应广泛开展包括区系、形态、生态、生殖、生活史、地理分布、虫管化石和系统发生等方面全面而系统研究。目前, 多毛纲的养殖种类多集中在沙蚕科的部分种类中, 实际上, 随着研究的深入, 应该可以挖掘到更多的养殖品种,如矶沙蚕目中许多种类个体较大, 应有一定的开发潜力。总之, 此方面研究的空间应该十分巨大。
[1]吴宝铃, 吴启泉, 丘建文等.中国动物志环节动物门多毛纲(I)叶须虫目[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7:329.
[2]吴宝铃. 中国海首次发现的海洋污染研究实验动物——毛轮沙蚕[J]. 环境科学学报, 1981, 1(2):190-192.
[3]杨德渐, 孙瑞平.中国近海多毛环节动物 [M].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8: 352.
[4]Hsieh H L.Laonome albicingillum, a new fan worm species (Polychaeta: Sabellidae: Sabellinae) from Taiwan [J].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95, 108 (1): 130-135.
[5]Grube A E. Beschreibung neuer von der NOVARA-Expedition mitgebrachter Anneliden und einer Landplanaria [J]. Verh Zool Bot Gesells Wien,1869, 16: 173-184.
[6]Chamberlin R V. A new freshwater nereid from China[J]. Proceedings of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1924, 37: 79-82.
[7]高哲生. 青岛近岸之多毛目环节动物 [J]. 山东大学科学丛刊, 1933, 1: 437-451.
[8]孙瑞平, 杨德渐. 中国动物志无脊椎动物第三十三卷环节动物门多毛纲(二)沙蚕目[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520.
[9]Zhou J, Yokoyama H, Li X Z. New records ofParaprionospio(Annelida: Spionidae) from the Chinese water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J].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2008,121(4): 308-320.
[10]Zhou J, Ji W W, Li X Z. A new species ofScolelepis(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sandy beaches in China,with a review of ChineseScolelepisspecies [J]. Zootaxa, 2009, 2236: 37-49.
[11]Zhou J, Li X Z. A report of the family Paraonidae(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China seas [J].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2007, 32 (2): 275-282.
[12]Zhou J, Li X Z. First record ofParaonella platybranchia(Hartman, 1961) (Polychaeta: Paraonidae) from the Yellow Sea [J].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onology, 2009, 27 (1): 100-102.
[13]Zhou J, Ji W W, Li X Z.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Microspio(Annelida: Spionidae)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J]. Marine Fisheries, 2009, 31 (3): 225-229.
[14]Zhou J, Ji W W, Li X Z. Records ofPolydoracomplex spionids (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China’s coastal waters, with emphasis on parasitic speci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J]. Marine Fisheries, 2010,32 (1): 1-15.
[15]沈寿彭, 吴宝铃.中沙群岛浮游多毛类的初步调查[J].海洋与湖沼, 1978, 9(1): 99-107.
[16]孙瑞平, 黄将修, 陈清朝.台湾东北和西北部沿岸海域的浮游多毛类[J]. 台湾海峡, 1998, 17 (3): 351-354.
[17]孙瑞平, 沈寿彭, 吴宝铃.中沙群岛浮游多毛类的初步调查[C]//我国西沙、中沙群岛海域海洋生物调查研究报告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8: 133-169.
[18]吴宝铃, 陆华.支序分类 CLADISTICS在浮游多毛类眼蚕科 ALCIOPIDAE系统演化研究中的应用[J]. 动物学报, 1993, 39(1): 23-29.
[19]吴宝铃, 孙瑞平.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地理分布和演化的初步探讨[J]. 海洋与湖沼, 1978, 9(2):215-223.
[20]吴宝铃, 孙瑞平, 陈木. 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多毛类动物地理学的研究[J]. 海洋学报, 1980, 2(1):111-130.
[21]韩洁, 林旭吟. 多毛纲动物系统学研究进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43 (5): 548-553.
[22]廖秀珍, 林荣澄. 多毛类 18SrDNA和 COI基因序列片段及其分子系统发育研究[J]. 台湾海峡, 2006, 25(4): 490-497.
[23]何明海. 东山湾潮间带多毛类生态初步研究[J]. 海洋通报, 1990, 9 (2): 48-52.
[24]何明海. 东山湾潮下带多毛类的分布[J]. 台湾海峡,1990, 9 (3): 206-211.
[25]Cai L Z, Xu Z M. Distribution of polychaete in subtidal zone, Haitan Islands [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1994, 33 (4): 537-542.
[26]虞蔚岩, 李朝晖, 黄成, 等. 互花米草入侵对盐城东台盐滩多毛纲动物多样性的影响及管理对策[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09, 18 (1): 47-52.
[27]毕洪生, 孙道元.胶州湾多毛类的生态特点[J]. 生态学报, 1998, 18 (1): 63-68.
[28]王金宝, 李新正, 王洪发.胶州湾多毛类环节动物优势种的生态特点[J]. 动物学报, 2006, 52 (1): 63-69.
[29]蔡立哲, 李复雪. 闽南—台湾浅谈渔场多毛类的分布[J]. 台湾海峡, 1995, 14 (2): 144-149.
[30]蔡立哲, 林鹏, 佘书生, 等.深圳河口泥滩多毛类动物的生态研究[J]. 海洋环境科学, 1998, 17 (1): 41-47.
[31]蔡立哲, 林鹏, 刘俊杰.深圳河口泥滩3种大型多毛类的数量动态及其环境分析[J]. 海洋学报, 2000, 22 (3):110-116.
[32]蔡立哲, 厉红梅, 刘俊杰, 等.深圳河口泥滩三种多毛类的数量季节变化及其污染影响[J]. 生态学报,2001a, 21 (10): 1648-1653.
[33]蔡立哲, 厉红梅, 林鹏, 等.深圳河口潮间带泥滩多毛类的数量变化及环境影响[J]. 厦门大学学报,2001b, 40 (3): 741-750.
[34]林俊辉, 郑凤武.泉州湾及其附近海域底栖多毛类生态的初步研究[J]. 台湾海峡, 2007, 26 (2): 281-288.
[35]吴启泉. 台湾海峡西部海域软质海底多毛类的生态[J]. 台湾海峡, 1993, 12 (4): 324-334.
[36]王建军. 黄渤海沿岸污损生物中的多毛类[J]. 海洋通报, 1991, 10(5): 52-58.
[37]严岩, 严文侠, 董钰, 等.南海北部近海污损生物中的多毛类[J]. 海洋通报, 1995, 14 (6): 40-45.
[38]丘建文, Lisa Levin, 吴宝铃.光周期对多毛类搓稚虫Streblospio benedicti生长和生殖的调节[J]. 黄渤海海洋, 1990, 8(3): 36-43.
[39]石小平, 赵清良. 几种生态因子对双齿围沙蚕早期生活的影响[J]. 生态学杂志, 1993, 12 (5): 21-24.
[40]朱明远, 杨宇, 吴宝铃. 沙蚕科性信息素的种间作用[J]. 海洋学报, 1994, 14 (5): 95-100.
[41]杨宇, 朱明远, 吴宝铃. 多毛类多齿围沙蚕(Perinereis nuntiaSavigna)的群浮[J].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 1992, 22 (3): 49-53.
[42]朱明远等. 温度和月相对多齿围沙蚕的群浮诱导[J].动物学报, 1994, 39 (2): 222-225.
[43]周一兵, 王宏. 大连湾双齿围沙蚕(Perinereis aibuhiteris)卵子生成周期及其与温度和光照时间的关系[J]. 大连水产学院学报, 1995, 10 (2): 9-17.
[44]唐森铭, 陈孝麟, 庄栋法, 等. 多毛类环节动物对柴油污染效应的模拟生态研究[J]. 海洋学报, 1993, 15(4): 85-90.
[45]吴宝铃, 丘建文. 青岛多齿围沙蚕的生产量[J]. 生态学报, 1992, 12(1): 61-67.
[46]郑金宝. 多齿围沙蚕的繁殖及培育的初步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 2000, 5 (2): 38-43.
[47]黄凤鹏, 丘建文, 吴宝铃, 等. 日本刺沙蚕Neanthes japonica(Izuka)大规模育苗的初步研究[J]. 黄渤海海洋, 2001, 19 (4): 76-80.
[48]孙瑞平, 黄猛, 杨德渐, 等. 沙蚕养殖与开发[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164.
[49]法清江, 丁欣宁. 双齿围沙蚕的人工育苗技术[J]. 齐鲁渔业, 2007, 24(9): 37-38.
[50]Imajima M, Hartman O. The polychaetous annelids of Japan [J].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Allan Hancock Foundation, 1964, 26: 1-452.
[51]Imajima M. Spionidae (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Japan, Ⅱ The GenusPrionospio(Aquilaspio) [J].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Museum, Tokyo (A,Zool.), 1990a , 16 (1): 1-13.
[52]Imajima M. Spionidae (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Japan, Ⅲ The GenusPrionospio(Minuspio) [J].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Museum, Tokyo (A,Zool.), 1990b, 16 (2): 61-78.
[53]Imajima M. Spionidae (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Japan, Ⅳ The GenusPrionospio(Prionospio) [J].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Museum, Tokyo (A,Zool.), 1990c, 16 (3): 105-140.
[54]Imajima M. Spionidae (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Japan, ⅤThe GenusStreblospioandDispio[J].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Museum, Tokyo (A,Zool.), 1990d, 16 (4): 155-163.
[55]Maciolek N J. A new genus and species of Spionidae(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Atlantic [J]. Proceedings of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81a, 94 (1): 228-239.
[56]Maciolek N J. Spionidae (Annelida: Polychaeta) from the Galápagos rift Geothermal vents [J]. Proceedings of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81b, 94 (3):826-837.
[57]Maciolek N J. New records and species ofMarenzelleriaMesnil andScolecolepisEhlers (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Northeastern North America[M]//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olychaeta Conferences. Sydney: published by the Linnean Society of New Wales, 1984a: 48-62.
[58]Maciolek N J. A new species ofPolydora(Polychaeta:Spionidae) from deep water in the North-West Atlantic Ocean, and new records of other Polydorid species [J].Sarsia, 1984b, 69: 123-131.
[59]Maciolek N J. A revision of the genusPrionospioMalmgre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species from the Atlantic Ocean, and new records of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generaApoprionospioFoster andParaprionospioCaullery(Polychaeta, Annelida, Spionidae) [J].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985, 84: 325-383.
[60]Maciolek N J. New species and records ofScolelepis(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the ea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with a review of the subgenera [J]. Bulletin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87, 7: 16-40.
[61]Maciolek N J. A redescription of some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generaSpioandMicrospio(Polychaeta: Annelida) and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species from the northwestern Atlantic Ocean [J].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1990, 24: 1 109-1 141.
[62]Maciolek N J. New species and records ofAonidella,Laonice, andSpiophanes(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shelf and Slope depths of the Western North Atlantic[J]. Bulletion of Marine Science, 2000, 67 (1): 529-547.
[63]Blake J A, Kudenov J D. The Spionidae (Polychaeta)from southeastern Australia and adjacent areas with a revision of the genera [J].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Victoria, 1978, 39: 171-280.
[64]Wilson R S.PrionospioandParaprionospio(Polychaeta:Spionidae) from southern Australia [J].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Victoria, 1990, 50: 243-274.
[65]Read G B. New deep-sea Poecilochaetidae (Polychaeta:Spionida) from New Zealand [J].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1986, 20: 399-413.
[66]Williams J D.Polydoraand related genera associated with hermit crabs from the Indo-West Pacific (Polychaeta: Spionidae), with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and a second polydorid egg predator of hermit crabs [J]. Pacific Science, 2001, 55 (4): 429-465.
[67]Sigvaldadottir E. Cladistic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Prionospioand related genera (Polychaeta, Spionidae) [J].Zoologica Scripta, 1998, 27 (3): 175-187.
[68]Rouse G W, Pleijel F. Problems in polychaete systematics [J]. Hydrobiologia, 2003, 496: 175-189.
[69]Bochert R. An electron microscopic study of spermatogenesis inMarenzelleria viridis(Verrill, 1873)(Polychaeta; Spionidae) [J]. Acta Zoologica (Copenhagen), 1996, 77(3): 191-199.
[70]Jelsing J. Ultrastructural studies of dorsal ciliated organs in Spionidae (Annelida: Polychaeta) [J]. Hydrobiologia, 2003, 496: 241-251.
[71]Radashevsky V I, Lana P C, Nalesso R C. Morphology and biology ofPolydoraspecies (Polychaeta: Spionidae)boring into oyster shells in South America,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J]. Zootaxa, 2006, 1353:1-37.
[72]Wielgus J, Levy O. Differences in photosynthetic activity between coral sections infested and not infested by boring spionid polychaetes [J]. Journal of the Marine Biologic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2006, 86 (4): 727-728.
[73]Manchenko G P, Radashevsky V I. Genetic evidence for two sibling species withinPolydoracf.ciliata(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the Sea of Japan [J]. Marine Biology (Berlin), 1998, 131 (3): 489-495.
[74]Manchenko G P, Radashevsky V I.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ibling sympatricDipolydoraspecies(Polychaeta: Spionidae) from the Sea of Japan, and a new species description [J]. Journal of the Marine Biologic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02, 82(2): 193-199.
[75]Zhou J, Li X Z. Records ofPrionospiocomplex (Annelida: Spionidae) from the Chinese waters,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2009, 28 (1): 116-127.
[76]Williams J D. New records and description of four new species of spionids (Annelida: Polychaeta: Spionidae)from the Philippines: the generaDispio,Malacoceros,Polydora, andScolelepis, with notes on palp ciliation patterns of the genusScolelepis[J]. Zootaxa, 2007,1459: 1-35.
[77]黄宗国. 中国海洋生物种类和分布[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4: 764.
[78]刘瑞玉. 中国海洋生物名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9: 1267.
Q958
A
1000-3096(2011)06-0082-08
2010-12-09;
2011-0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06084);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No. 2008M16)
周进(1981-), 男, 安徽合肥人,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海洋生态学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分类学研究, 电话:021-65684690-8199, E-mail: zhou_jin@foxmail.com; 李新正, 通信作者,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员, E-mail: lixzh@qdio.ac.cn
致谢: 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李宝泉博士和王金宝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安建梅博士、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韩庆喜博士在作者从事多毛类研究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帮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生物研究所Vasily I. Radashevsky博士为作者提供大量重要的多毛类文献资料, 日本国立水产养殖研究所Hisashi Yokoyama博士、马萨诸塞州能源与环境研究所Nancy J. Maciolek博士、赫福斯特拉大学生物学系Jason D. Williams博士在作者已有分类学论文发表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梁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