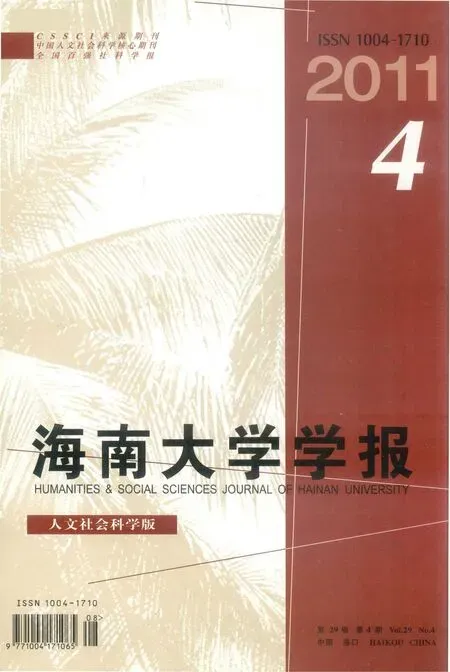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李西臣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李西臣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我国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以及“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等理论都已表明,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路径,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功能和特殊性,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应是综合性的问责,即构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的综合“责任集合体”及有效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宏观调控受体信任、遵从调控主体的引导以达到调控目标”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实现。
宏观调控主体;问责;法律问责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先后进行了7轮宏观调控,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我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彰显宏观调控法理基础的薄弱,尤其是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的缺失。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体现,是现代民主政治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主体利益诉求的必然反映。然而,“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中国化国民经济管理术语有别于日常的政府经济管理行为[1],因此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问责。
一、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理论
现代法治“不复仅仅是公民的准则,而且成了统治者所需要遵循的准则”,它要求法律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2]。法的双向运行模式要求法的制定和运行不仅是从政府到一般民众的过程,更是从一般民众到政府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关系中,调控受体在积极配合调控主体的调控措施的同时还应当享有正当的权利,如自主选择是否遵从调控主体推出的调控政策的权利、对涉及调控受体利益的决策的参与权、对调控决策的形成和执行的监督权、对调控行为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请求权等。对宏观调控主体问责除了督促政府及其官员为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为,也是保障调控受体合法权利的应有之义。
(二)公共选择理论
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政治家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必然会为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为。然而政府及其代理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惟一追求仅仅是理想的应然状态,现实的实然状态并非如此。据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同样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宏观调控主体而言,虽然其终极价值选择是社会公共利益,但政府官员的决策和执行同样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而调控主体问责制度有利于纠正和改进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非正式制度理论
非正式制度理论表明,经过长时间的自发演进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其变迁因而具有“时滞性”。与正式制度容易变迁不同,意图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非正式制度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我国,官员“位置优势”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因此,虽然经济体制向市场方向改革,权力再分配经济让位市场经济,意味着权力的转移、官员权力的衰落,但“官员优势位置”、“官本位”作为非正式制度却仍然在诸多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改革下发挥着绝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强调问责制度对于防止宏观调控官员滥用权力实属必要。
二、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的功能
一般而言,问责的功能有三种:惩罚功能、救济功能和预防功能。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制度也具有以上三种功能,但同时具有重要的特殊性:一是更突出预防功能,即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制度主旨在于增加调控主体违背遵循调控目标承诺的成本,以利于调控受体形成对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预期从而激励其遵从调控政策,该功能与民法责任中填补损失止于双方的矫正功能十分不同。二是宏观调控主体责任制度还在于保障约束调控主体权力滥用与科学、合理行使调控权力之间的平衡。宏观调控这项政府经济职能专业性强且极需智慧,需要充分调动调控主体的积极性和全方位的能力。然而调控的有效性与客观经济规律、其他社会发展规律等相契合,经济发展的复杂现实增加了调控政策的难度,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调控目标有一定的客观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于苛责的责任制度就可能束缚了调控主体主观能动性,使调控主体产生“不作为”的行为偏好,致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足。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政府及其代理人对宏观调控权的滥用,责任制度作为调控主体滥用权力的行为成本而存在一定要足以杜绝滥用权力,否则当滥用权力的收益大于滥用权力的成本时,宏观调控主体滥用权力就会成为常态。因此,科学、合理的责任制度应当是既有利于激励调控主体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调控政策,同时也足以减少甚至是杜绝宏观调控权的滥用。
三、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特殊性
(一)宏观调控主体实体违法认定的困难
调控行为的特性使得认定宏观调控主体实体违法存在困难。宏观调控是在“相机抉择”与“规则之治”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决策者事前宣布如何对各种情况作出反应,并承诺完全遵循这种宣布,那么政策就是按规则进行的。如果决策者在事件发生时任意判断并选择当时看来合适的政策,政策就是按相机抉择进行的。”[3]由于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相机抉择”,再加上宏观调控的高度专业性和临时性,因此对调控主体在实体上进行问责存在困难。
(二)对宏观调控主体处以自由罚的困难
自由罚的基础是主体行为的个体性,而宏观调控是集体决策的结果。基于集体决策的“公共负担原则”,对宏观调控主体施以自由罚并不恰当。“由于调制主体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如既是调制主体,又可能是行政主体或立法主体,等等),它在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作用十分显要,因而一般很难让它歇业、关闭,也无法对其处以自由罚。”[4]
(三)对宏观调控机构处以经济罚的不恰当
调控主体的财产属于财政范畴,若因其违背经济职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被处以经济罚,实际上是对用于公共目的的人民的财产进行处罚,即最终的不利经济后果由纳税人承担,调控主体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失。因此对调控机构处以经济罚违背了问责制度的初衷,并不合适。
(四)宏观调控责任的“非对称性”
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与宏观调控受体的责任具有“非对称性”或者“非均衡性”。虽然对调控主体和受体都设定了责任,但基于宏观调控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与受体地位的不对等性,对调控受体的问责无论是在归责原则、归责构成要件还是归责的具体方式上,都比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制度规定得更为详细和更具可操作性。
四、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体系
宏观调控过程的实质其实就是“调控主体引导调控受体遵循其调控政策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宏观调控主体问责制度就是要保障“调控受体信任调控主体”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顺利实现。为此,应依据各种问责形式本身的特点,构建以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为主的多元复合“责任集合体”。
(一)宏观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或者他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5]宏观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是指调控主体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调控受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
1.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内容 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实体和程序双重属性,对宏观调控行为的问责也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调控实体主要指宏观政策的选择,调控程序主要指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过程和步骤。一般而言,出现损害后果是法律责任设定所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对于宏观调控实体而言,若直接以宏观调控决策造成损害后果,或以其对宏观经济形势没有影响为依据来设定决策主体的法律责任承担是不合理的,相反对调控程序设定法律责任更为合理[6]。宏观调控的高度专业性和临时性特征使得对实体进行评价成本过高,而且对实体苛责容易激励调控主体产生不作为的行为偏好致使政府对经济干预不足,而历次调控的基本程序却相对稳定。并且宏观调控决策是一种集体决策,对集体决策后果的“公共负担原则”使得对调控程序的问责比对调控实体的问责更有意义。因此,对宏观调控主体的法律问责更多的是对调控程序进行问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调控实体就无法问责。
2.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宏观调控主体的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责任判断过程,为了充分发挥法律责任的功能,实现法的价值,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归结应当遵循合法、公正、有效、合理4个基本原则[7]。结合宏观调控的特点,本文认为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过错推定”原则。从广义上讲,宏观调控是一份调控主体与调控受体之间的合约。调控主体与受体的权、责、义、利与其所处的金融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宏观金融运行的易变性,使得确定一份明确的金融宏观调控合约存在莫大困难,因此金融宏观调控合约是高度不完备的合约,这份合约只能为主体和受体确定大致的法律框架,比如政府做出低通货膨胀的承诺,就不能中途为拉动经济而改为扩张货币政策。在这份高度不完备的合约中,政府作为主体具有技术信息的绝对优势,而受体除了从政府做出的简洁承诺获取信息之外并没有更加有效的信息渠道。并且,主体做出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时的主观状态受体难以观察,到底政府是应变“市场失灵”还是为自身利益集团行事都难以辨别;宏观调控往往又是集体决策的行为,让调控受体来证明调控主体的过错非常困难。因此让具有信息绝对优势的一方承担证明其没有过错的责任更加合理与公平。
3.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首先,具备宏观调控职能和责任能力的主体。从横向看具体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住建部、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等;从纵向看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次。从主体的形式上看,有宏观调控机关,即法人主体;也有具体履行宏观调控职务,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公务员。
其次,宏观调控主体行为违法。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经济职能,宏观调控权力的行使应当具有权威性,若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不是由法律事先规定而完全由自由裁量决定,势必造成宏观调控主体无法形成合理确定的预期,同时也容易影响调控主体调控的权威性。调控主体行为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而言,调控主体行为违法包括三类:一是调控主体不履行法定调控职责,消极的不作为状态使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减损;二是调控主体履行职责违反宏观调控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三是调控主体的职务行为超越法律规定。
再次,具有损害事实。此要件有以下特点:(1)损害的发生必须是受体遵从调控政策而发生。因为本制度的设计是鼓励受体遵从调控,鼓励受体与主体合作,那么对政府欲承担的损害赔偿自然是受体顺从调控而发生的损失。(2)损害是直接的财产损害。虽然本制度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但过于扩大的损害赔偿范围将激励政府做出不作为的行为策略,这很有可能会使政府“坐失”调控复杂经济形势的良机而造成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3)损害应当是确定的,即已经发生;客观存在而不是纯主观感觉或臆想,能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和公平意识予以认定[8]。
最后,因果关系采盖然性推论。金融宏观调控是一个专业信息密集的领域。专业信息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定义、方法,对其正确解码必须具备达到临界点的知识存量和相关参照系,共享程度较低的信息[9]。金融宏观调控中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蕴含大量金融学知识,对这些政策正确解码需要达至临界点的信息,因此让仅具备常识的公众对损害事实与违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严格的证明已经大大超过了公众的能力,若依严格因果关系认定责任那么本制度的设计将很可能难以运作而流于形式。所以政府承担违诺责任的制度中因果关系采盖然性因果关系。
(二)宏观调控主体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政治责任是指“政治官员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及没有履行好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10]宏观调控政治责任要求调控主体决策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符合、保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整体福利,如果调控主体的决策和执行行为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虽然不受法律明文规定的否定性后果,却要承担来自选出机构、选民、政党、专门监察机构、调控主体自身等多方的问责。
宏观调控的道德责任要求调控主体制定和执行调控决策必须符合社会公众所要求的道德标准与规范。B·盖伊·伊得斯认为:道德约束是强化行政职责的最后途径,这是可达到的最经济的控制形式,最终的也是最有效的形式[11]。同时,道德责任有利于防范调控主体做出调控承诺之后出现的道德风险。
(三)宏观调控主体的绩效责任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方面要取决于市场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要取决于国家职能的需要,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的干预能力和干预成本。”[12]绩效是对宏观调控主体的工作和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或产生的积极效果与所耗费的成本的一种评价。绩效责任有利于督促宏观调控主体降低调控“成本/收益”比率从而提高调控效率。传统的宏观调控往往注重调控行为本身和调控“投入”,对调控效果与“投入”之间的关系不太重视,这种情况容易出现浪费和官僚主义。对调控进行绩效管理,让调控主体承担绩效责任,是国家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的重要方式。
(四)宏观调控主体责任之间的关系
法律责任由于具有权威性和确定性而在问责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它通过确保“调控主体违背宏观调控承诺应承受强制的不利后果”来最有力地维护调控受体与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它维护的是调控主受体之间基于具体承诺的特定信任关系。法律责任要求“调控主体、行为与后果的关系”紧密、易于辨明。而对于宏观调控主体的诸多实体行为而言,由于宏观调控行为往往会与其他主体(其他宏观调控部门包括地方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等其他非宏观调控部门、市场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致使调控主体的调控行为与经济发展后果之间的关系即使依照盖然性也依然难辨,这就意味着法律问责方式在这类领域将难以适用。那么,对于那些法律无法问责但同样可能会产生调控主体信用减损的宏观调控行为,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则是最好的问责形式。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维护的是基础信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一个基本责任形式就是降低社会公众对调控主体在政治上的信任程度。基础信任的降低将直接恶化调控主受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基于“承诺—信任—守信”行为模式的宏观调控将难以为继。如果说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是从重在防止宏观调控出现不利后果方面维护信任关系,那么绩效责任则是从重在激励出现有效率的良性宏观调控方面正向促进主受体信任关系。
由此可见,在促进调控主受体良性互动上,四种责任形式从不同层次上规范着双方的信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宏观调控主体的四种问责是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当然,四种责任形式之间区别也是明显的。对宏观调控主体的政治问责较之法律问责而言:政治责任具有模糊性,政治责任更加原则和抽象,法律责任由于明文规定而更加确定;政治责任不能仅以专门的机关认定作为判定依据,而法律责任有专门的认定机关;政治责任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法律责任政治色彩远没有那么浓厚;政治责任具有连带性,而公法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不具有。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道德问责更多的是一种的“自律”,而法律问责却是基于强制力的“他律”。正是由于道德问责的内部约束力这一差异性特征和调控中“相机抉择”的客观存在性,使得道德问责能够对调控者的内心“留白”产生弥补性的社会控制功能。如果说前三种责任重在防止坏的调控者出现,那么绩效责任则在于促进好的调控者的形成。
五、宏观调控主体责任实施机制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问责机制主要有:《宪法》中的质询与询问机制,对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罢免和撤职机制,以及《宪法》和《立法法》中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监督机制等。总体而言,宏观调控问责机制尚不健全。为了完善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实施机制,首先,应考虑突破既有的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制度安排,增加调控受体维护合法权益、约束调控受体权力的途径,建立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复议和诉讼机制。其次,鉴于对调控主体实施经济罚不恰当,针对调控主体的惩罚就应突破物质赔偿形式。既然调控主体失效、错误调控行为的前提是调控权,那么责任的具体实施还应落实到促使做出修正的调控行为以弥补已造成的社会整体利益损失上来,如调控主体主动纠错之后的调控政策修改。并且,由于调控失败影响的是调控主受体之间的信任关系,那么责任的实施机制还应当有对调控主体信用评级机制。对调控主体信用级别的升降一方面有利于激励调控主体的合理、科学调控,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决策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再次,建立政党问责机制,健全选民问责机制(包括质询、调差、不信任投票、弹劾、罢免等一系列手段),完善自我问责机制。最后,构建调控主体的绩效评估方法,督促调控主体制定战略规划、战略目标绩效管理计划,定期测定调控绩效并向全国人大及常委和公众提供绩效报告。
[1]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5):17-23.
[2]W I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32.
[3]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第4版.梁小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1.
[4]张守文.经济法责任理论之拓扑[J].中国法学,2003(4):13-24.
[5]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73.
[6]张德峰.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性质[J].政法论坛,2009(3):181-186.
[7]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72.
[8]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63.
[9]伯·霍尔茨纳.知识社会学[M].傅正元,蒋琦,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32.
[10]张贤明.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比较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0(1):13-21.
[11]B盖伊·伊得斯.官僚政治[M].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42.
[12]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4.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Micro-control Subjects
LI Xi-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Xihua University,Chengdu 610039,China)
More-than-30-year practices of micro-control in China and theories,such as healthy and bidirectional operation of modern rule of law,indicate that the accountability to micro-control subject is a very important path to perfect micro-control,and is also inevitable demand for responsible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of law.In light of the functions and particularities of micro-control subject accountability,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should be a comprehensive one,namely,a synthetic responsibility aggregation which consists of legal,political,moral and performance responsibilities,and include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its core behavior pattern,i.e.,to reach the target of macro-control by winning macro-control objects’trust and their obedience to the instructions made by subjects.
micro-control subject;accountability;legal accountability
DF 41;F 123.16
A
1004-1710(2011)04-0084-05
2011-01-21
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10SB077);西华大学重点科研基金人才引进项目(ZW1020701)
李西臣(1980-),女,湖北宜昌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金融法的研究。
[责任编辑:靳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