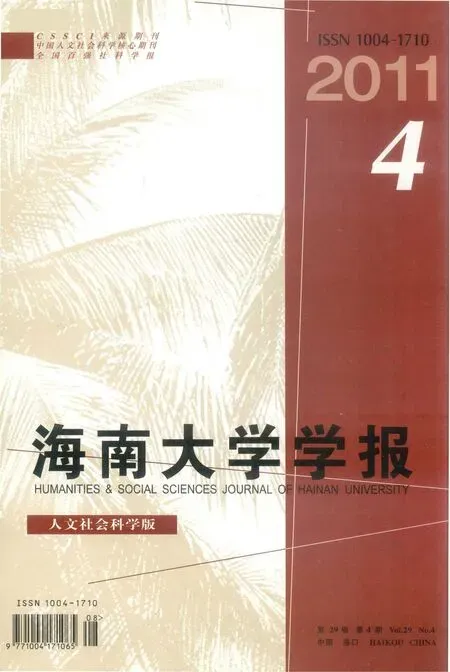论老年人的刑事诉讼保护
孙晓玉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论老年人的刑事诉讼保护
孙晓玉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犯罪愈发常见。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政策角度来看,都需要刑事诉讼制度给予特别对待。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仍然略显滞后,制度化、系统化不足,宽缓程度不够。有鉴于此,有必要综合考量,系统性地构建和完善旨在保护老年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
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中国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据相关研究报告,我国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17.17%;201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①我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就将60周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1996年《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2条也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在本文中,笔者采纳的也是这一标准。。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将会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老年人犯罪亦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②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 200人左右,而老年罪犯,1998年占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已占在押犯总数的2.1%;天津市社科院、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监狱管理局联合对天津市2002年和2003年当年入狱罪犯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60岁以上的罪犯占全部调查对象的比重为0.6%,2003年为0.8%。另外,关于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区的一项调查表明,截至2008年底,该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达8.27万人,占区总人口数的26.68%;2007年至2009年上半年,静安区检察院受理的涉及老年当事人的案件分别为50件、53件、29件,占同期受案总数的11%、12.4%、13.1%。前述数据,分别见吴宗宪、曹健、郭平、郭晓红、彭玉伟:《中国老年犯罪状况》,载于《老龄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蔡盛、林中明:“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积极探索老年人司法保护课题”,新华网:http:∥news.jcrb.com/xwjj/200912/t20091207_290018.html,2010年10月1日登陆。。在刑法领域,相关研究已对于如何在刑法中保护老年人有所涉猎③刑法领域的相关论著,可以参见赵秉志:《论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载于《法学论坛》,1988年第2期;徐光华:《老年人犯罪立法的宽容度度衡》,载于《求索》,2010年第2期;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刑罚问题刍议》,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周育平:《论老年人犯罪的特点》,载于《青年科学》,2010年第2期;张应立:《人口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犯罪问题初探——以浙江省老年人犯罪为例》,载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审议的刑法第八修正案亦包括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对老年人犯罪轻缓处理的规定④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不满18周岁的人和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过,从刑事诉讼角度研究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保护问题,目前尚不多见⑤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现有研究基本上从实体角度展开分析,最多附带地提到部分的程序改革措施,尚没有专文从程序上研究对老年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附带提到程序改革措施的论著,详见宋赟:《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老年人权益保护》,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徐光华:《老年人犯罪立法的宽容度度衡》,载于《求索》,2010年第2期;李益明、朱雪平、郭林将、王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犯罪研究》,载于《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2008年第1期。。有鉴于此,笔者斗胆作文,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起更多有益的讨论⑥需要说明一点,本文关注的是老年人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保护,而并不研究老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诉讼保护,因此在文中笔者所说的老年人即是指老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的理论与政策基础
由于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属于较新的课题,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除了通常的人权保障理论之外,笔者在结合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总结,认为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还有如下理论和政策基础。
(一)关怀理论
关怀理论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正义理论在面对时代变化渐显局限性之际兴起的。其基本看法是:传统的正义理论具有重分离轻联系、重理性轻情感、重普遍原则轻具体情境等特点,凸显的是一种抽象的冷冰冰的制度观念;而关怀理论关注关系、情感,注重因情境而异、因人而异,强调对具体情境中特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情境的反应及体验,强调的是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处事理念[1]11-30。关怀理论中关怀的要义在于对某事或某人负责,保护其利益、促进其发展[2],核心在于“爱”与“责任”。关怀理论作为道德领域的一个新兴理论,一经提出就逐渐超出了道德领域,如今已经进入了包括法律领域在内的诸多社会政治生活领域。
在笔者阅读和研究关怀理论的相关著作时,发现关怀理论对于老年人的诉讼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价值。传统刑事诉讼主要看重的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报应型、惩罚型正义,表现出的主要是一副非人格化的如“机器”般的面孔,其并不关心被惩罚者是老人还是普通成人,当然也不关注二者可能存在的区别。关怀理论使我们注意到,建立在惩罚基础上的刑事诉讼正义尽管必要,却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特别明显的方面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对老年人之特殊性和情境性感受关照不够,使得风烛残年的老年人不仅要直面刑罚的可能痛苦,还要面对刑事诉讼过程机器般的冷漠。这对于本已暮年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显得过于肃杀乃至不人道,从而最终达不到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⑦这其实也就是爱与正义分离的果,关于这种分离造成的悲剧,请见李猛:《爱与正义》,载于《书屋》,2001年第5期。。
关怀理论不仅让我们注意到传统刑事诉讼正义观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尽力将爱、责任与正义结合起来,在实现正义的同时尽可能关心、照顾有特殊需要的人。具体到老年人,就要求:一方面,在理念上,在处理老年人犯罪问题时,应当随时带有爱与责任之心;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应当充分关照老年人的特殊性,包括:其一,由于生理衰老,老年人动作和学习速度减慢,操作能力和反应速度降低,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加之记忆力和认知力减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衰退,他们参与刑事诉讼时,应当获得相应的特殊照顾;其二,由于生理功能衰退,老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反应速度都亚于成人,在此情形下,刑事诉讼亦应当给予老年人特殊关怀。
其实,如果追根溯源,中国古代早就有着丰富的关怀实践,尤其体现在对老年人的“怜恤”上。纵观我国古代刑事司法史,从最早西周的刑事法律“耄悼之年有罪不加刑”,春秋战国时期“老幼犯罪减免刑罚”、汉朝的“恤刑原则”到唐朝的“矜老恤幼”等,均素有悯老恤老的传统,并不乏对老年人怜恤的诸多规定。虽然古代刑事司法缺乏程序层面的关怀实践,但是作为一种传统,无疑仍为当前刑事诉讼领域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怀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
(二)弱势群体保护理论
弱势群体保护乃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生理、自然或者社会原因,在社会生活中权利有欠缺或实现权利有障碍的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3]。目前中国学者将弱势群体主要分为三类:生理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生态脆弱地区的居民和灾民、下岗工人、失业者等⑧相关论著,可以参见苏力:《弱者保护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切入》,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冯彦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论纲》,载于《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任云兰:《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载于《南方论丛》,2006年第2期;任丽丽、李瑾、刘凤云:《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载于《武汉学刊》,2008年第3期。。国外学者则一般认为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贫困者,移民、老年人、妇女、儿童等⑨相关论著,可以参见徐令彦:《国外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载于《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6期;Mary De.Chesnay&Barbara A.Anderson,Caring for the vulnerable:perspectives in nursing theory,practice,and research,second edition(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inc.,2005),pp.3-5;Lei Yu Shi&Gregory D.Stevens,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ohn Wiley&Sons inc.,2005),p.2;Paul Richard Katz et al.(eds.),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 the long term care continuum,vol.v(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2004),pp.7-14.。《世界人权宣言》也将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列为人类的弱势群体10见《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总的来看,无论中外理论还是国际文件中,老年人都属于弱势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老年人保护在内的弱势群体保护理论之基石在于罗尔斯的差别平等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是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但是将平等的权利赋予给每一个人,不考虑每个人的特性和不可通约性,这是不明智的”[1]75,因此需要差别平等,即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基于社会成员实现权利的能力不同,对权利的分配予以调节,使之最大限度地保护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成员,因为“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惟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4]对弱势群体给予差别对待即保护的实质,乃在于以“不平等”求平等,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与正义。
基于差别平等原则的弱势群体保护理论对于老年人诉讼保护具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意义。正如上面关于弱势群体的界定和说明所表明了的,无论是在国内外的理论还是国际条约的规定中,老年人都属于公认的弱势群体之一。对于刑事诉讼而言,这就要求刑事诉讼重视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这一事实,并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给予老年人以特别的保护措施,否则就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对待。事实上,我国刑事诉讼已经在未成年人、盲聋哑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在老年人保护上亦有一些举措,只是关于后者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改革。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其讲究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实体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实施,以及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不仅要求从实体上,也要求从程序上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刑事犯罪及其行为人,从而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显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就是区别对待、宽严得当,而区别对待、宽严得当的依据则在于具体案件的具体特点,以及区别对待的总体效果。
老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对老年人偏重于宽,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能达到好的整体效果11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排除对于对极少数社会危害性大,人身危险性高的老年人从严处理。因为这同样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只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宽缓是原则,从严是例外。。具体而言,一方面,对老年人犯罪处理偏宽不会有大的负面效果。老年人由于年龄较大受生理、心理能力的限制,拒捕、毁灭证据、逃逸等危险较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可能性较小,再犯能力较弱,对其采取比较宽缓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起诉、暂缓起诉、和解以及缓刑等宽缓处理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另一方面,对老年人犯罪处理偏宽积极意义明显。老年人经过成人期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已经固化,要对其进行改变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他们按照同成年人一样进行诉讼程序效果并不明显,不但创造社会价值的可能性不大,反而由于其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国家必须专门配置资源来照料其身体与生活,从而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相反,对老年人采取比较宽缓的刑事政策,如能不拘的尽量不拘,能不捕的尽量不捕,能和解的尽量和解,能缓刑的尽量缓刑,不仅可以节约诉讼资源,助益于老年人需要的切实满足,而且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尊老悯老文化的培育,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二、现行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制度及其不足
(一)现行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制度及其特点
我国现行法律中老年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各种位阶的法律文件中。《宪法》第45条第1款和第49条第3款规定了对老年人权益的保障,《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则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规定了老年人的保护问题,但是这部法律缺乏关于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的内容。在刑事法领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老年人保护的专门规定,不过最高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2006年)、《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2006年)以及《不起诉案件标准(试行)》(2007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2010年)中零星存有一些关于老年人特殊待遇的规定。概括以上规定,现有制度在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上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初步体现了老年人保护理念。如前所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并没有关于老年嫌疑人、被告人的专门规定。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在逮捕、不起诉、量刑建议以及办理速度上对老年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别关照12请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最高检察院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7条、第8条。,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在量刑上对老年被告人的特别对待等13请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1条。,均使得老年人诉讼保护在制度上从无到有,保护理念得到初步体现。
另一方面,对老年人的诉讼保护具有一定的全面性。纵观相关司法解释,不难发现,老年人保护的精神实际贯穿了刑事诉讼几个最为重要的阶段。比如,在逮捕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对老年人慎重适用逮捕措施;在审查起诉阶段,亦明确要求“对于……老年人犯罪以及……等纠纷引发的案件,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确需提起公诉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方面的意见”,并在《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进一步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条件的案件,同时是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依法决定不起诉”;在审判阶段,最高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1条也提出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酌情予以从宽处罚”。涵盖逮捕、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的老年人诉讼保护规定,虽然不够详细系统,但是却表现出了司法机关欲全面关照老年人特殊需要的努力。
(二)现行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制度之不足
由于我国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难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总体较为滞后,前瞻性不够。应当说,当前老年人犯罪问题已经较为严重(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将更为严重),对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犯罪的处理,目前的制度虽然能够应付,但是总体上已显滞后,这主要体现在目前的制度设计尚未明确提出老年人保护的理念,一些前沿理论如关怀理论等尚未引起重视,尚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老年社会对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冲击。
其次,系统化、制度化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全面性,但是系统化、制度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一,相关司法解释主要采用的是分散式规定,相关保护措施散见于各个条文中,缺乏统摄老年人诉讼保护全局的原则、政策性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其二,在诉讼架构上,纵向上仅包括了逮捕、起诉、量刑三个阶段,对于侦查尚未涉及,横向上仅包括了起诉和审判,而没考虑辩护问题;其三,在具体手段和措施上,一些新近的制度发展尚未引起注意,量刑调查、刑事和解等均未提及。
最后,在具体制度上,没有充分关照老年人的特殊性。尽管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但在目前的刑事诉讼中,一方面,处理老年人犯罪的大部分程序与普通成年人相同,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尚未将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看待,与普通成年人犯罪相较,相同处理仍是原则,区别对待则是例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沿袭目前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与目的,对老年人犯罪的处理,惩罚仍然是主流,关爱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缺乏对较为成熟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的借鉴,宽缓仍显不足。
比如,在侦查讯问上,未借鉴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相关规定,对老年人特性关照不足。在一定意义上,老年人与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上具有共通性。未成年人处于生命体力和智力的生长发育期,其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全部依赖家庭和社会提供,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是社会的特别保护群体。而老年人身心发展处于逐渐衰退的过程,也是弱势群体之一,属社会应当给予特别保护的群体[5]。同为弱势群体,同为应受保护受关爱的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4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2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141条对讯问未成年人作了特殊规定,但对讯问老年人则与讯问普通成年人的规定完全相同,没有体现任何区别。
再如,在起诉上,针对老年人的不起诉条件亦略显过窄。一如前述,老年人由于年龄较大受生理、心理能力的限制,拒捕、毁灭证据、逃逸等危险较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可能性较小,再犯能力较弱,对其采取比较宽缓的不起诉、暂缓起诉的社会危害性不大,至少较成年人危害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形下,现行制度将老年人不起诉条件设置得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无疑是以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
另如,在辩护上,因为没有确立针对老年人的指定辩护制度,使得老年人在审判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37条对应当或者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均不包括老年人。很明显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诉讼行为能力会受到不利影响并渐趋弱化,自我辩护的能力极为有限。在缺乏指定辩护又无力自我辩护的情形下,无力聘请辩护律师的老年人无疑将在审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具体制度层面,当前刑事诉讼在老年人保护上宽缓不足的表现远非上述三例,此处之所以仅择其要者例举之,实乃因为下文马上将要从制度建构的层面系统性地关涉相关问题。
三、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制度之建构
经由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目前老年人刑事诉讼保护制度亟待完善。就此而言,笔者的总体思路是,以保护、关怀为基本理念,条件成熟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关于老年人保护的专门规定,同时借鉴未成年人保护的做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门的老年人保护司法解释。具体的制度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在侦查阶段,确立侦查讯问老年人时通知老年人的配偶、成年子女或者其他成年直系亲属到场的制度,明确讯问老年人可以在侦查机关进行,也可以到老年人的住所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
一方面,对老年人传唤、讯问时,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通知老年人的配偶、成年子女或者其他成年直系亲属到讯问现场。老年人由于身心方面的原因,在面对侦查机关调查时,情绪可能极不稳定。其配偶、成年子女或者其他成年直系亲属在场不仅可以缓和老年人的不稳定情绪,也可以防止侦查人员对老年人进行诱供、骗供或者逼供。
另一方面,对没有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老年人,一般情况下对其应在侦查机关进行讯问。但如果老年人因为生病、行走不便或者其他生理原因不能及时到侦查机关接受讯问的,侦查机关应当关注老年人的特殊情况,根据具体情形到老年人的住所、医院等适当地点进行讯问。
2.在逮捕与起诉阶段,将年老作为不予逮捕的重要因素,放宽老年人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将年老明确纳入暂缓起诉的考量情形之列。
其一,关于将年老作为不予逮捕的重要因素。由于老年人生理上的限制,人身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较普通成年人低得多,不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相应地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大。因此可以在现行司法解释“慎重逮捕”老年人的精神指引下更进一步,将年老明确作为考虑是否有逮捕必要的重要因素,并规定对于75岁以上的老年嫌疑人,原则上不采取逮捕措施。
其二,关于放宽老年人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当前,老年人犯罪的相对不起诉仍然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但该条规定条件较为严格,能适用的案件范围狭窄,几乎不能体现老年人的任何特殊性。这无疑不利于老年人的刑事诉讼保护。笔者建议,对老年人犯罪,可适当放宽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将老年人相对不起诉的条件修改为: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决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还可以规定,对于75岁以上的老年嫌疑人,符合前列条件的,应当不起诉。
其三,关于针对老年人的暂缓起诉制度。所谓暂缓起诉,一般是指检察机关对符合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以后,为了促使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服务社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要求其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约定的义务,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义务,检察机关就不再对其进行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否则检察机关就会对其提起公诉,要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6]。目前,暂缓起诉已经在不少地区试行,效果良好,相关研究也比较充分。笔者结合本文老年人保护主旨,认为当前要做的,一是要尽快将暂缓起诉上升为法律,至少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下来;二是在暂缓起诉制度中,将年老本身作为适用暂缓起诉的重要考量情形。
3.在审判阶段,建立老少法庭,将指定辩护扩大到老年人,确立老年人量刑调查制度。
其一,关于建立老少审判庭。众所周知,未成年人犯罪由专门的少年法庭审理。那么对于老年人犯罪,是否需要专门设立老年人法庭呢?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笔者认为,专门设立老年人法庭没有必要,而是建议将少年法庭改造为老少法庭。少年法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较其他法庭,其审判人员更具责任心和关爱之心,该特点使得其不仅有助于教育、挽救少年被告人,也有利于更为合情合理地对待老年被告人,助益于引导和排解老年人的情绪问题,使老年人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与重视,从而积极配合法院的工作,促使案件得以顺利解决。有鉴于此,完全可以一举两得的将少年法庭更名为老少法庭,统一审理少年案件和老年犯罪案件。
其二,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指定辩护。如前文所述,由于老年人的特殊生理心理状况,不确立针对老年人的指定辩护制度,可能使得老年人在审判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开庭审理时,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考虑被告人身体素质、精神健康状况以及知识水平等,酌情为其指定辩护人;对75周岁以上的老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其三,关于量刑信息调查。当前制度中,除了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确立了量刑调查制度外,其他案件一律没有采用量刑调查制度。笔者认为,对于老年人犯罪,可以借鉴未成年人量刑调查制度。量刑调查的内容应当包括老年人犯罪前的日常表现、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医疗经历、犯罪前科、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老年人的精神状态、生理状况以及犯罪后的表现等方面。
4.在老年人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广泛适用刑事和解。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7]。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理论,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也无论被害人是否提出终止刑事追诉的要求,这种由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都要进行下去,而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的影响和左右[8]。然而,近年来兴起的刑事和解实践方兴未艾,打破了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桎梏,赋予加害人与被害人较大的自主空间,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在笔者看来,基于刑事和解的巨大优势,为了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利益,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非常有必要在老年人犯罪处理过程中广泛适用刑事和解。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与未成年犯罪相比,老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适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从老年人的特殊生理心理特点和中国悯老恤老传统来看,在老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无疑有着极为广阔的空间,其积极效果可能并不逊色于未成年犯罪的刑事和解,并较普通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更为明显,同时也可能更易达成和解。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时,不妨从制度上鼓励各个主体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广泛适用刑事和解,以便在助益于刑事和解积极效果最大化的同时,更为合情合理地保护老年人这一刑事诉讼的特殊群体。
[1]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赵雪霞.西方教育模式的比较:正义与关怀[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院,2008.
[3]冯彦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论纲[J].当代法学,2005(4):37-43.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104.
[5]李莉,郑胜利.老年犯罪应适用从宽处罚原则[J].中国司法,1999(8):34.
[6]肖仕卫.刑事法治实践中的回应型司法:从中国暂缓起诉、刑事和解实践出发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4):17-29.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5):3-14.
[8]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第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lderly Peopl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SUN Xiao-yu
(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With the coming of aging society,the elderly crime is increasingly common.As a special group,from both theoretical or policy perspective,old people need special treatmen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At present,the relevant judicial explanations have made certain effort,which is still slightly lagging behind,institutionalized,insufficiently systematic,and relief-lacking.So,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and systemically construct and perfect the investigation,prosecution and trial system to protect the elderly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the elderly people;criminal proceeding;protectiont
D 925.2
A
1004-1710(2011)04-0078-06
2010-12-13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项目(SC09Z003)
孙晓玉(1983-),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
[责任编辑:王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