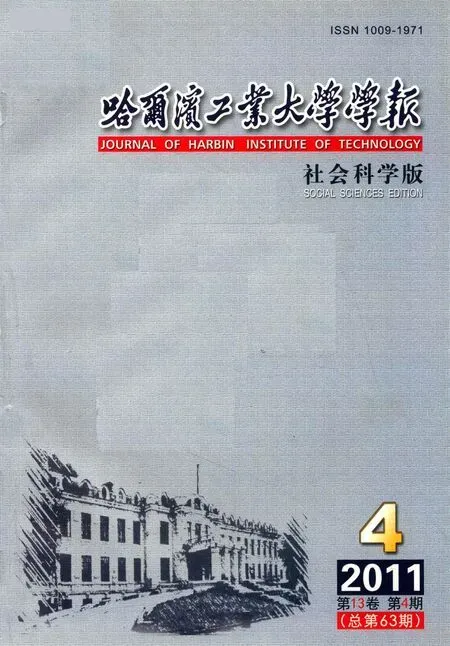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何坤翁
(武汉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武汉 430072)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何坤翁
(武汉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武汉 430072)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明代文学;洪武;朱元璋;台阁体
明代的台阁体是以杨荣、杨士奇为代表作家的。他们主要活动在从永乐后期到正统初的时段。纯粹以文学方式来讲述台阁体,应当直接从永乐后期开始,也可以斩断一些无谓的文学纠葛。但是,明代初期的两件重大政治事件,建文新政的失败与重修太祖实录,迫使我们从洪武时期来追述台阁体的政治起源,因为台阁体文学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是文学的。建文新政与永乐统治,是以对洪武制度的态度差异相区别的,永乐帝对洪武理念的执守,造就了台阁体。台阁体的种子,由洪武帝亲自埋下。
一、恢复儒家叙事传统
朱元璋信奉儒家道德,是程朱理学的推行者。早年在军旅中,宋濂便恒侍左右,为朱元璋讲授理学,包括《春秋左氏传》和《尚书》。对宋濂宣说的儒家教义,朱元璋“悉称善”。
天下一统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在全国推行儒家教义。洪武二年十月,诏令天下府州县都设立学校。他谕中书省臣说:“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兵革以来,人习战斗。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1]这是一种学制上的创举。徐一夔《德庆府端溪县新建庙学记》说:“皇朝既一四海,乃洪武二年冬,制诏州县兴学。且监前代虚文之弊,严立教条,限以岁月,务底成效。于是天下风动,凡有民社之责者,莫不知兴学,而人亦莫不知务学矣。”[2]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秀才》条说:“府县学生员之制,始于明太祖。欲令人才一出于学校,于是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副以训导。其生员之数,府四十,州、县递减其十;月廪人六斗。其后命增广员数不拘额。”[3]
洪武帝鉴于元人不重儒术,礼崩乐坏,享国不足百年,他要将江山传之万代,就不能不大兴教化,推广程朱理学。理学作为官方意识,是由朱元璋的明王朝开始的。但知识分子对理学的尊崇,在元代中叶已经发生,一直持续到元末,只是得不到元朝廷的积极回应。
依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读书人如果舍弃释道两途外,便只有习儒,别无其他可以安顿生命。释道崖岸高绝,不能成为生命力展放的常态。儒家学说作为主要的生命力吸纳机制,却被元朝廷等闲视之,使得大量的读书人将身心托付给儒家学说后,无法入仕,只能转而寄情山水,以儒家的心态步履释道的途辙。元代知识分子的这种遭遇,使他们的写作疏离了政治,最具有今天所说的文学意味,却偏离了儒家传统的叙事方式,按照儒家学者的看法,元代恰恰是一个不够文学的时代。关汉卿、杨显之、王实甫等剧作家的活跃,都证实了儒家叙述方式的衰微。
时至元末,著名作家杨维桢以诗文为艺,遭到了儒家正统派的批评。嘉定文人王彝针对杨氏文风,撰写了《文妖》,云:“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緑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4]四库馆臣评杨维桢《东维子集》云:“朱国桢《涌幢小品》载,王彝尝诋维桢为文妖。今观所传诸集,诗歌、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剪红刻翠以为涂饰,声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观其于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歧误,此岂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5]1462馆臣理解有误。王彝指斥杨氏者,不是其文章形式而是内容。《涌幢小品》卷一六《文淫妖》条云:“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为文本经术。会稽杨维祯,以文主盟四海,彝独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态惑人媚人,所谓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数百言诋之。”[6]从朱国桢所记来看,王彝是从内容上批评杨维桢的。王彝批评杨氏,正是当时文坛风气开始转变的信号,要从诗酒流连的艺文转为儒生入世的道德之文了。
儒家的书写传统是由《诗》、《书》、《春秋》等确立的,在美刺和实录之先,必须严华夷之辨。洪武政权占尽了华夷之辨的好处,朱元璋仅凭文明再造的身份,就足够在儒家史书系统中获得大写的形象。他对儒家书法又相当留意,有清醒的历史表演自觉,平时有意制造意义深刻的君臣对答,或者评价历史兴亡,或者发表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见解。
对于儒家主张的美刺,朱元璋只接受赞美,反对讥刺。删节《孟子》、罢孟子配享的事,足可表明洪武帝对儒家的选择态度。《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7]3982罢孟子配享,为明代著名事件,谈迁《国榷》、黄瑜《双槐岁钞》俱言之灼灼,《明史考证》又详加考辨。兹不赘述。《静志居诗话》卷二《苏伯衡》云:“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逮明孝陵,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若苏平仲、徐大章辈是也。当日有事圜丘,恶祝册有‘予’‘我’字,将谴撰文者。桂正字彦良言于帝曰:‘“予小子履”,汤用于郊;“我将我享”,武歌于庙。以古率今,未足深谴。’帝怒乃释。可谓善于悟主矣。惜未有为平仲调解者,竟瘐死于狱,悲夫!”[8]《廿二史劄记》有《明初文字之祸》,记洪武帝动辄以文字杀人[9]。这些可以见证朱元璋只接受儒家叙事主张的美,而反对刺。赵翼和朱彝尊所说的明初文字祸,或许言过其实,所举事例与史实有出入,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已经作过辨正。苏伯衡也不死于文字祸,黄云眉《明史考证》于《苏伯衡传》下有案语:“旧考:按开国臣传,伯衡卒于家,与此异。”[10]但空穴不来风,必是洪武帝一贯反感讥刺文字,疑心重重,史籍里才留下了民间的纷纷传言。
元朝的统治不足百年,蒙古人口数量很少,在生活风俗上对汉人的影响甚微。当时的民间习俗,各行其是。朱元璋被读书人视为扭转元胡风气的帝王,主要不是生活方面的移风易俗,而是恢复儒家学说的政治统治地位。他以制度方式保证了读书人的政治出路,树立了朝廷留心圣学的形象。由元入明的凌云翰,对此深有感触,其《送金元哲之官分水序》云:“圣朝之设科也,本德行而兼六艺,黜词赋而崇礼乐,盖有合于成周三物教民宾兴之意。若明经对策,则又斟酌汉唐之制而加详焉。是欲底于实效,非徒事乎虚文而已。一时之士,咸喻上意,莫不鼓舞奔走以报。”[11]洪武年代所立的科举,效果在永乐时就看得更清楚了。永乐年间的梁潜,在《溧阳县学乡贡题名记》中说:“进士之科,自隋唐距今几千年,贤豪俊义之出不可胜计。圣明统一万方,诏天下立学,既岁贡其士子之贤者,又取之以进士之科,此与成周乡举里选之法并行不废也。故今之得士也尤盛,至于熏陶消化使人人自趋于善,禁制防范使不失其性,则三代以下未尝有也。由是海隅边徼万里之外,皆翕然响应。”[12]
洪武革元旧制,读书人欣欣然地回归儒家的轨道,主张政治的文学,反对风月的文学。元末的文学疏离了政治,在明初人眼中就成了纤秾缛丽之物。洪武帝又不允许讥刺,儒家美刺叙事的双环,只剩了一个单边。两种因素合在一起,便只能颂美政以鸣国家之盛了,这为后来台阁体的兴盛埋下了种子。
二、《洪武大诰》及《皇明祖训》的威权框架
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评议明代台阁体时,多为台阁“三杨”的身份所迷惑,将台阁体与翰林制度及当时清平的政治相联系,指责台阁体脱离生活,而对一个基本事实弃而不顾:台阁体作家几乎都关心民瘼,对于底层百姓及国家前途的忧虑,比号称为爱国诗人的杜甫要深广得多。杜甫的忧虑国事只是政治旁观者的批评,是消极的意见;台阁体作家爱民忧国,则是躬自践行,意见总是建设性的。
考察台阁体,如果不能注意到台阁体作家群的普遍优秀品格,就是本质的失误。离开了写作者的那种卓越品质,台阁体将不复存在,只会沦为谄媚体。关心百姓,廉洁奉公,是台阁体作家群的共同品质,也是台阁体文学的内质。此种内质的形成,只能由洪武时代的文化精神才能得到说明。台阁体作家虽然从永乐后期才开始活跃,而所受教育则多由洪武文化熏陶而来。对此永乐皇帝也曾明言。《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九下“(建文)四年六月丁丑”云:“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数十年所作养者,岂建文二三年间便能成就!’”卷二三“永乐元年九月壬辰”云:“吏部尚书蹇义等言,太祖时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后复以罪黜,今有来告复职者,此于例不当复。上曰:天下人才,皆皇考所造就,为国家之用。朕即位以来,绍遵成宪,凡一才一艺悉用之。古称任官惟贤才,初兴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况出皇考所造就,岂得因建文尝用而遂弃之?自今勿复分别,但随才擢用。”
关心百姓和廉洁奉公,是洪武时代的基本精神。洪武皇帝出身贫贱,熟悉底层社会生活。为了保护小民百姓的利益,对于贪官污吏,他是深恶痛绝的。洪武十二年开始的胡惟庸案,是由惩贪引发的。此案坐诛者三万余人,受诛官员直接的罪名是谋反。其实,胡本人至死也没有显露明显的谋反迹象,此案在史学界被称作明代第一冤案。然而,受诛者尽是些贪顽不法、侵夺民利的官员,则是事实。
洪武十八年,胡惟庸案初告一段落,皇帝颁布了《御制大诰》。接下来的两年,续颁《大诰续编》和《大诰三编》。《大诰》及其续编和三编,由皇帝亲自撰文,全是站在普通百姓立场上,流露的情感至为真切。如《官民犯罪》条:“今后官民有犯罪责者,若不顺受其犯,买重作轻,买轻诬重,或尽行买免,除死罪坐死勿论,余者徙流、迁徙、笞杖等罪,贿赂出入,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以死,法司罪同犯者。此犯不分赃之巨微,除失错公罪不坐,凡私的决,并不虚示。”[13]要杜绝的是权钱社会的司法不公,直接受益者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为了让全体百姓知晓这部利民文册,《须行续诰》说:“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明史·太祖本纪》,说他“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评价是中肯的。
《洪武大诰》一类,属于治理官员的临时经验集录,类似法律案例,可供阅读者援引,这是朱元璋的外法。朱元璋另有一套内法,专门整治皇家事务,就是《皇明祖训》。从登极以来,朱元璋一直在思考传国万代的大经大法。六年五月,他的构想初步完成,编成《祖训录》。他亲自作序:“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14]
《祖训录》的写定要到二十八年九月,距离洪武帝驾崩仅两年多。皇帝日夜思考,随时损益,至此完备,便将《祖训录》改名《皇明祖训》,而且告谕天下:“后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论,毋赦。”
《皇明祖训》的民本思想十分突出,如云:“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风雨不时,则民不聊生,盗贼窃发,豪杰或乘隙而起,国势危矣。”云:“凡听讼要明。不明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久则天必怒焉。或有大狱,必当面讯,庶免构陷锻炼之弊。”又云:“凡广耳目,不偏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后大小官员,并百工伎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闻奏。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
《皇明祖训》虽然是写给继位的君王,而设定的读者对象不限于朱氏皇族。如:“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在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凡庶民敢有讦王之细务以逞奸顽者,斩,徒其家属于边。”御史、出差官员和普通百姓,必须平素知晓祖训内容,方能预为不犯。
以大诰和祖训为基本内容的洪武政教,具有无尚的威权。洪武之后的文皇、昭皇、章皇,都秉承祖训,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拥戴。洪武帝确立的政治框架,还培养了一批关心民命的台阁体作家。夏原吉、黄淮、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胡广等人,求学成长都在洪武时期,夏原吉和黄淮还是洪武间的进士,杨荣、金幼孜、胡广则是建文二年的进士,诸人都能执政为民,严于律己。《明史》夏原吉传记载,“尝夜阅爰书,抚案而叹,笔欲下辄止。妻问之。曰:‘此岁终大辟奏也。’”[7]4154金幼孜传记载,“幼孜简易静默,宽裕有容。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时,家人嘱请身后恩,不听,曰:‘此君子所耻也。’”[7]4127其余台阁作家,为人行事与夏、金两人相类。
祖训关于废止臣相的规定,对台阁体文风的形成尤其有影响。《皇明祖训》首章诸条,有一条云:“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它使得辅佐大臣必须阿依皇帝,不能自主行权,台阁诸臣位重而权轻,虽有经营天下之心,却铺排乏力。永乐年间,文皇一切尊从祖制,阁臣只聊备顾问而已。胡广随文皇北征,有诗《度紫微冈》云:“成功在庙算,一一由圣皇。嗟我乏远猷,谬忝侍从行。”是阁臣不能行权,且不能行谋的写照。于是,在永乐时代,阁臣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忝在禁林,职在纪述”,诗则弃言志而颂瑞,文则弃载道而鸣国家之圣。仁宗时代,阁臣虽不行权,但可以行谋,对于阁臣所议,仁宗多能依从。但无论如何,受朱元璋祖训的限制,明代阁臣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宰相。
洪武的清明政治,经过历史反思后,才更清晰地显露本色。景泰年间,马文升《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云:“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君临天下,慨彼前元纪纲沦替,彝遵倾颓,斟酌损益,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始著《大明令》以教之于先,续定《大明律》以齐之于后。制《大诰》三编以告谕臣民,复编《礼仪定式》等书以颁示天下。即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意也。当时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贵贱,各有等差,无敢僭越,真可以远追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之所能及矣。迨我太宗文皇帝克平内难,正位宸极,及至列圣相承,一遵成宪,恪守旧章,礼仪不紊,法令严明,人尚节俭,不事奢靡。至景泰年间,祖宗成宪所司奉行未至,风俗渐移。”[15]
三、提倡道德的政治的文学
洪武时代的威权政治,为永乐之后的台阁体准备了制度基础。如果离开洪武帝创立的政治管理结构,没有事先经过洪武时代的官员淘汰,留下给永乐朝的官员品质就不会那样整齐,就不会有台阁体的生存环境。台阁体需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洪武朝都已经具备,但台阁体文学没有出现在洪武朝。
朱元璋推广理学,偏重道德节操的修养和自律,对于儒家的文饰没有兴趣。经他亲手处死的文学家有高启、张孟兼。诗人杨基、袁凯都被放归乡里,危素被谪和州。这些是最著名的,其他知名文学家被杀被贬者,数量更多。
在儒家受尊宠的时代,哪怕皇帝不看重文学的治化功能,而由于儒生的政治本性使然,润色鸿业,文章华国总是成为知识界的自觉主张。明王朝一改元制,给了读书人政治出路,文人们在感激之余,普遍要求文章歌颂新朝的政治,摆脱元末纤弱的文风。
需要注意的是,元末文风更符合现代的文学标准。为了说清此一点,可以将话题稍微拉远。六朝文学,曾被指责为“兴寄都绝”,毫无骨力,遭到陈子昂的激烈抨击。陈子昂主张歌颂新时代的政治,他的《感遇》诗是标准的政治诗。但是,唐代的文学没有按照陈子昂的设想走下去。甚至政治热情高度亢奋的杜甫,也从六朝汲取营养,苦学阴铿、何逊等人的技巧。唐诗以兴象取胜,意在言外。唐文以词藻华丽的骈文为大宗,韩、柳古文是当时的异数,而且韩、柳二人有以文为戏的爱好,如《毛颖传》、《河间传》、《黔之驴》出于一时兴趣,初无深意。唐代传奇作者众多,从更普遍的角度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文学观念,文学是偏于艺,而非近于道,文学当以词章取胜,不宜凭说理定高下。唐代由于国力的强盛,其文学赢得了后人的认可,而六朝短命,其文学也备受后人责难。其实,唐文学与六朝文学无论在质感或是作家的创作倾向上都是接近的。李白诗中再三叹咏“大小谢”,足以表明唐文学与六朝的亲密关系。他也说陈子昂讲过的建安风力,“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最让后人误会。“建安骨”的代表人物是曹操和曹植,“七子”多是他们的亲密朋友。曹氏父子诗文直面现实,表现收拾山河成一统的志向,与一般文人的批评社会或赞扬统一安定根本不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整河山是曹氏的家事,“三曹”抒发的政治志向,是非常私人化的情感。如果位居下僚的文人,却歌颂国家的统一,揭露社会的丑恶,尽写些自己无力干涉的政治大事,那是谄政或谤政,绝不是什么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在于“三曹”文风,其核心是“三曹”抒发的政治理想,都是曹家的家事,虽然言政,仍等于言情。所以,建安风骨与六朝文风其实是旨趣相通,都以私人言说为尚。元朝的官方意识没有覆盖到民间,文化管制十分松散,元末文学是作家在看不到朝廷前途的环境下,干脆远离政治,歌酒流连的产物,自我抒发最多。诗宗盛唐,是元末文坛的呼声。这个呼声,一入明朝,马上消歇,要等到前七子崛起文坛时,才重新成为口号。可见,元末的文学,与唐文学的精神颇相通。只因为元朝的短命,并且元朝廷疏离儒家文化,元末文学又更疏离政治,遂被儒家学者贬为“纤秾”。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元末文学比明初文学更精致更深刻。
明朝一复汉唐旧制,评价标准回归儒家传统,元末文学差不多与六朝一样“绮丽不足珍”了。于是,转变私人化的情感文学,趋向社会化的政治文学,就成为明初文坛的呼声。宋濂为汪广洋的诗集《凤池吟稿》作序说:“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词之或异耳。濂常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曲以畅,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阙宫观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而镗鞳。”[16]宋濂在元末,隐居龙门山,著书立说,何尝不是山林之文?一旦归为朱元璋的文臣,便自觉地按照儒家方式来评价文学,抬高政治文学,明确主张文学为新朝廷唱颂歌,贬低疏离政治的山林文学。
朱元璋虽不重视文学,但对文学的政治性提出了要求。《翰林记》卷一一《正文体》云:
国初文体承元末之陋,皆务奇博,其弊遂浸丛秽。圣祖思有以变之,凡擢用词臣,务令以浑厚醇正为宗。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谓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直,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其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17]
朱元璋在军中自学儒家典籍,当登基时,他不仅能自如地阅读儒家典籍,而且能用得体的文言书写碑文诏令。以《尚书》为主的典谟训诰,是相当艰深的,韩愈就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话,而朱元璋对《尚书》领会很深,经常引用《尚书》条文来解释政治。以他的文化造诣,反对当时文士的险僻之语,肯定不会是看奏章时发生了阅读障碍。细味朱元璋对詹同所说的话,目的是要反对词章化情感化的文章,而主张文章要政治化道德化。他的主张还是消极的,不是积极地促进文学为政治服务,而是在文学如果继续存在的条件下,那就希望它们尽量政治化一些,不要成为词章的文学。
文人自己这一方面,比皇帝要积极得多,从开国之初,就要摆脱元末词章化的绮缛风气,做政治的文学。只要皇帝在文学上热心鼓动一下,明代的台阁体必然会出现在洪武时代。但是,皇帝对文学的态度冷淡。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准台阁体作家,就是吴伯宗。
吴伯宗,名佑,以字行,金溪人。洪武辛亥初开科,太祖亲擢第一,授礼部员外郎,历武英殿大学士,寻降检讨。有《荣进集》四卷,今存《四库全书》本。吴氏创作与台阁体关系甚大,其《荣进集》四库提要云:“其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5]1477清人说的明代台阁体胚胎于此,是从时间上划分,不含有因果相续的意思。永乐末期开始的台阁体,诸作家不必从吴伯宗受影响,尤其是杨士奇,在武昌一带坐馆时,苦自力学,文章已经法度谨严。他的文学才能得于《汉书》甚多。入史馆后,才可以读到吴伯宗的文章。
但是,《荣进集》作为一个准台阁体样本,是开启台阁体理解之门的一把钥匙,它表明了这样一点:台阁体不是文学自然演进的结果,不是文体的嬗变,而是皇帝威权与儒生的政治追捧相结合的产物。明代台阁体是以歌颂大明王朝,贬低元朝及宋唐为基本内容的。崇今抑古,以颂新朝,在《荣进集》已显端倪,如《送长山徐县丞序》云:“夫自国初以来,凡于士之仕者,或以贤良选,或以草莱进,拔茅汇征靡有遗焉者。用贤之广,前古未之有也。”《送梁伯兴赴苍梧太守序》云:“皇上建元洪武之四年,大兴文治,念民者国之本,长吏实民命所系,而承流宣化必得经术才能之士,知民疾苦而廉慎醇悫者,然后可居其位而称其职,乃诞降德音,旁搜广揽,甄别而用之,亲谕而遣之。责任之重,前古未之有也。”
要之,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时期,是为后世创规矩的时代,洪武之后的文化政治在《皇明祖训》和《大诰》的框范下运作,继位君王不同,持守祖法有宽严之别。永乐至正统初,朝廷恪守祖训,文学之臣,一尊皇权,是为台阁体。洪武帝对台阁体的影响,是制度生成式的,是根本性的影响。台阁体文学的潜流已经在洪武时代形成,到了永乐后期,终于冒出地面,开花结果。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204.
[2]徐一夔.始丰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580.
[4]王彝.王常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62.
[6]朱国祯.涌幢小品[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982.
[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41.
[9]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740.
[10]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4.
[11]凌云翰.柘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梁潜.泊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朱元璋.御制大诰[M].续修四库全书本.
[14]朱元璋.皇明祖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5]马文升.马端肃奏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汪广洋.凤池吟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黄佐.翰林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吴伯宗.荣进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郑红翠]
Emperor Zhu Yuanzhang's Important Effect on Literature of Tai- ge Style
HE Kun-weng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In early Ming Dynasty,as a result of tyrant politics,the literature of Tai- ge Style was created by the Emperor's authority and narrative regulation of Confucianism.As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Zhu Yuanzhang wrote the Imperial Mandate,Sermons From Forefather of Ming Dynasty,to tell his descendents how to control the country.His words and action was such a powerful effect on literature's growth that main features of Tai- ge Style even appeared in the time of Hongwu Emperor.
literature of Ming;Hongwu;emperor Zhu Yuanzhang;tai-ge style
I207.2
A
1009-1971(2011)04-0106-06
2011-04-07
何坤翁(1969-),男,湖北来凤人,副编审,从事明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