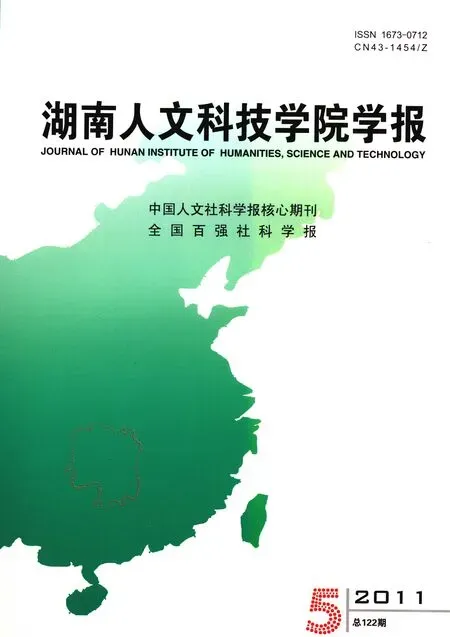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
吕 超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
吕 超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以“意义元素的多寡及其变异情况”为标准,可分为三大类:母题研究、题材研究和主题研究。母题是人类体认世界的最小意义单元,有着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是题材和主题的必备要素;题材是多个母题根据一定序列结构而成的有机体;主题则是作者根据题材立意而来的思想,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并随着文化观念的迁徙而演变。
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范畴;母题;题材;主题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类型,比较文学主题学主要关注同一主题思想及其相关因素在不同民族或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并进一步辨析、阐发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如果从十九世纪德国民俗学者的拓荒算起,主题学研究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依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譬如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主张分为三类:1)局面与传统的题材;2)实有的或空想的文学典型;3)传说与传说的人物[1]。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认为应分五类:1、典型情境;2)地理题材;3)传统描写对象,指植物、动物、非生物等;4)世界文学中常见的各类人物形象;5)传说中的典型[2]。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主张分为七类:题材、主题、母题、形势、意象、特性和惯用语[3]129。国内学者除借鉴韦斯坦因的观点外[4-6],还提出如下分类:主题、套语、意象、母题[7];母题、主题、情境[8];题材、人物、母题、主题[9];题材、母题、人物、意象[10]等。如此众多的分类方式,难免让初学者感到迷惘,甚至产生望而却步的畏惧心理。
仔细研读相关著作,笔者发现上述学者在陈述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时,许多并未细致阐述其分类的标准和学理依据,便直接给出了分类结果,难免给人以武断之嫌。众所周知,任何分类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参照标准,并且依据这个标准划分的各“子集”之间应最大可能地避免重复。本着这一原则,笔者在考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意义元素的多寡及其变异情况为标准,将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分为:母题(motif)、题材(subject matter)、主题(theme)三类。其中,母题是人类体认世界的最小意义单元,题材是一系列意义单元结构而成的有机体,主题则是作者根据题材立意而来的特色构思。其它如人物(figure)、意象(image)、情境(situation)、套语(topos)等研究对象,则依据其所含意义元素的具体情况,分属到三个门类之中。
1 母题
母题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最基本研究范畴。早在十八世纪,歌德就认为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3]140。到了十九世纪末,有“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称誉的亚·维谢洛夫斯基将母题视为“社会发展早期人们形象地说明自己所思考的或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最简单单位”[11]。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比较文学家弗兰采尔则认为:母题“是较小的主题性(Stoffich)单位,它还未形成完整的情节或故事脉络,但其本身却形成了属于内容和情景的成分。”[3]138仔细探究上述观点,我们不难找出其共同之处,笔者将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提炼出来,这也便形成了母题的狭义概念:人类体认世界的最小意义单位,即各类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行为等。显而易见,狭义的母题具有抽象、普遍、宏观的性质,如生命、死亡、道德、感情、义务、求索、空间、时间等。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认同德国学者保尔·梅克尔对母题数目的估计[3]139,但毋庸置疑的是,狭义定下的母题数目相对题材、主题而言,确实要少很多。
进一步推理,母题既然是人类体认世界的最小意义单元,那么它便是由“体认”这一行动衍生出的,而这一行动必然缺少不了主体和客体,否则母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里的主体和客体作为独立的意义单元,也应当属于母题研究的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母题的广义研究范畴。具体而言,广义的母题研究包括三类:人物母题、意象母题(自然环境)和情境母题(社会环境)。
人物母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保存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这类人物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某个母题的具体化身,其名字甚至就是某个母题的代名词,譬如浮士德代表着求索母题,精卫代表着锲而不舍母题,大禹代表着无私母题等等。另外一类则是从母题衍生出来的人物形象,如“贪婪”母题生发出来的各色吝啬鬼(如夏洛克、阿巴贡、葛朗台、泼留希金),这些人物反过来又成为狭义母题的形象代表。
所谓意象即“表意之象”,是人以情感体认事物时,意识中所呈现的形象,它“意味着对过去的感觉或直觉经验的重现或回忆,而并不一定诉诸于视觉”[12]。因此,意象作为自然环境的抽象和概括,不仅是视觉形象,还囊括触觉、嗅觉、听觉等形象。一般而言,意象“往往微不足道”,只有在“被有意识地重复或起巧妙的衔接作用时,才能成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3]148。譬如时钟、沙漏、日晷等意象都是“时间”这一狭义母题的具象化身。在特定文化体系中,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是稳定的,譬如古松代表着长寿,麒麟代表着吉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意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代表着不同的母题,譬如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皇权,而在西方的中世纪传统中则象征着邪恶势力。
情境(也可称作形势)一般被认为是人物在某个特定时刻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人生境遇。情境母题是经过高度抽象以后而形成的模式化、类型化的社会环境,如战争、变革、误会、复仇、三角恋等。这里举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比利时比较文学家雷蒙·图松认为母题“是指明一种情境,……,一种基本的非个人情景”,而韦斯坦因则认为“母题是从情境中来的”[3]139。二者观点之所以相互冲突,是因为其中的被定义项(母题)所指并不相同:雷蒙·图松认为的母题是指广义概念下的情境母题,而韦斯坦因认为的母题则是指狭义概念下的母题。
至此我们可以说,广义上的母题研究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狭义母题研究,例如王立对“生死”、“别离”等意义单元的研究[13];其二,人物母题研究,例如比利时学者雷蒙·图松对普罗米修斯的研究;其三,意象母题研究,例如乐黛云对不同文化中月亮意象的研究[14];其四,情境母题研究,例如法国学者乔治·波蒂尔在其著作《三十六种戏剧情境》中对戏剧情境的分析[15]。一般而言,狭义的母题作为最基本的意义单元,其含义是跨越民族文化界限的。换句话说,狭义母题在不同民族中的文化含义是大体相同的。比较而言,人物、意象、情境母题的含义则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例如龙的意象在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不同意义。但不管怎样,母题本身是客观性的常项,并不包含强烈的个人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这也正是母题与主题的最显著区别之一。
2 题材
众所周知,题材作为文学中的生活现象,在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作者一切立意、技巧的依托物,是主题的安身之本。也正是因为如此,题材一开始就成为主题学的重要研究范畴之一。在德国,早期的主题学研究甚至被称作“题材史”(Stoffgeschichte),即研究不同民族文化语境中相同或相似题材表现形态的异同,进而深入阐释其文化蕴藉。
就母题和题材的关系而言,母题是人类体认世界的最小意义单元,是题材的必备要素;题材则是多个母题依照一定序列组合而成的有机体。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题材作为生活现象,其内容包罗万象,并不只是“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或情节的素材”[16]。如果只将题材限制在叙事文学类型中,明显是一种画地为牢的短视行为。
就目前而言,题材研究中成果最多的是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题材研究。这里以神话题材为例。神话蕴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不同地区收集到的神话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神话同语言的其他部分一样,是由构成单位组成的,……,但是神话中的构成单位不同于语言中的构成单位,就像语言中的构成单位之间也不尽相同一样;神话中的构成单位更高级、更复杂。因此,我们将它们称为大构成单位”,并且“每一个大构成单位都由一种关系构成”[17]。其实,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这里所说的“大构成单位”也就是主题学研究中的题材。因为早期人类的生活境遇基本相似,所以各民族神话所包含的题材便有了颇多相通之处,譬如创世、造人、盗火等题材。当然,由于历史境况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在处理相同题材时也会有着具体细节的不同。譬如“神造人”题材,该题材在世界各重要神话体系中都有相关记述:在中国神话中,女娲抟黄土造人;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在古巴比伦神话中,马尔杜克用血造人;在古希伯莱,人们则相信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一男一女”(《创世纪1:27》)。由此可见,虽然同是造人,但创造者和造人用的材质却各有不同。
具体而言,比较文学主题学中的题材研究应当包括如下两个方面①:
其一,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传和演变情况。这种有实际影响关系的题材,是早期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重点。以“赵氏孤儿”题材在欧洲文学中的流变为例:《赵氏孤儿》是中国元朝纪君祥创作的一部历史杂剧,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故事情节来自司马迁《史记·赵世家》里晋大夫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和晋景公等人谋立赵氏孤儿的记载。1735年,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全文刊载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译文。而后,欧洲各国陆续出现了对该题材的改编本:在英国,先后有剧作家哈切待的《中国孤儿》(1741年)和谋飞的《中国孤儿》(1759年);在法国,有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剧《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1755年);在意大利,有诗人梅达斯塔苏的歌剧《中国英雄》(1748年);在德国,有歌德的未尽稿《埃尔佩诺》②(1781年)。众多改编本大都沿袭原著描写正义与邪恶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主题。唯独伏尔泰独辟蹊径,将题材重新加工,意在表现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在和解的结局中,洋溢着理性、仁爱和道德的光辉。当然,对伏尔泰剧作新意的研究,已经成为主题研究的范畴了。
其二,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中出现的相似题材。这类题材虽然内容相似,但却未必有着确凿的事实联系。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合理的解释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际遇是相似的,在特定时期,往往不约而同地使用相似的题材。这里主要介绍“二母争子”题材,该题材梗概为:两个女人共认一个孩子为自己的亲子,裁判者围绕孩子画一个圆圈,谁能把孩子从圆圈中拽出来,谁就是孩子的生母(或用利器将孩子劈为两半,二人各分一半),亲生母亲怕伤害孩子,只好放弃,裁判者据此推断出真相。这一题材在佛典《贤愚经》,希伯来《旧约·列王纪》,伊斯兰《古兰经》,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李行道),以及藏族古典文史名著《巴协》中都可以找到。到了二十世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高加索灰阑记》中,将故事改编为抚养孩子长大的女仆不忍用力,只好放弃,意在表现感情胜于血缘的主题。同样,对《高加索灰阑记》这一创新构思的研究也超出了简单意义上的题材研究范畴,进入了主题研究范畴。
在阐明了母题和题材这两个研究范畴之后,我们很容易辨析惯用语(即套语)的性质及其归属问题。有不少学者将其单独列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笔者则以为并没有这个必要。惯用语依据其所包含基本意义单元的寡众,可以分别纳入母题或题材的研究范畴。举例而言,如“漂泊的犹太人”、“洋鬼子”等套语可以归入人物母题研究范畴;而“南柯一梦”,“塞翁失马”等套语则可以归入题材研究范畴。
3 主题
顾名思义,比较文学主题学肯定离不开对主题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这里便无法回避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主题是什么?随着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发展,关于主题的定义也变得越发复杂:最初它以作者为中心,指基本思想;后来,形式主义者削弱了其主观说教性,把主题的根基从作者转移到文本上来;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含混不清,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18]。不过,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题应该属于文学的内容范畴,是作者通过题材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换句话说,主题是作者以特定的思想立场、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对题材加以倾向性介入后才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对母题和题材有所取舍、重构,甚至在特定语境中诠释出新的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对母题、题材、主题三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较全面的概括:母题是最基本的意义单元,在文学中反复出现,是题材和主题的必备要素;题材是多种母题组合而成的有机体,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母题和题材可以蕴含一定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一般的、抽象的、模糊的,而经过作家再诠释产生的主题才展现个别的、具体的思想,甚至会在特定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在三个研究范畴中,主题是最具主观色彩的,它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取向,并随着文化、观念的迁徙而演变。因此,比较文学主题学的主题研究范畴,是建立在对母题和题材研究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作家个案,明辨其作品的传统继承性和独创性,进而把握作家个性、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等因素。
具体而言,作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范畴之一的主题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作家对已有题材的再利用。如希伯来和希腊神话传说中都有“主母反告”题材,代表性的男主人公分别为约瑟和希波吕托斯,主母向他们求爱不成,则反咬一口。这无疑反映了母系社会瓦解时期,男性对女性作为主妇地位的颠覆意识。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拉辛依据该题材写成的悲剧《费德尔》,从主题上承袭并强化了这种倾向。但二十世纪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长诗《费德尔》,却对主母的处境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从乳母角度渲染费德尔的苦闷和无助,并批判希波吕托斯的冷漠。在这首长诗中,题材基本没有改变,但却成功颠覆了传统主题,成为现代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品。
第二,作家对一些人物母题的再加工。譬如西方作家对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的重新诠释: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虽然也描绘了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无畏反抗,但最终表现的是言归于好的世界观;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表现了基于博爱的民主思想和时代精神;二十世纪美国剧作家罗威尔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则意在强调现代人精神的复杂,以及存在的荒谬。由此可见,人物母题虽然相同,都是普罗米修斯,但所蕴含的主题却有了很大的差别。
第三,作家对一些意象母题的再处理。在文学作品中,意象常常以隐喻的形态传达出作者的文化心理、审美倾向和情感意识。例如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山”作为意象母题常常表达仁厚、宽善、稳定的意义。孔子说:“仁者乐山”,《韩诗外传》解释说:“山者,……,生万物而不私,育群物而不倦,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有似乎仁人志士,此仁者之所以乐山也。”古代文人常常隐修、游历于山林之间,在他们的诗词中,山总给人很强的亲切感和归属感。然而,山意象经过诗人的再处理,也可表现威胁、争斗等其它主题,如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十六字令》:“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已完全不同于山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所代表的“仁”这一思想。
第四,作家对一些情境母题的新诠释。这里以人们所熟悉的“三角恋”情境为例。一般而言,“三角恋”情境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多指有悖常理的道德观念,最多再加上一些浪漫、悲情和感伤的叙述色彩。但二十世纪法国作家萨特却给予“三角恋”情境以全新的阐释,在其独幕剧《禁闭》(1944年)中,萨特通过加尔散、艾丝黛尔、伊内丝三个灵魂之间的复杂爱恋关系,表现了存在主义的著名哲理:“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不难看出,萨特给“三角恋”情境赋予的全新主题是人们很难用传统常规思维构想的。
最后,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母题、题材和主题,三者是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强行分割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嫌。不过,在进行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时,从理论层面上作适当的区分则是必须的。只是任何分类都不应该“作茧自缚”,限制具体研究实践的探索和开拓。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终极真理,它总会随着实践的检验而不断调整。因此,笔者期待着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不断丰富发展,甚至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进而修正本文所做的分类。
注释:
①有研究者将“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出现的不同题材”作为第三种类型,见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但笔者以为,题材作为母题的组合,其形态变化万千,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其学理基础未免不足。再者,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方面的著述也很少。
②关于歌德是否模仿过《赵氏孤儿》,学术界说法不一。参见卫茂平《歌德〈埃尔佩诺〉是〈赵氏孤儿〉的改编本吗?》,载《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5期。
[1]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戴望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03-114.
[2]亚历山大·迪马.比较文学引论[M].谢天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95-100.
[3]WEISSTEIN U.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4]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95-105.
[5]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187.
[6]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4-223.
[7]陈鹏翔.主题学与中国文学[M]//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15.
[8]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23-129.
[9]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92-200.
[10]张铁夫.新编比较文学教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261-270.
[11]波利亚科夫.结构-符号学文艺学[M].佟景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74.
[12]WELLEK R,WARREN A. Theory of literatur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186.
[13]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14]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5-272.
[15]POLTI G. The thirty-six dramatic situations[M]. Boston: The Writer Inc,1944.
[16]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268.
[17]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44-47.
[18]MAKARYK I.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642-646.
(责任编校:文君)
OnResearchCateg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Thematology
LUC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f we take “the quantity and variation of meaningful element" as standard, the category of themat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motif, subject matter and theme. Motif is the smallest meaningful unit by which human cognize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with narrow and broad conceptions, it’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subject matter and theme. Subject matter as organism is constructed by several motifs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 Theme is the author’s ideology which comes from subject matter,it contains obvious value judgments and emotional orientation, and chang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concept.
themat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category; motif; subject matter; theme
2011-09-19.
吕超(1982— ),男,江苏徐州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
IO-03
A
1673-0712(2011)05-00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