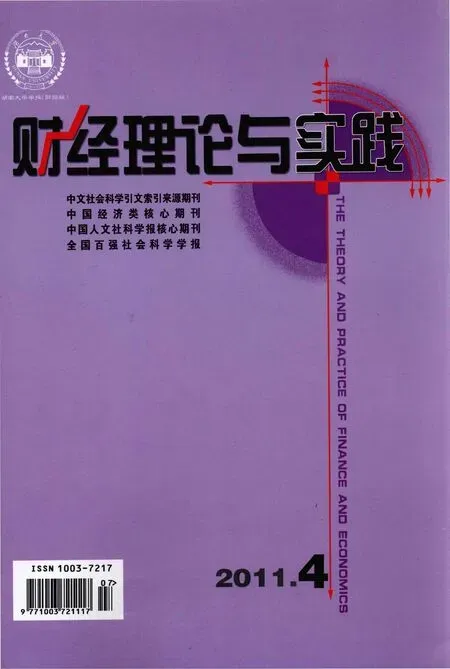对后危机时代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创新的思考
黎四奇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尽管在应对2008年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的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展现了其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作用,但是新形势下该制度内外交织而生的缺陷也表明在根治危机方面,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良方。对于法律自身物竞天择与适者生存式的演变,哲学家黑格尔先生的名言是:“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1]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遏制未来的危机,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对比较久远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新的金融语境下作一个“应该是什么”与“事实是什么”的理论。
一、谁最有资格担当最后贷款人——一个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之际,谁最有资质救危险中的金融机构摆脱“苦海”?——这不仅是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同时也事关救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目前已有的实践来考察,这似乎是一个不屑一提的小问题,因为各国的金融史已多次证明,这是中央银行责无旁贷的责任。而且,早在1802年,学者桑顿便指出,这是中央银行的使命所在,在行使该项职能时,其目标有二:“一是控制长期货币供应;二是迅速提供临时流动性清偿资金,以防止出现全国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该理论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追棒,代表了一种主流,其因就在于央行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且其拥有多项法定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横向比较之下,由央行来肩负起最后贷款人的重任似乎就是“天经地义”与“义不容辞”的。
真理的本质是相对性,新形势下,旧有的真理若想保留住它原有的成份,那么人们就必须审时度势地对其作出开拓进展的解释。从事物的发端来看,虽然由央行来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代表了历史选择,但是在形成定论之前的对垒性观点也有助于我们捕捉到一些制度自身不可回避的缺陷性信息。如作为与公共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对抗,早期的自由银行学派便抛出“私人最后贷款制度”。金融的编年史也告诉我们,这也并不非什么牵强人意之论,如在比利时,银行业共同出资成立“银行信用保证局”,以在不时之需时基于公共利益,对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财务援助。“日本的樱花银行、富士银行、东海银行等曾联合向陷入困境的太平洋银行提供1100亿日元的十年低息贷款,以助其将十年期间内可能发生的坏账撇除。”[3]虽然在实证的法律制度下,公共学派与自由学派之间的争鸣已见分晓,但是主体资格“花落谁家”仍值得我们从学理上进行检讨与反思。
最后贷款人职权非中央银行莫属吗?虽然说自由银行学派所宣扬的“私人最后贷款人制度”由于不能克服市场失灵的缺陷及行业互助性而曲高和寡,而且央行一直所把持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已有厚重的历史沉淀,但由此是否就必然推断出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掌控非央行不能呢?对这一问题的穷根究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当下央行所扮演的这一角色,而且也益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背景下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推陈出新。实质上,在价值博弈取舍中,各国之所以否定“私人救济说”而肯定“公力救助论”,就在于,“公力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借助国家之手,具有自觉性、及时性和稳定性的优势,这恰恰是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同时,最后贷款人一般由政府部门,尤其是金融监管部门来担任,因为其拥有宏观调控权或市场规制权。”[4]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在遴选最后贷款人这一问题上,政府的选择肯定是多元化的,如财政部门、存款保险公司、及外汇管理部门等有经济实力的公权机构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Bordo就曾独到地指出:“这样的官方机构并非一定就是中央银行。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加拿大以及其它相关国家就是这样。在这些样例中,最后贷款人功能通常由其它形式的货币当局提供,如美国的财政部、加拿大财政部及外国货币当局。”[5]无独有偶的是,学者Repu llo则采取了分切式的思维,他利用不完全合同的微观基础模型证明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由央行来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而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则由存款保险公司来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6]。此外,央行“币值稳定、保障就业、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向也往往迫使其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鉴于央行承担着币值稳定的重任,所以其必须持续、适度地控制着货币发行的规模和速度,维持通货在固定汇率下的可兑换性或者防止浮动汇率下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在金融恐慌来临时,出于金融稳定的压力,央行往往又会被迫临时性地采取宽松的量化货币政策。因此,从本质上评判,央行货币政策职能与其把持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和紧张,而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其身兼最后贷款者适格性的质疑。
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垄断了流动性资源及具有信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政府部门中由央行来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已是一种基调,但是以上的分析及已有的金融危机救助实践表明央行的这一角色并非是难以撼动的。众所周知,央行的主要职责在于执行货币政策,如果直接或间接地过多涉足于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则其权力集中的事实有背于法治下分权的要求,“因为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7]如果在初期这一问题还不那么招惹人眼的话,那么随着央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危机导向下的逆向性扩张,权力集中风险问题便显得有些严峻起来。如中国人民银行在其《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中便借势主张:央行要进一步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有效发挥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作用,加强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同时,健全对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检测、分析和预警能力。实际上,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救助中,即使是在作为金融监管完备楷模的美国,在贯彻最后贷款人职能时,这一角色也并非由美联储一家大权独揽,其财政部等机构在危机解困中也功不可没。在越来越崇尚效率与效果、成本与收益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目光来考评这一问题。事实上,随着经济金融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人们已开始对最后贷款人职能务实地进行新的审视,其结论是,并不绝对排除由央行以外的公权机构来承担,问题的关键在于二点:“一是该机构要能几乎无成本源源不断地获得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二是能够与金融监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以便及时、快捷、充分地获取市场信息,形成信息优势。”[8]在机构创新中,财政部门、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都具有担当最后贷款人的基本资质。当笔者如此之论时,其意并非要颠覆央行所扮演与至今仍保持的传统角色,而是在于阐明制度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是故,制度的因势因时而修正是一种历史使然。
二、最后贷款人制度究竟是服务于谁——一个必须突破的瓶颈
法学家耶林曾说: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如果这句话是可以经受历史考验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推论就是,有目的地用制定法的形式创制规则就是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体系的最佳方法。最后贷款人制度设定的目的在于防控和克制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与维护整体金融的安全。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必须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作为金融风险遏制底线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到底是服务于谁?或者说,该制度的效力指向对象何在?
在探讨央行的特性时,人们惯于将其归结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等几个方面。实质上,这种定位对于解答上述问题还是非常具有助益的,因为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密切难分的关系已说明在传统上其是服务于商业银行的。如美国大学的通用教材《货币、银行与经济》就将央行的职能厘定为二个方面:“一是控制货币数量与利率;二是防止银行倒闭,即最后贷款人职能。”[9]学者古德哈特亦指出:“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这种地位的建立是为了承担起责任,使中央银行去发挥它自由决定金融管理的特定艺术,普遍地对银行系统的健全予以全面的支持和负责。这种管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同经济中货币总状况有关的宏观功能与职责;另一个是同银行系统(个别)成员的健全与福利有关的微观功能。”[10]实际上,这种界定并非一家之言,随意翻开一本相关货币银行学或金融法学的教材,就不难捕捉到类似的针对央行特性的阐述。这表明在本质上央行的客户对象是商业银行,这一定位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且更是落实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需要。在漫长的演变中,这一特点也被法律化,如我国《中国人银行银行法》第2条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金融业比较单一化及经济非金融化或半金融化的时代,这一设定还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金融业务的分分合合流变中,随着金融业内部分工的日益模糊而出现异质业务交叉之时,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专司于商业银行的指向已明显不能适应金融整体稳定的时代诉求。可以说,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救助就使得这一问题隐而不彰。尽管在危机救助中,各国央行相机抉择而不拘泥于法律的形式,但是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滞后于金融现状的事实已是一览无余。
最后贷款人制度专为谁而设呢?在控制系统风险中,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虽然已有的法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但这只是一个半对半错的回答。为了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金融安全网的制度化已不能刻板地固守于金融机构,必要时,还必须将网扩大到与金融安全息息相关的非金融机构。由于金融创新的频繁和混业经营的加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难分,非金融类机构作为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失败也容易滋生系统性风险,所以“太大而不能倒”的保守监管理念也必然会延伸到非金融性的机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空穴来风,如“两房”(Fannie M ae&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就获得了美联邦储备银行流动性的援助。
金融混业并不单纯是一种业务形式的创新,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某些金融监管理论与立法实践进行了彻底的毁灭。尽管在“百货公司型”的金融企业集团模式下,为了规制内幕交易风险,立法者相机抛出了防御性的金融防火墙制度,但是该制度的有效性又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密切相关。英国学者Richard Daley认为,“银证混业对最后贷款者职能的影响最终取决于银行和证券交叉部分监管的不同方法,若防火墙得以建立,并确实有效,那么最后贷款者的职能就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反之,若防火墙没有建立或者没有作用,那么不言而喻,最后贷款者的职能就应伸展到证券市场,以防止证券公司的风险向银行业渗透。”[11]实际上,在追求规模效应与利益协同化的导向下,金融企业集团在组织结构上日益复杂化,其不仅表现为不同金融业之间的异质性组合,而且也表现为以金融业与一般实业的融合。同时,其内部的组织模式亦各有千秋,如或表现为母子公司关系,或为管理合同关系,或为合伙关系。
虽然从法必须因时利导的层面评判,立法者应求真务实地对最后贷款者制度作出创新性的法律解读,但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是效力范围问题;二是若打破传统的局限,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最后贷款者制度将不作任何甄别地适用于全体金融机构呢?若标准化,那么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规范来避免厚此薄彼问题呢?三是该制度是否适用于非金融类的机构?若答案皆是肯定的,那么法该从何而出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最后贷款人制度显然应扩展适用于可能直接或间接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构。若要对后二个问题进行较准确的回答,以给未来的立法提供指引,就有必要重温一下最后贷款人这一概念的内含,“其是指在实行部分准备金和央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前提下,中央银行为应对将引起流动性需求非正常增长的不利冲击,在其它市场来源不能满足这种流动性需求的情况下,对金融机构或整体市场所采取的相机提供紧急流动性的制度安排。”[12]籍此可以推理出以下结论:一是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同业市场失灵易使机构出现系统性风险,因而有必要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因为央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所以其有能力提供流动性;三是积极作为的目的在于弥补流动性的不足,而非清偿力的危机处理。若对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作经济的与政治的交叉性解释,结合最后贷款者制度产生的历史源流,则不难感受到新金融情势下,是否运用最后贷款人制度的要点在于某一金融类或非金融类的机构是否因流动性不足而恶化到影响整体性金融稳定,即不以“定量论”,而以“定性论”。马克思曾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13]因此,从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及制度创制的目的诉求来更新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效力边界是时下立法者所必须慎思的问题。
三、最后贷款人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共存——一个效率的问题
法律的重心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功能与实效。对此,波斯纳就认为,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在金融安全网的构建中,波氏的洞见同样地具有广阔的市场,如金融监管机构的数量是否与金融的安全性之间呈正线数关系?在监管机构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明晰监管权而避免监管资源浪费,在机构之间的权能本就存在交叉不清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职能冲突及避免监管失灵呢?……这一切都是新金融情势挑战下法律创新都必须深察的现实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是金融安全网建设中抵御最终风险的两道不可或缺的相互帮衬的防线。也正因为在救助中,该两制度都附着有“事后”了难的特点,所以其职能就难免存在交融与“混合”之处。虽然通俗意义上,我们可以用“人多力量大”来粉饰这一现象,但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的笑谈告诉我们效率的改善是以明确分工为必要条件的。尽管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可以利用“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人制度在功能、提供的条件、经济效应、对公众的保护等方面的差异”来为这种共存的合理性提供学理上的支撑,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大拯救中,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没有作壁上观的事实也说明,理论上的逻辑并不能给实践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大千世界中,我们所面对的只是现象,本质在现象之外。尽管在表象上,我们可以说存款保险制度是对一个即将退市的商业银行机构的善后,而最后贷款人制度则是对一个出现问题的银行机构的“救死扶伤”而使其荣获新生,但事实是在应对重大金融事件之时,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异变为“破产预防”,而不在于困难机构真正地关门大吉,因为金融风险的连坐性决定了金融体系、市场、社会与国家都难以承受与消解机构破产的消极性放射效应。对于这一拙见,美国1991年通过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就提供了有力的回应,该法设定了一套详尽的循序渐进的“结构化时期介入与解决机制”,其“目的在于银行资本充足率跌至一定水平,但远未导致倒闭时,促使监管者对银行采取措施,以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14]在制度创新中,笔者认为,立法者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明辩。
其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要不要共存及能否共生共存?对此,我们可以作逆向的思维,即如果只有最后贷款人制度,金融的稳定性是否不会有太大影响,或者即使发生了突发的恶性金融事件,仅依赖于该制度,监管仍能游刃有余。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银行机构倒闭的连锁效应及“太大而不能倒”的经验表明,即使在一国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中缺乏明示性的存款保险制度,那么它肯定也存在比明示性更有保障力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这种单边的做法不仅会迫使最后贷款者在面临问题机构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国家对存款人损失的兜底实践与预期也不利于国民风险意识的培育,由此而生的另一后果就是银行机构与存款人逆向选择套利的道德风险。而存款保险制度的直接性、法定性、公开性、公正性、及风险共担等特点恰好对最后贷款人制度的缺憾起到拾遗补缺的功效。从这一点看,明示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对最后贷款者制度的必要补充。反之,在一国金融监管体制中,只单设存款保险制度又能否适应金融安全的要求呢?勿庸置疑,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无论是在功能定位,还是在资金充沛量、信息占有量、及救助能力与经验方面,最后贷款人制度都具有其它机构无法比拟与替代的作用。由此可知,该两制度的互补性及职责分工性决定了在应然度与实事度上,两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
其二是若能共存,那么存款保险机构与央行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权责的分配、谁应该服从于谁、及两者合作的标准是什么等?对于这一问题,国内金融学界已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对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讲,银行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最后贷款者制度是第二道防线,而存款保险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划清中央银行最后贷款者与存款保险出资救助的时间和顺序,处理好两者在解救银行危机时的关系。”[15]这种分工布局性说明最后贷款者与存款保险机构之间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附属性。另外,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确立的论述中,则又可感觉到另一种说法,即“最初存款保险机构应由中央银行设立存款保险局,并附属于中央银行,不以赢利为目的,业务受中央银行监管,但是必须具备权威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待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建立存款保险公司。”[16]
尽管在独立性问题上,赞成者与反对者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它毕竟揭示了独立性的确是该两制度共建中的一个必须一清二白的问题。那么,出路何在呢?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本质是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起点。顾名思义,存款保险的目的在于对存款人的存款提供保险,其旨在于通过“保险”的方式应对局部性的银行机构破产的风险,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最后性”则说明该制度所关注的是整个金融系统全局性的风险,是金融安全保障的最后“杀手锏”。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各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亦有类似的载述。基于这一制度设立的“必然性”判断,我们的结论就是,在某一问题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局部性,不具有广泛的扩散性,且是可以被成功拯救时,那么存款保险机构是独立于最后贷款者的,或者说是存款保险机构对最后贷款人起到了保险作用;反之,当流动性风险非常严重,可能产生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会危及整体金融安全时,那么从监管的有效性、及时性、及成本性评估,存款保险机构应是从属于最后贷款人的。如此道来,独立与否识别的标准就在于问题机构的风险程度,即是局域性的,还是系统性的。这一划分不仅是出于节约监管成本及提升监管效率的诉求,而且它也尊重了监管制度与措施的援用必须循序渐进的理念。
四、结 语
哲学赫拉克利特曾言,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事实上,这句话同样可以被借用于我们对法律知识创新的探索。抑或是出于标新立异,或是出于一种知识领域的圈地……,我们将法律冠上了科学的名号,如果我们并不刻意地去对这一“科学”的定性是否名副其实进行较真,那么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当下,我们就必须承认科学的精神就是挑战、质疑和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我们的知识、法律理念与制度……才会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更新换代。如果说在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才刚刚揭开篇章的时代,最后贷款人制度非央行莫属、其“央行——商业银行机构”的一对一的服务模式也是千载难改的,那么我们只能说这只是反映了初级金融阶段的时代要求而已。事物发展的非恒定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客观地对任何一种理念与制度适时地进行审时度势。经济金融时代下的金融突变已全方位地对传统的金融法律制度提出了拓新的诉求,而危机后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因时而异便是法律必须适应动态社会发展的体现。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7.
[2]George J.Benston,Robert A.Eisenbeis,perspectives on safe&sound banking:past,p resent and future[M].M IT Press,1986:109.
[3]江曙霞.银行监督管理与资本充足性管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28.
[4]何锦前.最后贷人制度的法律价值二元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6-59.
[5]Bordo,M D.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alternative view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conomic Review,Jan/Feb,1990:18-29.
[6]Repullo,Who Should Act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an incomplete contracts model[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Banking 32,No.3(August 2000),pp580-605.
[7]Montesquien,The Spirit of Law s,tans by tho masnugent[M].Ha fner Publishing Company,1996,150.
[8]汤凌宵.现代最后贷款人操作规则的创新与发展[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16-21.
[9][美]托马斯◦梅耶等.货币、银行和经济[M].洪全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2-185.
[10][英]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胡坚.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419-420.
[11]Joseph J.Norton,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the1990s[M].L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p.132.
[12]汤凌宵.我国经济转型期隐性最后贷款人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5,(12):16-24.
[13][德]马克思.论婚姻法草案.马克思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83.
[14][瑞士]艾娃.胡普凯斯.比较视野中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M].季立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0.
[15]颜海波.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J].中国金融,2005,(11):34-36.
[16]王贞琼.银行风险与存款保险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71-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