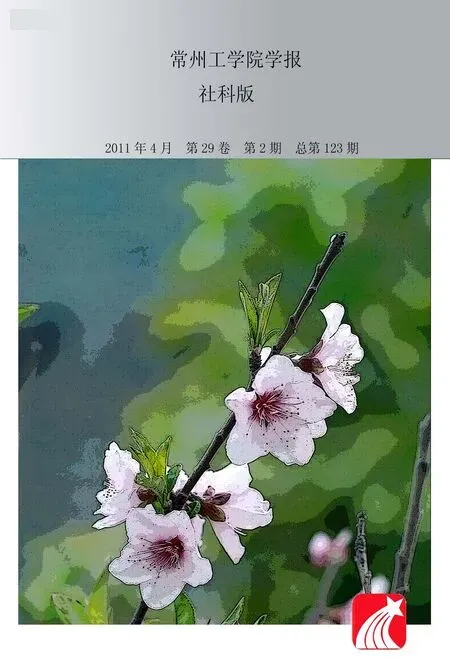论战时重庆文学中的经济世界特点
喻冰清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47)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并于此后陆续西迁。几经周折,历史最终选择重庆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938年后,产生了大量与重庆有关的文艺作品。川地本土作家和西迁作家用各自不同的心灵与视角关注着激变中的重庆——他们踏入同一个山城,笔下呈现了迥异的三个世界:第一个属于踏遍尸骸、俨然身处乱世桃源的高官巨商(以下简称“世界一”);第二个世界包含一切尚可温饱的重庆居住者(以下简称“世界二”);第三个世界游离于前两个世界之外,满地都是被踩烂的贫民骸骨(以下简称“世界三”)。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作品中的重庆,都流离着数量过多、与经济中心城市风貌不相符的贫民,并且又拥有太多国难时期崛起的富豪。
战时重庆文学中的经济世界,具有非常明显的战时特点。
一、成员流动具有战时特殊性
张恨水是华语世界知名度很高的作家,通俗小说家的出身决定了他的作品拥有情节性强、时代现象描摹入微、想大众所想之事、言大众欲听之闻的特点和优势。比之纯粹正统文学对心灵震颤的追求,张恨水的作品更注重对社会状况的存真性①。他是写小说的老手,小说的技巧,如小说创作忌语言冗繁,忌情节重复,他比谁都清楚,但他偏偏在《魍魉世界》里不厌其烦地借多人之口、眼、行,讲述了几个大同小异的发财故事。
第一章,区家老少齐聚西门博士家中谈改行,区家老大讲的是纸烟贩翻身记。一个穷得无处安身的同乡科长,借钱做买卖,因生病耽误了贩烟时间,没料想在生病的十天里纸烟价格涨了对倍。他以这笔钱为资本尽可能大量贩烟,利上滚利,开起纸烟杂货店,就此摆脱了贫困生活。第十二章,巨商温家二奶奶与西门太太等人聊赚钱,二奶奶和区家女儿区亚男讲的是书呆子发财记和官员盛德刮地皮。书呆子的爸爸买了六七千元的材料准备盖房子,因重病和战乱,工程不能继续,一年后书呆子卖出原价两三千元的材料已经赚了好几万,剩下四五千元的材料在战乱中价格一涨再涨,书呆子什么也不做,就拥有了百万身家;官员则是战前买了老百姓十几个山头,战时地皮和木材价格暴涨,发财发得不可思议。这几个故事的共同关键词是“躺着也发财”。
除了口传的传闻故事,张恨水以区家的双眼写了几个具有共性的人物。第九章,以亚雄前往渔洞溪寻找弟弟亚英情节线为例,兄弟俩于一天之内在当地就遇见两个改头换面的熟人:先是碰到曾在南京烧开水卖烧饼的店老板,现已在重庆开工厂,西装革履,面貌焕然一新,谈吐已然不俗;再是碰见昔日的车夫李狗子,当年满身疥疮掏不出五元钱的人,如今住别墅,当经理,已经鲤鱼跳龙门。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可共判词是“有钱人宁有种乎!”
然后是区家的亲身经历:区亚英穷得无法可想,变卖皮鞋和自来水笔外出行商,因为偷懒,积了三百斤油不曾变卖。市价高涨,一个月内三百元本钱就加倍翻成了千余元。虽然还谈不上发达,区亚英的资金初步积累方式与之前传闻中提到的“躺着也发财”的诸君是完全一样的。观其行商期间言行,则隐隐然又有“有钱人宁有种乎”的意思。区亚英是新一轮发财传说主角的雏形。
《魍魉世界》充斥着大量轻易改换了经济地位的暴发户:“囤货就可以赚大钱”、“走一步遇见两个一穷二白的人发了财”。创作这样的“童话”通常只能证明小说作者是一个拙劣的白日梦编织者。但在战时特定背景下,这却是张恨水对重庆市面单调而切实有效、一再成功的商业经的介绍。重复讲述囤货、暴富情节,并非张恨水江郎才尽,而是整个社会的现实:如区家般受经济压迫的家庭们,或在观望或在准备复制躺着发财的成功史;如温家二奶奶般金钱富裕之辈,一直都在躺着发财。身处不同生活圈的重庆居民,持续性的、不约而同的关注点都是钱。整个社会不断涌现的也都是发财的童话。
在当时,人口激增,政局动荡,物价飞涨。资本雄厚的炒黄金地皮,换外汇,本小的也可做百货。商品无一不涨价,只要有原始资本,找不出可以亏本的生意。仅以吃、穿、用等生活日用品为例,吃方面:1937年,重庆五花猪肉平均零售价每市斤0.264元,1941年5月每市斤3.43元;鸡蛋1937年一个0.018元,1941年6月一个0.28元。穿方面:1937年土布每市尺0.112元,1941年3月每市尺1.66元;1937年帆布鞋每双0.354元,1941年6月每双8元。用方面:1937年草纸每刀0.04元,1941年6月每刀0.6元;1937年灯油每市斤0.324元,1941年6月每市斤2.6元[2]。如果把敏锐的市场嗅觉、灵活的经济头脑、果断的决断力、良好的人脉等素质视为每个时期白手起家并在商海获得成功、改变命运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战时重庆从商成功的第一先决条件只是一笔资本或一些资源。物资大量紧缺,求大于供,导致市场对优秀商人的甄选无法成立——商品普遍涨价,因此经商失败的风险几率大幅度降低,人人敢于下海;商品价格与价值不匹配,因此涨价幅度呈现无序性,巨商固然可以把握整个市场的波动,对于小商人而言,拥有一双看得穿市场流行风潮的商人之眼,远比不上多一点运气、体力和狠刁的心肠。
在战时重庆行商谈不上优胜劣汰。经商→用原始资本买进货物→囤积→赢利,流程毫无技术含量和入手难度,又几近没有亏本的危险,只要不怕脏与累,低得下头“和气生财”,人人可参与这场商战,并借此跃身其他阶层。像区家这样家里原是翰林、在现代也接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的家庭,尚有愧煞士大夫的顾虑;对原来职业就是车夫、轿夫之类的体力劳动者而言,在战时重庆行商只是另一份体力劳动工作。不能否认良好的商业素质会在商人进入拥有大量资源的第一世界后发挥作用,帮助优秀的商人站上顶级商人的位置;但没有相关素质,甚至资质愚钝,也绝不会影响一个人改变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流动进入第一世界。
进入第一世界的阶梯是黄金、外币、棉纱、大批稀缺物资,第一世界内全民皆商。从事工业商业,收谷养地,同时打算亲近政治得到权力的陆神州们,是显性的商人;无数不甘银行金钱贬值,又限于政治影响不能出面,藏身台后参与多项投资的无名氏,小如西门恭们,托人代理贩售战时稀缺药品,大如杨先生们,借从政界退职的旧部下公务员之手筹划办公司、办银行,其本人却连商人也不愿多见——这些是隐性的商人。
立身第二世界的必备条件,是至少要拥有强健的体魄、糊口的官方职业、抹得下面子去巴结的脸皮、战时重庆需用的技术这四样中的一样。具有重庆特色、抬滑竿走过漫长曲折山路的轿夫们是当时街头体力劳动者的代表;每日坐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等因奉此、支取微薄薪水和平价米的公务员区亚雄们是尚坚守本职工作的重庆知识分子成员;以心理学博士之名为敲门砖行掮客之实的西门德们,舍弃医师资格下乡做小商贩的区亚英们,则是接受了畸形社会的现实,决心为金钱进行一场搏斗的那部分逐渐脱离知识分子身份的新商人;开车在国内外跑长途的区亚杰们可以算作工人,他们为商人倒卖货物收入丰厚,绝不至于落到金钱困顿的地步,大手大脚的花费也决定了他们不会进入经济层面的上层社会,区亚杰们将持续在第二世界内不知所谓地生活。
堕入第三世界居民的共性是劳动能力的缺失或者严重的生活之累。第三世界内既有体力劳动者,也有知识分子,囊括社会上几乎所有职业的成员。包括巴金作品中没有办法继承遗产的重病中的轿夫杨老幺们②,以及重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和艺术家洪深们③。
从兼容士农工商、多种职业混杂的第二、第三世界到全民皆商的第一世界,战时重庆三个世界的成员流动体现了对能力条件极度放宽;对进阶职业要求极度单一严苛——几乎只有商人才有能力进阶,与和平时代大异。
二、文明倒逆,知识分子经济地位反转
在《魍魉世界》中已经可以注意到,身为社会喉舌、于战前拥有崇高社会地位和丰厚收入的知识分子,在战时重庆以经济划分的世界中处于第二、第三世界:公务员想要摆烟摊;医生愿做挑夫,愿拉黄包车,愿抬轿,最后很干脆地去乡下做了小贩,很明显日子过得不如苦力。其实,这样的生活就是战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因而多位作家的笔下都有相关描述。如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陈瘦竹的《声价》、茅盾的《过年》。
《声价》讲述了发生在重庆邻市泸州一个小县城里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为躲避日军空袭,政府机关从重庆疏散至当地。比之重庆,泸州的物价让这些公务员以为置身天堂。自从得知公务员王大成每月能赚一百二十块钱,合一年一百四十四担谷子,房东周恕斋就打定主意要把二女儿嫁给他。因为公务员有钱,“读书人地位高,有面子”[3]1395。一番曲意结交,周恕斋终于如愿以偿。没料到谷子价格涨得那么快,公务员的工资就是不肯涨。到周二小姐生产时,王大成一年工资已经买不到四担谷子。有面子的读书人从当地乡绅座上宾变成了为孩子洗尿片的奶爸,王大成忍了又忍,终于不堪忍受周家的冷嘲热讽决定离婚。小说的结尾,周家慌了手脚,定要追回二女婿,当然,这不是因为王大成和周二小姐之间发生了深厚的感情,而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带着孩子两张嘴,怎能容忍她吃的全是娘家?
《吃了一顿白米饭》的主角林雨生,居住在重庆周边的郊区乡下,他本是来自上海的曾拥有优裕生活的作家,在当时的重庆,在“最好的作家的作品的稿费千字不过二十元”、排字工千字六十元的行市下[3]1049,只能勉力苦撑生活。他的儿子春生抗战后出生,每天盼望吃白米,实则是没有见过不带谷壳、饱满充实的白米饭。在做生意的印书局黄经理家里吃过饭后,林春生对于谈做生意赚大钱吃白米饭话题的兴趣远远超过了谈打走日本鬼子话题的兴趣。
而生活在重庆山城内的老李(《过年》),无钱怕回家过年,情愿呆在办公室值班。终于办上一斤年糕做年货,却被老鼠拖走了,即使追到肮脏的屋角,也要鼠口夺食,把老鼠咬掉一半的年糕抢回。
战时重庆,重商轻士达到了顶峰,在经济方面完全是“商农工士”。拥有固定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哀叹微薄的薪水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自由职业者几乎走到绝路。没有什么不涨价,只有文字一直在跌价。1940年1月刊登在《新蜀报》上的《蜀道》首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4],谈对贫困作家进行援助的问题。出现这样的议题本身,已经说明当时奋斗在文艺战线上的战士们发生了普遍性的、已经使人无法忽视的生活困难。
中国话剧运动奠基人洪深对生活感到绝望,与妻女服毒自杀;老舍生活困窘,营养不足,百病缠身,罹患贫血、打摆子、肠胃病、盲肠炎[5];其南温泉的邻居张恨水,从入川起三年没缝过一件褂子[6]。作家生活的困窘与创作的丰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前文所举三篇小说各有千秋,都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声价》是带着微微自我解嘲意味的讽刺,《过年》是叙事平淡到极点反而造就了可再三回味的韵味,《吃了一顿白米饭》更让人感到直接的痛苦和悚然。
“天老爷,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雨不下,吃泥巴!”
林雨生之子林春生自天旱开始唱的应是成都一带老童谣《老天爷,快下雨》的变体。如其字面意思,这是一首农人期盼丰年的祈词。一再吟唱这样的歌谣,是长期居住郊乡、知识分子家庭被农家邻里大程度同化的证明,也是对儿童的渺小憧憬与难以实现的冷酷现实的强调。林春生在黄经理家丰盛的酒席上唱出童谣,因其年幼纯真的姿态而更显讽刺和悲凉。林雨生为了鼓励儿子和自身,决定把歌谣改成“天老爷,快打日本鬼,保佑娃娃吃白米!不打日本鬼,吃泥巴!”……如果小说在此结束,这也已经是一篇完整的激励抗战的作品,但春生对白米饭的渴望却不容许故事就此完结。他在问明黄经理家不用打完日本鬼子也能吃白米饭是因为做生意后,即低声哼出了“天老爷,快做生意……”
当身为祖国未来的幼子在“你要做生意还是打日本鬼子”的询问下毫不犹豫选择做生意时,所有还珍视祖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悚然心惊:谋取良好的物质条件并不可耻,然而,生活过于困苦导致对富裕生活的渴望远远超过对祖国的爱,这样长大的孩子们是无法承担中国的未来的。战时极度的重商轻士,不仅损害了传承中国文明与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身心,还将祸延下一代。
幸运的是,极度的生活艰难并没有扼杀中国文艺工作者进行抗日宣传的热情。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心,战时涌现了大量以服务抗战为目的的创作。战时文学具备报告性与通俗性,体现了强烈的鼓动性与攻击性[7]。文艺家们歌颂抗战的英雄,描写战时百态,批判社会黑暗。纵观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包括小说、戏剧,不难发现正直的知识分子、充满希望的青年学生、憨厚诚实的劳动者、勇敢的战士、自私卑劣的军阀官僚、利欲熏心的国难商人等多样形象。而对上等阶层着重于批判,导致了处于第一世界的正面爱国商人、企业家等在文学作品中的鲜见。
一直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庆,面临着战争的严峻考验。重庆被西迁者和中国的局势改变,同时也改变所有重庆居者的生活和命运。对此,历史学家以慎重的态度记录下了抗战时期重庆的所有事件,文学家则用双眼拍摄了那个时代的具体社会风貌。
以抗日救亡为目的,文人们于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持笔为矛,举纸作盾,写尽战时苍生。每篇成功的战时小说,都是深入中国腹地,以几乎要摧折生命的危困生活为代价换取了写作深度的作家们直取灵魂的嘶声呐喊。在史学家和文学家诚恳而追求真实努力下还原的“黄金时代”重庆“画卷”,比现实更直观地充斥着畸变的社会冲突而非社会竞争。
注释:
①对张恨水的理解参考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杨老幺为巴金《憩园》里的人物。巴金:《憩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③左翼文艺家洪深因生活困苦无以为继,1941年与夫人常青真以及肺结核晚期的女儿一家三口服毒自杀。因得到抢救幸告脱险。见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493页。
[参考文献]
[1]李松林.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K].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326.
[2]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338-339.
[3]艾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二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4]楼适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一编·文学运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14-620.
[5]老舍.老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150-210.
[6]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00.
[7]靳明全.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战时性[J].文学评论,2002(4):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