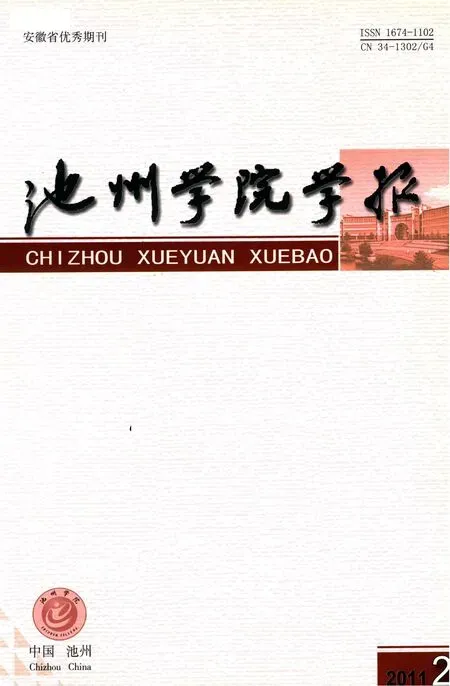守望者的热爱与痛惜
——楚风小说创作述评
徐明旭
(新街中学,安徽 天长 239324)
守望者的热爱与痛惜
——楚风小说创作述评
徐明旭
(新街中学,安徽 天长 239324)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叙事呈现出纷繁的价值观念,如何坚守普世价值立场而又有所突破与创新成为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亦折射出汉语写作的某种困境。论者从思想蕴涵、艺术特色、价值立场等角度出发,对当代小说写手楚风的创作展开述评,就此问题作一些具体探讨。
自我缺席;语言;守望;困境
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较少地关注当代文学,似乎成了我的一个偏好,因为我总觉得当代文学创作缺乏深层的精神叙事。小说写手楚风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这个观点,楚风也以一种守望者的姿态站立在我的精神视野中。
1 思想蕴涵
评论小说首先要回到作品的叙事现场。楚风的叙事现场总是透露出一种精神的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凭借作品的意境或者叙事风格展现出来,而是通过作品的思想蕴含得以彰显。楚风的《兽性》、《骨瘦如柴》和《边吹泡泡边唱歌》等作品便包含着这样的紧张,展示出自我缺席的纷繁镜像。这里且以这三篇作品为例进行叙述和评论。
小说《兽性》描写了人性和兽性的对峙和错位。在这里,动物生灵表现出具有人格意义的善良、真纯、坚忍和执着,而人则表现出本性中的阴暗:贪婪、自私、猥琐、残酷,缺乏对生命应有的同情与悲悯。在作品提供的场景中,人性与兽性悄然对视并且展开了激烈较量。动物一再退避,似乎要以自身的光芒唤醒主人早已沉睡的良知,但悲壮行动没有取得主人怜爱与同情。甚至在经历死亡威胁而被动物挽救之后,主人依然本性不改,一再突破道德底线,向真纯的兽性疯狂进击。这种对峙与较量最终以动物与人的共同毁灭而告终。
楚风显然采用了隐喻的方式揭示出自我缺席之后人性到底能走多远。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并不难理解。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格划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的构成是原始的生命本能,无条件地按照“快乐原则”行动,没有道德是非和时空限制。而“自我”则代表了人格中理智和意识的部分,行为准则是“现实原则”,根据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来调整本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超我”则是道德化的自我,用自我理想来确立行为目标,用良心来监督行为过程,使自我摆脱本我的纠缠,按照社会规范和要求活动。这三部分在人格构成中,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心理需要和遵循不同的运作原则,因而往往相互矛盾、冲突。
在我看来,《兽性》表现出来的纯美兽性隐喻着人的“超我”,而主人的阴暗本性则隐喻着“本我”。作为调节“本我”与“超我”矛盾冲突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成了缺席者。而正是“自我”的缺席使得作品折射出人的阴暗本性所能达到了程度,或者说是人在丧失理性藩篱后的疯狂所能达到的程度。这是丧失“自我”的行尸走肉,对待动物的疯狂态度其实是对生命的漠视:可以因为利益、可以因为喜好、可以因为无聊、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因为而对动物残暴施虐。这种对生命的漠视足以毁灭人的自身,小说结尾明确揭示了这一点。
“自我”在生命过程中的缺席无疑是人的一种扭曲的生存状态。这种扭曲在不同的生命个体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应对方式,小说《骨瘦如柴》展示的便是这个内容。和《兽性》中简单的二元对立不同,《骨瘦如柴》有着更广阔的生存背景和更丰富的生命镜像,也在深刻的层面上揭示出人的生存困境。
《骨瘦如柴》着力刻画了一位名叫“蓬头士”的文人形象。他享有许多文人一生追求而鲜能如愿的盛名,在世俗的眼光里是没有遗憾了。可是在行将就木的时候,“蓬头士”真正认识到自己把一生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应景文字上,没有写过自己钟爱的文字。他对“我”说:
“……我的遗憾是永恒的,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我一生也没写过我满意的文章。”
在“蓬头士”人生经历中,精神人格的“超我”部分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自我”被排除在了精神世界之外,这一结局成为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同样的悲剧还在更多不同的人那里展现出来。在琬城中心广场,一群丧失“自我”的文化销毁者举行了恣意狂欢,以夸张甚至怪诞的言语行动谱写出了地道的“后现代宣言”。这个“宣言”在解构意义、解构崇高的同时也解构了生命存在的理由,人的生存也便降格为动物生存。这些所谓文化销毁者的行为艺术,其背后都有一个放大了的、找不到出路的“本我”。
《边吹泡泡边唱歌》看似语调轻松,趣味横生,但作品背后分明透射出深刻的忧郁和紧张。小说描写了一群快乐生活、茁壮成长的小学生,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1]。他们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完美融合。可是他们的“自我”正随岁月与生活的磨砺缓缓失落。他们的脚步被要求整齐划一,喊出响亮的口号,他们的睡姿被规范要求并受到监督,他们的顽皮话语和疑问被当作违法乱纪,他们正被教导要“听话”而成为“有用的孩子”。
小说中的灵子老师应该也有过纯真的童年,可是我们看到的灵子已经走出了纯真,成为“超我”占据人格主体、言行符合社会规范的人。她正以教师的身份职责要求孩子们完成社会对于他们的角色期待。但是外部世界施加给孩子的许多规范并不顺应孩子的天性,这其实是“超我”对“自我”的挤压。这种挤压所带来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人,终究要穿过童年的感性与灿烂阳光,不可避免地走向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但是总有许多人,当他们融入社会之后又将自身最初的境遇施加给新生的孩子们,如此循环往复。
“自我”的缺席与寻求是生命个体对自身人格的审视与超越,是从精神意义上摆脱颤栗与不安的艰难选择。正是这一点带来了楚风小说叙事的精神紧张,同时也生长出小说的美学气氛。
2 艺术特色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灵韵”(Aura),也就是说,艺术品的诞生应具有即时即地性,是“……在一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2]。本雅明的这一美学原则启示我们,优秀艺术作品的美学境界与表现方法应当是深刻而独特的。就文学创作来讲,优秀作品须能唤起令人沉醉痴迷的审美体验,同时形成个性鲜明的语言系统。这两方面,尽管楚风的创作做得还不够深入与完美,但其反观与努力已臻于自省和自觉。
楚风小说较为注重意境营造,从而带领读者进入文本世界,感受艺术的真实与美。
楚风营造意境的一个手法是神奇的联想与想象,这在《边吹泡泡边唱歌》最为突出。如“风儿把柳树的倒影吹虚了,把睡莲吹醒了,粼粼的波光上碧绿的“大肚脐”、火红的“赤兔马”、金黄的“麻狼”、黑白相间的“铁铁”、纯黑的、天蓝的、紫红的……这些我给起了名和没来得及起名的蜻蜓一伙一浪地飞来窜去,拥挤着,追逐着,胆子的大蜻蜓掠过水面时,还不时地用尾巴击水面。这个场面让我想起我们午餐前整队的场面:它们当中是否也会发生捉辫子、咬肩头、抢座位……”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蝉儿在唱,风儿在笑,柳树在跳草裙舞,绿油油的小草一波一波地做俯卧撑,我快乐地把歌唱成了“喵喔喵喔喵喔……”这可算得是俯下身来体验儿童的心理世界,充满趣味的场景透过文字传达出来。
另一个手法则是民间文化元素的融入,《骨瘦如柴》中就有诸多这类描写。如父亲在送别我时唱的《正月十五雪打灯》:
“正月十五雪打灯/我送我娃走一程/在外要受千般苦/回家才知爹娘疼……
还有《请神歌》:
“三皇五帝表不尽/一心想表唱歌人/昔日有人高三娘/所生五个好儿郎……”
这些深具民间风情的曲词推动作品形成了缥缈悠远、惝恍迷离的意境。
成熟作家具有个性鲜明的语言方式,形成独特的语言系统。楚风小说有许多出色的语言描写。小说《兽性》结尾这样写道:
“凝固的空气在一声巨响中爆裂,一股黑烟腾起,呛得主人眯上了眼,在主人放下被震麻木了的手臂的时候,一道红光闪过,主人像一只麻袋仰面跌倒在地上,他本能地用手护住了脸,从臂缝里他看到三虎两只火红的前爪按在他的胸前,三虎血肉模糊的脸与他如此地接近,三虎缩着脖子紧张地抽动的嘴唇,使他的脑海里立刻映出眼镜蛇昂首捕食时的情景,血在这一刻冷却下来,从头顶寒冷到脚心……”?
这里写主人打算杀狗却因为枪管走火而毙命,语言洗练、传神,又含蓄、蕴藉。最后的语句读来更有意犹未尽之感。在《边吹泡泡边唱歌》中,生动、有味、富有质感的语言俯拾皆是,上面已有涉及,此不赘述。
但是楚风的语言尚且需要打磨。就我读到的作品来看,我以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是作品有些语言给人的感觉是急促、冷硬,该节制的时候显得罗嗦,该铺展的时候又显得简洁。如《骨瘦如柴》写“我”在儿子病中的急速奔跑,“我带着浓浓的沉沉的雾在马路上奔跑着,它们一刻也没有放过我,镜片上满是水汽,我把眼镜摘下来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戴和不戴都一样,我只能凭着感觉跑,我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在这样的夜晚没有人会奔跑在马路上,除了我,我一刻也不停地奔跑着,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不停地奔跑,我也不管腿是绵软的,我也不管呼吸是粗重的,我也不管心跳是杂乱的,我只想跑,直到累死!”
这段文字读起来让人觉得很累,却并不感到“我”心情急切,原因在于语言处理张弛失度,内在的节奏冲淡了应该表现出来的人物情感。
有些语言则显得过于冷硬。比如下面的语句,
“那天的场合安排在午时,因为考虑到要让“蓬头士”早上有足够的睡眠……”
“飞絮萦绕着他上下翻飞,不经意中粘在他的青布衫上,从青布衫的轮廓我看到了他骨瘦如柴。”
“场合”一词所指称的情形本不错,但用在这里显得生硬,改成“仪式安排在午时……”读起来更晓畅,语感上更自然。而“不经意中粘在他的青布衫上”这个句子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中”与“间”相比是更富于金属般质地、硬度较强的词,用“间”在语感上要细腻圆润得多。
其次,楚风的语言具有强烈的速度感,似乎急于把故事讲述出来,少了些优雅从容。这方面《兽性》和《骨瘦如柴》表现得较明显,《边吹泡泡边唱歌》相对好些。比如《兽性》开头:
“清晨母亲突然嗅到了主人的气味,母亲心房痉挛起来,母亲跑回来发现三虎没了,母亲伏在地上绝望地嚎叫了几声,然后把三只挤过来吃奶的狗崽儿都咬死吃了。”在这里,语言的速度显得过快,读来令人感到压抑,可以换舒缓一些的表达。
第三个不足是语言缺陷,也是表现手法缺陷,那就是缺乏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少了更多的参与感。细致的心理描写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舒缓叙述节奏,营造小说所需的意境,使人物形象更富立体感。《兽性》、《骨瘦如柴》和《边吹泡泡边唱歌》这三篇小说,除了《兽性》由于叙述角度的原因不便于进行心理描摹外,后两篇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展开更为精彩的心理描写,拓展人物存在的时间背景和空间背景,达到动人、传神的艺术效果。这是我所理解和向往的美学境界。
3 价值立场
文学创作须坚持恒定的普世价值,否则呈现出的将是由于价值立场的退却而产生的纷繁乱象。丁帆先生在谈到新世纪十年文学创作中的这一问题时指出,“作家所扮演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代言人’角色的人格面具被取下,代之以媚俗的嘴脸(市场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扮演什么色)……”同时强调“我们确定的价值观念应该是符合人性和人道主义,以及历史发展要求的取向,它既是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的底线,也是对其的最高要求……”[3]观照起来,楚风小说创作的价值立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今天是一个文学创作观念趋向多元、低俗文化日益泛滥的时代,能够坚守传统道德信条和价值关怀的作家似乎越来越少了。与诸多喧嚣浮躁的写作不同,楚风的写作依然保持着明澈的客观,守望着我们熟视但又远离的精神光芒。他用真诚的叙述带着我们一边走,一边听,提醒我们关注路边的风景,倾听心灵的声音,热爱那些该热爱的,痛惜那些该痛惜的。
楚风小说批判了人的某些幽暗本性。《兽性》对人不如兽的丑恶现象的揭示,《骨瘦如柴》中对文化销毁沙龙场面的勾画,乃至《边吹泡泡边唱歌》对灵子老师教育孩子的言语行动的描写无不透露出小说作者的深深痛惜。在人性的某些光辉已然丧失或正在丧失的背景之下,这种痛惜已经敲响了时代和社会的警示钟声。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中这样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4]。
在这个众神退隐、众声喧哗的年代,楚风依然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与情怀守望着那些我们本来拥有也应该拥有和持守的价值立场,这种写作姿态无疑可以给我们日渐麻木的灵魂带来微弱的温暖。
正如对黑暗的控诉源于对光明的向往,痛惜并不和热爱决然对立,楚风的痛惜与批判恰恰是对人性光芒的热爱和赞美。以艺术化的叙述和描写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善美及其意义是小说作者的话语方式。而一个人的话语方式很多时候就是他的精神本身。比如《兽性》的开头部分对母亲的描写:“……母亲的眼泪静静地流着,她伸出色泽暗淡的舌头,舔了舔嘴角,咸咸的是泪,腥腥的是血,母亲就这样爬着没有再挪动过,直到她死去”。
《骨瘦如柴》中写到“蓬头士”对自己精神路程的真诚忏悔:
“改邪归正,返朴归真,可惜啊,对我来说晚了!”、“……黄钟大吕啊,天堂妙音,你怎么会是在这里?!”
这些表达充分显示出小说作者对精神之美的赞颂和向往。因此,《兽性》、《骨瘦如柴》和《边吹泡泡边唱歌》皆脱生于“自我”缺席的同一母题,形成了楚风小说的叙事范畴,我们不难从小说中觉察作者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操守。
但是楚风的小说创作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精神窠臼,折射出来汉语写作的某种困境。
无论是对人性的自省自觉,还是对生命的终极追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渴望回归本真,从而达到精神的自圆自足。当他们遭遇现实的苦难,往往从庙堂走向山林,从终点回到起点。这种现象当属人之于家园的“回归意识”。《骨瘦如柴》中“我”回到家乡,“蓬头士”向本真自我的呼唤便是如此。是不是只有回归才是唯一的精神出路?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缺乏更为丰富的精神纬度。
面对精神困境,或者说面对生存苦难,中西方文学各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果从中西方文化形态的差异出发来看,可以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与启示。
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等生存环境的差异使得中西文化体现出不同形态。中国没有宗教,这个古老民族整体上缺乏宗教情感。因而中国早期哲学总是思索着一种宇宙与生命的统一,即所谓“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特征的文化特征,我们的精神与人格总是体现为一种封闭结构,表现在审美趣味上则是追求一种阴柔与娴静。相形之下,西方宗教强调“原罪”意识。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采取的方式是毁灭人类。突破原有平衡,取得新的跃进和突变,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西方哲学充满躁动和遐思,体现在文学上则是歌颂一种骑士精神,人的精神呈现出开放式结构。
西方文学注重表现人与神灵或疏远或亲近的关系。对于现实苦难,西方文学或者表现为隐忍和坚持,比如大仲马《基督山伯爵》、海明威《老人与海》等;或者表现为对于宗教精神的皈依,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无论哪种选择,都是表现阳刚、健劲的精神之美。高行健的《灵山》写了流亡作家沿长江流域寻找灵山的过程,尽管没有找到灵山,但作家的步伐依然继续。可以说,《灵山》传达出来的终究是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
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在摆脱精神困境、消解生存苦难这一问题上具有拯救与逍遥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表现为思索和寻求,后者落脚在逃遁与回归。西方文学的智慧与表达给我们以参照,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要突破困境必须拥有新的精神资源。为此,我们期待——圣灵降临的叙事。
总体来看,楚风小说在“意”上已经超越了当今许多状态的写作以及伪写作,在“境”的营造上还需要更多的磨练和付出。坚守普世价值立场与价值关怀的写作,需要大的智慧,也需要大的勇气,在不断升华和超越之中,完成文学之于心灵的拯救与安放,楚风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1][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尹溟,译.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2003:20.
[2][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13.
[3]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J].文艺争鸣,2010(19):43-44.
[4]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M].上海:三联书店,1994:9.
I206
A
1674-1102(2011)02-0093-04
2011-02-24
徐明旭(1976—),男,安徽天长人,新街中学教师,中教一级,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章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