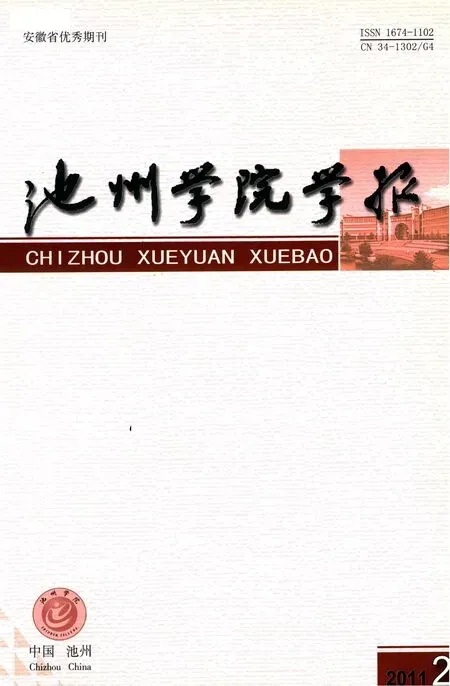论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从“钓鱼执法”事件说起
冯志华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从“钓鱼执法”事件说起
冯志华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钓鱼执法”事件再次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容易被滥用。而其深受诟病的原因就是违反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子原则,即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国务院在政策文件中已对“比例原则”作出权威性确认,在法治化进程中,现亟需立法明确此原则。
钓鱼执法;比例原则;行政法
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晖开私家车外出,途中因搭载一名路人而被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非法运营”为由科以行政处罚。2009年10月14日晚,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驶面包车行驶时,路遇一位衣着单薄的男子,恳求搭载一程,上车几分钟后,孙中界的车就被两辆路政执法车包围、逼停,并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罚款1万元。一时间,针对“钓鱼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追问占据各大媒体头条位置。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诉说、诠释,从法律角度分析的,“钓鱼执法”深受诟病的原因是违反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也就是在为实现公共利益或维护社会秩序,限制公民权利时,行政权力滥用,严重侵犯了公民权利。可迄今为止,一个已深入人心的理念,在我国行政法形式渊源中却没有此原则。不过,国务院在2004年颁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六项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其中对“合理行政”的规定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尽管该《纲要》并非法律,但是亦可谓中央人民政府对“比例原则”已经作出权威性确认[1]。
1 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渊源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三个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性原则。
1.1 妥当性原则
又称适当性原则、妥适性原则,系指一个法律(或公权力措施)的手段可达到目的之谓也。换言之,就是要求所采取的手段(means)要能够达到所欲追求的法定目的(ends)。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实质的法理内涵就是要求行政手段的正当性或者正确性。也就是说,要求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必须能够达到合法的目的,至少要有助于目的之实现,或者说不能与法定目的相悖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对这一原则的认定上采取最低限度标准,即: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或者全然不适合,就不违反妥当性原则。
在打击“黑车”营运过程中,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车主遵守国家法律,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但在“钓鱼执法”事件中,行政机关的处罚目的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有通过非正当乃至违法犯罪手段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而为自身谋取私利的嫌疑。对实施“钓鱼执法”的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处罚的目的发生了偏离,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甚至是为了某一特定单位创收而罚款。据统计,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一年中就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高达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了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指标任务。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为了行政机关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所谓的“钓鱼执法”行为背离了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因此,“钓鱼执法”的行政机关为获取相应罚没款的目的,就采取诱导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等方式,从而制裁之,即使其已经获得了相关的证据,也因为已严重背离法律的内在目的,而违反了“妥当性”原则。
1.2 必要性原则
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众多能够相同有效达成行政目的的手段中,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或侵害最小的手段。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存在多个能够实现法律目的的行为方式,否则必要性原则无适用的余地;二是在能够实现法律目的的前提下,选择对公民权利自由侵害最轻的方式[2]。对于此原则,魏玛时代的德国学者F.Fleiner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击麻雀(只用鸟枪即可)”,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 “杀鸡焉用宰牛刀”。 对于“最小侵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是以手段对基本权利造成侵害程度来作为标准,然后通过比较来决定那一种手段为最小侵害。也就是说,手段越接近核心保障之基本权利,侵害性就越强;如果触及仅是基本权利保护的外围,则侵害性就较弱。在实践中,该标准可遵循公认的价值观来确定。以公认的价值观,一般认为,限制财产权比限制人身权侵害要小;限制物质权益比限制精神权益侵害要小;负担性的措施比禁止性的措施侵害要小。德国法中,甚至提出了在能实现行政目的的诸方式中,由当事人自由选择侵害较小的方式,这是个更为可行的方法。
“钓鱼执法”,实际上是指行政机关的运用一种近似于刑事诉讼程序中“诱惑侦查”(又称“执法圈套”)方式来调查取证。但即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诱惑侦查的采取也是非常谨慎的,通常认为,诱惑侦查仅是一种补充性、特殊性的侦查手段,不能作为一种常规侦查手段,并且只有在无明显被害人案件、系列犯罪等案件中才允许使用。能够通过其他侦查方法查处的案件尽可能不通过诱惑侦查的方式实现,因为诱惑侦查会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法律后果。因此,在对社会秩序构成最严重破坏的刑事案件的查处过程中,采用诱惑性侦查都是非常之谨慎和小心,并有着严格控制的适用范围。而“钓鱼执法”事件中,非法营运属于轻微违法,其恶性程度远不及刑事犯罪那么严重,而行政机关运用诱惑手段取证以证明相对人违法的行为,则明显违反了比例原则。
“钓鱼执法”并不一定都是非法的,但它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一般只能在刑事侦查中才能使用。并指出:“钓鱼执法”,法律术语称之为诱惑侦查或诱捕侦查,是一种遵循着严格程序和范围的特殊侦查方式,目的是为了获取那些有违法意图或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因此,上海市的“钓鱼执法”是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有着本质的区别,用“钓鱼执法”来查处行政违法案件,就是南辕北辙。因为这种措施和手段与它所要达到的法律目的之间不相称,不成比例。“行政执法必须在阳光下进行,而我国目前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为行政领域的 ‘钓鱼执法’提供法律依据。上海城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做法不仅有违依法行政,同时也有损行政机关的公信力”[3]。
1.3 比例性原则
又称狭义比例原则、合比例性原则、均衡原则、相称性原则或法益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利益的限制或损害不得超过法定目的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必须相称或者成比例。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公共利益的保护与私人权益的保障之间要形成合适的比例;另一个方面,手段的负效用与手段所欲达成的目的之间要有适当比例。因此,问题就是:国家行为所欲达到的公益相较于所侵害的私益是否显失均衡?对于行政权而言,即使满足了妥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要求,也就是说,手段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但假如该手段所损害的公民私人权益,与最终实现的公共利益相比较,两者明显不相称时,行政机关采取的此项措施也就违反了比例性原则,因为公民权益所受的损失超过了行使行政权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就造成了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这就是利益权衡的问题,其要求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时,应当将行政权对公民造成的可能损害与实现法定目的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损害小于利益时才可采取;否则,就不能采取。当然,这就有个标准,简言之,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人类尊严不可侵犯的理念;公益的重要性程度等[2]。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及文献中写道:所谓手段与目的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正当”或“理性”、“均衡”的。也就是日常所言:既不可大题小做,也不可小题大做。付出的成本与取得的收益间应成比例。这就是利益衡量的方法,衡量行政目的所要达成的利益与公民权利损害或社会公益损失之间是否“成比例”,是否“均衡”[4]。
对社会危害性较重的个别犯罪,侦查机关采用诱惑侦查,公众或可接受,可能还没有超越人们的心理预期。但“钓鱼执法”的所针对的只不过是行政违法嫌疑人,其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从其成本和收益的上来权衡,是“得不偿失”的。而这些又都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也丧失了“安身立命”之地。并且“钓鱼执法”也早已逾越了国家机关的道德责任底线,败坏了政府诚信的形象,付出与收益益明显不相称。那最终可能就会如法里斯在《社会解体》所描述的那样,社会与其构成人员的机能关系崩溃,现存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失去影响力,人们反社会的态度得到助长,社会成员的整合、共同感处于欠缺状态[5]。
中国社会调查所针对“钓鱼执法”事件,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的近千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钓鱼式执法”的危害远大于“黑车”,引诱方式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而且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更是对法律的不尊重。抹黑了政府便民、利民、为民的形象。媒体皆言:“钓鱼式执法”让人不敢“善良”。人们将难于判断人们是否是真诚地要进行交易行为或者是否是真切地需要帮助,这种在道路交通中形成的人与人交往时的“怀疑主义”会潜移默化地泛化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信念和习惯,长此以往,和谐社会建设将成为“墙头之草”、“无根之萍”[5]。
姜明安教授认为:“钓鱼执法”事件会对未来行政程序的立法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在这次事件中已经被凸显出来,手段和目的要成比例,并趋于一致,“用大炮打蚊子是荒唐的”。
2 我国行政法实行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我国行政法实行比例原则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行政国”是世界的大趋势,“福利社会”的出现,使得行政职能不断增加,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扩张,行政部门日益拥有广泛的对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管制的职权,负有多种多样的公共服务职责。可以说,行政权渗透到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行政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行政机关的权力能替公民提供福利;另一方面,也能侵害公民的权力和自由[6]。因此,如何确保行政权在达成行政目的的前提下,其所采取的手段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或限制达到最小,便成为公法领域重要课题的重中之重[4]。
从权力的天性来讲,其运行的不变规律仍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要走向滥用和腐败[7]。因此,孟德斯鸠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而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法律力图给赤裸裸的权力统治设置障碍。而行政法所主要关心的乃是法律制度对行政官员和行政机构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所作的约束。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但,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8]。而列举式的限制是不可能的,只有予以比较容易操作的原则性规定,比例原则正好能当其位。
现代法律在权利方面的特征是从自由权本位向福利权本位发展,福利权本位势必使自由权受到某些限制。在公民自由权本位时代,作为一种绝对权的自由权,只有行政权力不干预就能够实现。而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以福利权利为本位,行政以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和福利为职责,行政权力只有积极发挥组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功能才能保障公民福利权利[7]。因此,行政权力在不断扩张,世界各国法律几乎都规定了“立法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保证法律有效对行政权力控制。但还不能有效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为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必须在行政法中明确比例原则,使行政行为作出时,充分权衡,遵循程序,并有司法审查予以救济,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环节按照比例原则去进行控制,就更为有效。
2.2 我国行政法实行比例原则的可行性
孙笑侠称“当代中国法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中国法的形式化或称制度化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推行法治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中国法形式化或制度化的过程”。因此,对行政权的制约、保障公民权利的也要制度化和形式化。十二五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多重推动的形势:政府改革民生的决心,公民维权的意识及意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反映,形成了公民—社会—国家(政府)的多重良性互动,我国逐渐从公民—国家的传统社会模式向公民—社会—国家的现代社会模式转型,社会权利、权力正在培育之中,公民权利的保障多了一重屏藩。国家,尤其是执政党有着推动社会改革的认知及意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障民生”,“依法治国”等治国方略的确立,法治意识增强,法的现代化进程加快。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学界达成共识的地方,国家立法能确立行政法之比例原则,并通过对个案的适用使之具体化。
从对当代中国政治控制机制的实际考察来说,警察式巡查,媒体和上访等“报警”系统等传统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之后遭遇困难。而第三种机制就是行政法——主要是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形式来限制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规范它们的行为。其缺点也转变成为相对有利的优点。首先,行政程序在原来的情况下会影响政府政策的顺利进行,但在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却降低了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的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增强有效地获得真实信息的有效手段。因为,此时上级政府将监控下级政府的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上的其他环节,让新闻媒体、专家、利害关系人来监督政府的行为和决策过程。事前的听证会能防止“生米煮成熟饭”,让事情还有挽救的余地,使行政决策在程序上看起来更公正,保证了这类决策的合法性,因而容易得到被管理人的认同。其次,虽然经验证明这种制度设计仍会遭到下级政府的有效抵制,但是其行政行为和决策不得不受到这种制度的影响。由于这些组织和个人与地方政府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就不存在上下级政府博弈时因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以一对多”的那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后,利害关系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会尽量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声音的愿望远远大于上级巡查官员的检查动力。上级政府因此也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更有效地获得准确的信息,从而更有效地监督和惩戒下级政府。同样如此,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之后,司法审查在这三方面的缺点也转变成为相对有利的优点。因此,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9]。
3 结论
比例原则也就是,行政机关为达成行政目的,要选择有效的手段;如有多种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公民侵害最小的手段;并且手段与目的之间要成比例关系,即因采取此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不得逾越为达成目的而获得的利益。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纲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也就是说,国务院在政策文件中已对“比例原则”作出权威性确认。然而,时至今天依法行政对于很多地方行政机关来说仍是一句空话,“钓鱼执法”就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具力度的反例。因此,继续切实地推进依法行政是必要的。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是有法可依,然而,作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很多重要的法律依然处于立法空白的状态。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制定了行政程序法,以规范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时限及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并且在该法中明确禁止了和否定了带有诱惑他人违法犯罪的“诱惑取证”、“执法圈套”这一类执法方式。在法治化进程中,为规范行政行为,控制公权力滥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亟需立法明确此原则。
[1]周刚志.论行政调查取证行为之合法性控制——兼评上海市闵行区的所谓“钓鱼执法”案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2):124-129.
[2]黄海华.我国台湾地区的比例原则研究 [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43-47.
[3]薛宝库.“钓鱼执法”最终让谁上了钩?[J].吉林人大,2009(11):30-35.
[4]姜昕.公法上比例原则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
[5]张伟,章友德.上海交通“钓鱼执法”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2010(2):75-79.
[6]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1.
[7]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5-186.
[8]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9-386.
[9]贺欣.作为政治控制机制之一的行政法[M]//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7-226.
A Study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Administrative Law——A Case Study of Entrapment in Shanghai
Feng Zhihu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
The case of entrapment proves again that unrestrained power will cause abuse of power easily.It is criticized because i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Generally,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cludes three subprinciples: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has been affirmed authoritatively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the policy documents.During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theruleoflawinChina,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shouldbeclarifiedbylegislationurgently.
Entrapment;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Administrative Law
D912
A
1674-1102(2011)02-0030-04
2011-02-16
冯志华(1973— ),男,安徽望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省计划生育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公法学。
[责任编辑:韩志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