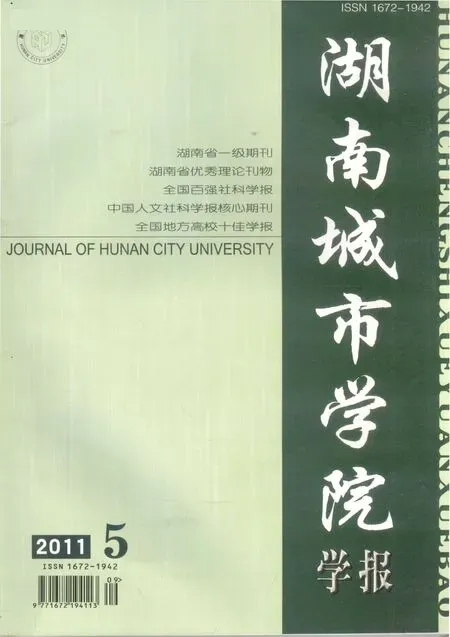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政分府
霍修勇
辛亥武昌首义后,清王朝统治秩序被打破,各地纷纷组建新政权。在原来的省治地方,资产阶级基本按照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建立了军政府。而在少部分省治地方以及道、府、县驻地则显得十分混乱,他们除了直接组建军政府外,还有诸如军政分府、军政支部、总司令部、巡逻部等政权形式。其中,军政分府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911年10月12日,湖北省建立了第一个军政分府——汉口军政分府,随后全国其他地方多有效仿。据初步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组建的军政分府不少于81个。整体上看,军政分府在推进辛亥革命向纵深发展、稳定一方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清末民初地方建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军政分府处于清末民初政治体制的转型期,加之其本身的复杂性,研究者还没有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军政分府的主要类型、组织结构、与军政府的关系、取消过程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辛亥革命时期地方政权的发展演变作一剖析。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军政分府的建立
根据军政分府建立者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以资产阶级下层激进派为主导推动,以资产阶级中上层温和派为中坚发起,以地方军政官员为首的保守派改组等3种主要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占有绝对优势。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在国内设立了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经过数年发动、组织,各省集结了大批反清志士。1911年10月10日,湖北志士吹响了武昌首义的号角,散布各地的同志充当了推翻清朝统治的主力军。按照光复的具体形式,又可把激进派推动建立的军政分府进一步细分为激进派统一领导、当地激进派发动、激进派矛盾斗争使然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激进派统一领导组建军政分府。武昌起义后,昆山同盟会员周梅初等苦于无兵无械,只能焦急等待。上海光复后,王尧民、张栋等“立即往见沪军都督陈其美,请示光复昆山的办法”,陈便将光复责任交给二人,并制订了比较详细的方略。张栋回昆山后,依照指示积极准备。11月6日,发动起义,成立昆山军政分府。[1]13111月8日,上海光复军乘坐钧和兵舰赶到南通,组织军政分府,推举张詧为总司令、许宏恩为军政长。第二种情况为当地激进派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分府。湘西独立前,当地同盟会员田应全、聂仁德等已经取得哥弟会首领唐世钧的支持,11月12日,田等以武力为后盾要求道台朱益浚投诚。“朱见人心反清,大势已去,复函表示愿洁身引退”。次日,“众议决,建立新政权,设‘湘西军政分府’,公推周瑞龙为军政长兼管屯政,聂仁德为行政厅长,张胜林管财政,田应全管交际,韩善培管教育。”[2]278在厦门,11月15日张海珊等带领群众向道台衙门挺进,“翌日,军政分府成立”。[3]116第三种情况为激进派内部斗争使然。辛亥革命酝酿过程中,激进派内部存在矛盾分歧是不容争辩的实事。起义爆发后,他们为争取新政权的主导地位展开了斗争,军政分府的成立,暂时缓和了各派间的冲突,此种情况以汉口、吴淞军政分府为代表。在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的矛盾一直存在,直至1911年9月底,两派才实现松散联合。武昌反正成功后,共进会会员和部分下层官佐拥立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引起文学社成员不满。10月14日詹大悲“会商蒋翊武、张廷辅、蔡济民、王宪章、吴醒汉诸将领,仓卒率兵二连,与蔡济民渡汉,成立军政分府”。[4]汉口军政分府完全由文学社成员组成。在上海,以李燮和为中坚的光复会、以陈其美为领袖的中部同盟会以及地方自治机构代表三种力量共同推动了上海光复,其中光复会员李燮和功绩最著,担任都督的呼声也比较高。11月6日下午,各界代表筹组新政权,主持人李平书提出由李燮和担任都督,但与会者多为陈其美亲信,该提议被否决。随后王钟声力持“非陈君莫属”,蒋介石、刘福彪等则叫嚷请陈其美担任都督!“众无言,公举都督事总算大定”。[5]158-159对于这个结果,光复会部众表示强烈不满,“光复军所部多不愿隶属‘冒牌都督’陈其美之下,吴淞炮台官兵主张尤其激烈”。[6]33-34于是,黄汉湘决定恭迎李燮和赴吴淞,李于9日率部前往称吴淞军政分府都督。
温和派是随着清末新政改革而出现的阶层,它不仅包括地方自治人员,还有随着自治发展而成立的商会、保安团等地方组织。他们多属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人物,对清政府存在一定不满情绪,遂成为光复地方的一支力量。其中,江苏的清江、松江、常熟等军政分府由其发起组成。在全省光复的混乱局面下,清江出现了官兵、土匪哄抢商铺的骚乱。于是,当地士绅组织保安公所,推选闻漱泉出任民政长,“料理善后及维持地方秩序”。11月12日,绅商“公推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为临时江北都督”。[1]33616日,松江士绅知悉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要求各地反正的电报,随后,“城自治公所,即发传单开会,当场宣布独立”,大家“推定钮惕生君为军政部长,谢宰平君为民政长,沈思齐君为执法部长,钱选青君为财政部长,另专设参谋部,为四部之总机关,以提署为松江军政分府司令处”。[7]21在常熟,见风使舵的地方绅士从保护身家性命出发,取得清朝官吏的默许,“也挂上了象征光复的白旗”。[1]199
当革命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清政府注定要被推翻时,以部分清朝地方军政官员为主的保守派也适时调整策略,主动宣布脱离清朝统治。在浙江,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台州后,引起了当地官员恐慌,11月5日驻扎海门的原清军统领雷廷瑞乘乱进城,宣布就任军政分府都督。7日,衢州清军巡防营统领沈大鳌的侄子沈瑞麟、沈增海和巡防营中军游击陈怀玉联络,在商会召开大会,宣告光复。推陈怀玉为军政长,原道台李龙元为参谋长,商会会长孔庆仪为民事长。在延州,原清朝知府余炳文宣布担任军政分府都督。武昌首义爆发后,驻扎郧阳的军队队官沈权、司务长康代瀛、司书生郑家荣等在鼓动军队的同时,也和参事会成员聂炳基、翁人健、刘震川等人进行接洽。11月14日,沈权“遍请绅商学各界人员来会,商议郧阳要公”,在其劝说下,各界代表同意光复。[8]2211月28日,光化县令兼军统黄菼仁,新军官佐张国荃、李秀昂等宣布起义,随后制定了攻取襄阳的计划。30日,成立军政分府,黄被推为分府,管理民事;张国荃为分府司令,管理军事。[8]28
二、军政分府的机构设置及特点
目前,军政分府的数量并没有非常准确的数字,就笔者所掌握的80多个而言,也难以完全知悉其组织结构。不过,从下面列举的分府机构设置,也能够窥测到它们的基本状况:
上海军政分府:都督、司令部、参谋部、军务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部、海军部、外交部。
松江军政分府:都督、军政部、参谋部、民政部、执法部、财政部。
常州军政分府:司令、民政部、审判厅、检察厅。
南通军政分府:司令、总司令处、军政处、民政处、司法处、财政处、司法厅。
扬州军政分府:分府、民政部、执行部、警务部、教育部、财政部。
无锡军政分府:总理、军政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
如皋军政分府:军政分府、民政分府,审判厅、检察厅。
宁波军政分府:都督、副都督、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民政部、执法部、财政部、总务部、外交兼交通部。
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总务科、财政科、军务科、执法科、盐税局、酒捐局、禁烟局。
嘉兴军政分府:都督、总务科、民政科、财政科、司法科、教育科、执法官、参议会。
九江军政分府:都督、炮台总司令、副司令、参谋部、民政部、财政部。
处州军政分府:都督、军政部、民政部。
赣州军政分府:都督、行政公署,法院。
河东军政分府:总司令、兵马节度使、民政部、秘书处、军务处、盐务处、总务司、交通司、财政司、司法司、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
柳州军政分府:总司令、军需部、军械部、军法部、参谋部、执法部、秘书部、邮电部、外勤部。
庐州军政分府:总司令、军政部、民政部、财政部、巡警部、执法部、秘书处、顾问处。
寿州军政分府:总司令、参谋部、民政局、审判厅、支应局。
湘西军政分府:军政长,财政处、交际处、教育部、行政厅。
襄阳军政分府:分府、司令部、参谋部、军政部、政事部。
汉口军政分府:都督、司令处、参谋处、军需处、军政处、军械处、军法处、交涉处、稽查处。
郧阳军政分府:总裁、司令官、军事顾问、军务支部、参谋支部、政事支部。
川南军政分府:都督、军政部、参谋部、民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司法各部。
蜀北军政分府:都督、副都督、军事部、民政部、财政部、交涉部、秘书处、训练处。
登州军政分府:都督、总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民政部、司法部。
和军政府政权相比,分府的组织机构及其职官设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机构设置与军政府极为相似。湖北军政府的建制对各地军政分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九江军政分府成立时,“其内容之组织,均照湖北办理。”[9]144郧阳也“仿省垣章程,组织军政分府”。[8]36但是,毕竟是分府,它们的机构完备程度稍差一些,正如许师慎在回忆九江军政分府组织机构时所说的:“看到上面的组织,似乎较之其他各省的军政府不甚完全。当时我们的意思,认为九江是一个府,不是省会地方,受了人力财力的限制,只能就军事的需要来安配,需要的设立,不需要的不设立,所以不能有一个庞大的组织。”[10]205常州、无锡、如皋、处州、赣州、湘西等分府的机构设置基本都属于这种状况,一方面表明分府的权力覆盖面要比军政府小,另一方面也表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性。
第二,二级机构名称多种多样。如果军政府的基本单位可以说是“部”或“司”的话,军政分府就难以下类似的结论。比如,南通、汉口分府的单位是“处”,绍兴、嘉兴分府是“科”,河东分府则是“部”、“司”、“处”俱全。这说明,分府机构的设置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组织者的认识也是混乱不一。
第三,分府长官权力高度集中。虽然军政分府长官有都督、分府、府长、军政使、司令、总司令、总理等名目,显得比较混乱。但他们的权力却比较集中,江苏省曾经提出,军政使有“管理所辖地方,及防守事宜,执行法律命令,统辖军队,及所属职员,掌其吏事”等权力;浙江规定军政分府府长“处理本府直辖地方一切事务,兼有监督府属各县之权”;[11]四川要求军政分府司令官“统揽地方军事及一切行政大权”。[12]108
第四,军事地位更加突出。革命初期,维护秩序、巩固政权是最主要的任务,加之许多分府驻地本来就是军事重镇。所以,军事机构在分府中所占的比重更大,拥有的地位更高。比如,汉口、柳州都设有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部;襄阳军政分府有司令部、参谋部、军政部;郧阳军政分府为司令官、军事顾问、军务支部、参谋支部等。甚至有人说:“除军事外,悉与旧日知府主管事项无异,而制定于临时,义专于兵事,军兴则假以号召,事定则从而取消之。”[8]38
总之,和军政府的组织机构相比,分府除了稍显简单之外,几乎没有重大差别,这些表明军政分府的“分”字体现更多的是革命的道义和基于传统的统辖心理、统辖关系,而非制度规范上的主动认同。不可否认,这种脆弱的心理依赖,使二者难以建立严格、有序的互动格局,从而导致分府、军政府的之间存在诸多分歧斗争。
三、军政分府与军政府的关系
辛亥革命爆发前,省政权与道、府、州、县政权之间存在比较稳固的统辖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机构的级别上,还蕴含着下级对上级的天然认同感。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地域界限,甚至出现了许许多多个权力中心,这一混乱局面势必影响到分府与军政府的关系定位。
辛亥革命过程中,独立各省基本在省治地方建立军政府,但分府却不同,除了极少数分府外,绝大部分遍布道、府、州、县各地。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被拥戴为中央军政府,各省军政府也是重要的一级机构。在如此复杂的状况下,分府、军政府的关系定位出现了4种类型:
其一,省军政府的下级机构。这种情况比较多,分府一经成立,组织者就积极向军政府汇报情况,以求承认。常德分府首先打电报往长沙,向焦都督报告起义情况,请派人来常德指示进行,“听说焦都督已派杨任(晋康)为西路招讨使,日内启程来常德。消息传来,大家更是兴奋。”[2]263襄阳分府黄菼仁给武昌军政府的电文称:“望示方略并多济军械,实力资助,以期巩固”,已派“专员赴省请领印信、关防、军械,并面禀筹饷练兵保教安民各事宜”。[8]31榕江分府都督吴嘉瑞,任命谢集林为副都督,傅佐卿为靖边营长,赵普扬、倪松农为参赞,“并得贵阳军政府承认。”[13]439通州分府成立后不久,分府总司令处奉到江苏大都督正式委任状,随后作出布告,“自认是苏军都督的辖属”。[14]150
其二,隶属于其他分府。光复前,镇江、扬州两府并无统辖关系,但光复后,两者发生了变化。据回忆,扬州光复时,“街上贴有镇江都督林述庆布告”,讨论扬州政权机关时,林述庆所派帮办李敬臣,“欲置扬州于镇江属下”,“拟名‘镇军都督扬州军政分府’”。[1]296后来,定名为扬州军政分府。未久,李竟成前往招抚分府都督徐宝山,“收其部伍,编为镇军第二师,并令其兼扬州军政分府,防守扬州各属,于是扬州数县,亦归镇军都督所属范围矣。”[9]250
其三,湖北军政府的分出机构。吴淞军政分府成立后,曾明确宣布:本分府“由武昌军政府分出,今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7]5其他军政分府建立过程中,也有人坚持认为革命机关是两级制,“湖北名军政府,各地应直属湖北。”[1]306
其四,与军政府处于并立地位。上海军政分府曾经宣布:“上海之起义,与武昌别为一事,惟随后将与武昌总部联络。即一省之起义亦于武昌全无关涉,惟彼此理想目的皆同,将来终当合并为一,同居一国旗、一政体之下。”[15]344此举无疑表明,分府拥有独立的地位。镇江军政分府成立后,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要求其归属,都督林述庆“怒曰:‘德全衰朽无能,因人成事。予岂下人者,乃藐视予耶。’碎裂来檄。”[16]
分府、军政府之间定位的多样性,直接影响了两者的互动关系,根据两者的互动特点,可以将之归纳为服从型、自主型、矛盾型三种。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前两种类型最为常见,是主导,各地分府基本承认军政府的领导地位,自觉履行有关的权力和义务,尽最大努力推动革命的发展。而第三种类型则显得比较特殊,虽然同为革命政权,但却矛盾重重,它们的斗争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其原因也是纷繁复杂。
四、军政分府的取消
由于分府、军政府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加之分府为了巩固自身政权往往私自扩展势力,致使两者间的磨擦、矛盾日趋升级。为此,有的省军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消解军政分府,取得一定成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和各省军政府一道加紧了取消分府的步伐。
1911年12月,江苏军政府确定省内只设苏州、镇江、上海、江北、徐州5个分府,其中,苏州军政分府管原有之苏州、常州,镇江军政分府管原有之镇江、扬州,上海军政分府管原有之松江、太仓,江北军政分府管原有之淮安、海州、通州、海门,徐州军政分府管原有之徐州。[14]264这样,就从数量上进行了限制。在湖北,军政府于1912年1月中旬颁布《各府县暂时行政规则》,明确告知郧阳分府称:“鄂省境内,无军政分府名义,所拟分府名目,即行取销,改任为郧阳府知事”,进而从制度上否定了分府的合法性。[17]99对于军政府的举措,分府往往为了自身利益与之进行对抗,再加上错综复杂的派别之争,导致整合过程比较缓慢。时人感叹称:“其最甚者,莫过于一省之中,复自为分裂,不相统属。”[18]619
中华民国建立后,这一任务更加紧迫。1912年2月,为了实现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南京临时政府采取强制取消的手段。28日,公布了《陆军部拟裁撤军政分府通告各都督电文》。命令颁布后,各省加快了统一步伐,各地分府纷纷拥护南京临时政府决定,自觉遵令裁撤,只有极少数妄图借助袁世凯的力量与南京临时政府对抗。
广西都督陆荣廷通电命令柳州、梧州、龙州军政分府于3月1日起一律裁撤,“各军政分府总长一律改为统领,为各该辖区军队司令,专管军事。”[19]511这个目标很快实现。3月8日,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知襄阳分府谓:“季雨霖计可抵襄,即望和衷共济,分府名目各处一律取消,以后称为司令处可也。”[8]黄仁菼立即将分府改司令处,照常视事,以待季军,适雨霖至,即以军政、财政、民政移交接管。在浙江,嘉兴首先通电接受中央指示,各军政分府均于1912年4、5月间“遵令撤销”。而绍兴分府王金发却迟迟不肯行动,并派秘书长谢飞麟前往南京,向南京留守黄兴说明利害,“痛陈革命军于革命完成以前不可裁遣,军政分府不可撤销,陈‘三难三可惜’之说。”。[20]75但是,黄兴并未同意。后来,谢飞麟将结果告知,王金发表示接受。
同时,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婉言劝慰军政分府遵守南京临时政府通令,庐州、芜湖两地很快表示同意。庐州分府司令孙万乘称:“先取消分府名义,所有各营军队,请陆军部另委贤接带。”[21]328随后,芜湖分府吴振黄也向南京临时政府表示:“所有皖芜行政一切,均须直接安庆孙都督”。[22]两个军政分府撤销后,“民政统一归省府管辖,军事上成立革命军陆军第十五师,以孙万乘为师长,师部驻芜湖。”[6]391此时,大通军政分府却表现出严重的分裂倾向,分府都督黎宗岳投奔袁世凯,把大通作为黎元洪的前哨,与东南各省同盟会势力争权夺利,公然与南京政府为敌。
3月9日,安徽军政府曾经向南京临时政府禀报,黎宗岳屯兵大通,意图割据。中旬,柏文蔚以陆军部名义电邀黎宗岳派代表到南京与安徽军政府、全皖联合统一会代表协商,各方约定 3月20日前取消分府,“兵归部编,财政、民政、民权,由都督派员接收 ”。[23]但是,黎奉袁世凯让其“仍驻大通”的命令,公开撕毁协议,并于3 月19日致电《共和急进报》叫嚣:“外间传言大通取消军政分府,此系奸人捏造,冀以摇惑军心”,[24]165声称大通分府“断无取消之意”,[21]360这样,柏文蔚等人的和平统一道路被阻碍。
为坚决实现统一政策,3月2 1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命柏文蔚率步兵队二营、机关枪一队、炮队二队、军舰二艘前往大通以武力强制解散。4月初,柏最后一次表达了和平解决的愿望,并派汪菊友、邵逸周等人进行规劝,许以南京留守部次长笼络,但黎表示“愿受北方袁氏节制”。[25]112于是,柏文蔚遂改变策略,率水陆军并进,同时暗中与黎部下胡聘臣接洽,争取了胡的反正。6日,黎宗岳仓皇出逃,8日柏文蔚不费一枪一炮安然抵达大通。至此,安徽的军政分府全部取消。
在江苏,4月4日,吴淞军政分府同意撤销,“所有水陆军队、侦探队,概行移送江防张统制接管;护卫队内部人员概行遣散;吴淞区巡警已移交宝山县民政长接管。”“所有护理吴淞军政分府总司令名义,自阳历3月底,一并取销。”[26]5485月,锡金军政分府撤销,锡军步兵团在充实了一营常州兵员以后改称常州步兵团,直接受江苏都督指挥,不再是无锡的地方武装了。[14]867月15日,陈其美给程德全的电报称,“目下敝处取消在即,所有沪上各军队,均拟即日移交贵处接管,饷项亦请就近另筹。”[26]4078月初,程德全赴上海接收一切事宜。
截止1912年8月底,各地分府基本取消,省内政令不一的局面结束,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目标得以实现,独立各省新的行政关系初步形成,这一成果为进一步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M].南京:江苏人民民出版社, 1961.
[2]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辛亥革命在湖南[M].长沙:岳麓书社, 2001.
[3] 丘廑兢.厦门辛亥革命前后[M]//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4] 佚名.詹大悲先生事略(手稿)[Z].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5] 章天觉.回忆辛亥[M]//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0.
[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7]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 湖北省博物馆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M].武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2.
[10]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M].台北:正中书局, 1976.
[11] 浙省地方官制之规定[N].申报.1911-12-06(1).
[12] 周勇.辛亥革命重庆记事[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6.
[1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七)[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14]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J].1991.
[15] 周育民.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M]//辛亥革命与 20世纪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16] 茅乃登, 茅迺封.辛亥光复南京记事[J].近代史资料, 1957(1):71.
[17]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18] 隗瀛涛, 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1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二)[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20] 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21] 张湘炳, 蒋元卿, 张子仪.辛亥革命在安徽资料汇编[M].合肥:黄山书社, 1991.
[22] 芜湖来电[J].临时政府公报(27号).1912-03-01.
[23] 浦口电报[N].民立报.1912-04-02(1).
[24]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在安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25] 丘权政, 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