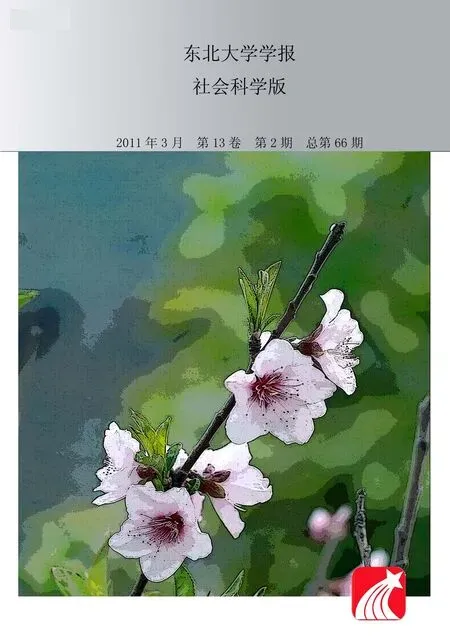遭遇消费时代的尴尬
----从消费景观看新世纪以来文学中的北京
张惠苑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法国哲学家波德利亚说:“正如中世纪社会通过上帝和魔鬼来建立平衡一样,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1]如果让我们反观当下日渐繁荣、充满诱惑的中国城市,再没有比从消费这个角度进行切入更加合适、准确了。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城市正经历着消费主义的形塑,“消费主义文化共同完成了对当代城市文化的重铸与改造,并形成了新的占主流地位的以消费为表征的城市文化形态,与传统的城市文化构成了一种断裂关系”[2]。所以它们表现出与以往城市所不一样的文化特征。都市森林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国际品牌的橱窗里日日更新的时尚潮流讯息正在宣告,生活在当下任何城市都毫无例外地被消费时代拥抱怀中,制造着、享受着或真实或虚假的消费需求*所谓虚假的需求可参考如下解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消费主义文化输出其意识形态,其方法就是通过大众媒体倡导一种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广告、社会舆论等控制和改变人的消费选择,使人产生了一种和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人们被这种‘虚假需求’所牵引着、支配着,而体现为‘自由’、‘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作为人的‘真实需求’却被人淡忘了。”详见刘启春:《略论法兰克福学派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年。。没有城市能够逃离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但是不同的城市对潮流的接受样态又是不一样的:有的城市欣然接受着以消费为表征的城市文化形态,有的城市则在以消费为表征的现代城市文化形态和传统的城市文化形态之间表现尴尬,后者最为典型的代表城市就是北京。
在消费景观下,城市文学中的上海像是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早有了明星的资质,给她一个舞台,就能成为光彩夺目的“上海小姐”。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本身就是具有浓厚消费色彩的城市,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消费时代的讯息一到来,只需一个华丽转身,它就是消费时代的宠儿。而北京作为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和传统的城市,更像一位正处在叛逆期的少年或者思想已经定型的老人,面对消费时代所营造的物质的丰盛、欲望无限膨胀的城市景象,表现出不是赶不上时代的迟钝和不适应,就是十分向往但又手足无措的尴尬。所以中国文学中城市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在同一个角度下,不同的城市会用它固有的城市品性熏陶出不同的城市文学。在城市消费景观下,“尴尬”则能较为准确地概括北京在文学书写中所呈现的特质。这种尴尬表现为城市固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心理对消费时代冲击的排斥、物质丰盛下的精神匮乏与个体认同的危机。
一、城市固有文化品格对消费时代的排斥
北京有着与其他城市一样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繁荣表象。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一方面这个城市有着鲜明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那是永远鲜活的皇城古都的历史与凝固在城市中的传统文化记忆。另一方面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物质的不断丰富刺激着人们欲望的膨胀。这下无底线上不封顶的需求欲望像现代化的战车,推动着这个古老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挺进,并吞噬着这个城市古老的历史痕迹。这就形成一种对峙。这种对峙在其他城市也会存在,大多数城市的应对是:城市的历史和传统在现代化都市景观的压迫下退守到人们的记忆中。北京不同,它的历史是鲜活的,古老的紫禁城要与现代化的CBD中心区在城市中形成对峙,老北京的四合院要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对峙。它们就像“线装书一样孤零零地横插在城市的书架上”[3],就是周围的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吞噬掉这个城市最后一块绿地,闪耀的霓虹灯遮蔽掉这个城市最后一丝月光,也遮盖不了这本线装书孤单背后的清高与自信。这是古老与现代的对峙,是常与变的对峙。所以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在侵入这个城市时遭遇到尴尬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这种尴尬源自于北京城所蕴涵的超稳定性元素,让北京的城市文学中仍多少保持着雍容、大气的传统文化心理。无论北京城市文学再怎样描绘现代大都市的繁华,老北京城和老北京人特有的大气与镇定总让这种浮躁的繁华不能随心所欲地猖狂起来。这种城市文化精神决定着这座城市几千年不变的气象。不管北京高楼盖得有多高,世界名牌在这个城市开了多少家连锁店,胡同里的人们还是过着老北京的生活,“那些老房子里的人家,日子过得精细,好容易攒下了报纸瓶子,自己就上废品收购站卖钱了,哪怕是一根钉子,也别指望老头老太会扔出门去”[4]。如有人评价京沪的流行一样:“上海是一个不玩中国古董的城市,如果她要复古,她也是复欧式的情调;而北京不同,她喜欢从紫禁城里出来的豪华和胡同里的灰色质朴。”[5]占据北京城市记忆的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思想和生活与审美习惯。王小妮在诗歌中曾描绘:“据说宽敞的街道/再三折叠成为弯曲不明的胡同/一把打不开的折扇。/北京城因为他/而滴水不泻/成了一件高不可取的神器。/所有的故事都蒙上密密的天鹅绒。”[6]北京的城墙、胡同以及这些建筑中藏着的几千年说不完的故事,让它成了一个滴水不泻、高不可取的神器。这些积淀,造就了北京的超稳定性,不会随波逐流地为一时时尚所诱惑,改变城市固有的生活节奏。
北京的历史沧桑和大气磅礴构建了这个城市超稳定性的历史空间,而北京人趋于保守和自尊的文化心理决定了这个城市稳定的城市心态。他们对有悖于传统价值理念的事物还是有所忌讳,甚至会挺身而出。最为典型的就是刘一达的小说《画虫儿》的主人公冯爷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北京大爷的心气和做派,用作品里的话说就是“爷气”。他的爷气表现在他的行侠仗义:文革时冯爷可以将被造反派打得奄奄一息、子女避而不见的收藏家钱颢老人,用板车拖到医院抢救;看到被人欺负的流浪女孩石榴,能在自己已经深陷险境的情况下,出手相助;他还将自己收藏的价值连城的齐白石的名画拱手送还给画作原来的主人。作为名声响遍京城书画界的“画虫儿”,他的爷气还表现在他玩赏古玩字画时对职业操守的坚持。当钱大江等人在书画界沽名钓誉、以假充真、扰乱书画市场的时候,他却能见到假画就一把火烧掉,为的就是不能让赝品再次欺世。他还凭借着自己的深沉老辣,在卖画风波中不仅保全了作为钱颢老人收藏的合法继承人小湄的权益,而且也让被金钱引诱丧失了学者品格和骨肉亲情的钱大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揭掉假面具。冯爷对书画的沉迷表现了北京人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他用北京人特有的做派反抗有人利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来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刘一达在《画虫儿》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正的、活在当下的北京人形象。在冯爷身上我们看到沉稳、大气的城市心态在个人身上的体现。而在徐坤的《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中,我们通过旁观一对男女在广场上的三次跳舞,可以窥见北京人保守、顽固的文化心态。小说虽然展现的是男女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博弈,但是通过周围人对这对男女好奇又复杂的猜测,北京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在此一览无余。那对男女无论是穿着还是舞姿都在广场上显得太与众不同了:那个女的穿着时兴的劲爆天鹅裙,超短,飘逸,人一转起来,裙子下摆“沙拉”“沙拉”绽开,露出修长的白腿,随着舞姿闪动还会露出里边平角螺纹镶有蕾丝花边的猩红色的真丝底裤;男的干练,精瘦,浑身哪儿都绷得紧紧的,殷勤环绕她的裙裾伸手抬腿,扭胯耸腰。这样一对男女要是被上海人撞到,他们一定就会像看到一件在电影上才见到的新奇衣服:“一眼一眼地瞟着,吃那裙子的冰激凌,等那人走过去,才转过头去看。那时的眼睛里,飞快地生出一只手,拉开裙子,检查它的裁法与做工;捏一捏布料,了解它的质地;摸一把腰头,看看有没有秘密可以揭短”[7]。上海人的眼睛里透着的是对新奇、时尚的羡慕与挑剔。可是在北京人眼里这些新奇、出位的事物,他们多半会消化不了,因为他们出了格。老北京人不会这样跳舞,大家都是穿着松松垮垮的背心、大裤衩前来跳舞的正派居民。跳舞的风格也该是仨仨俩俩,搂搂抱抱,踢踢踏踏,懒散挪动着脚底下的“北京平四”舞步。对于这样一对出位的跳舞男女,北京人会毫不掩饰地眼光乜斜,态度倨傲地瞟向那对妖冶俗艳的陌生人,而且把身体的距离拉得与他俩远远的,让他们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单独显眼出洋相[8]。从北京人看跳舞看得出北京人中庸自傲的文化性格,他们对自己文化和品格有着自觉的维护和防御心理。这也是北京超稳定性的根源所在。一般流行与新奇是进入不了北京人的法眼的。特有的城市文化特性使这个城市的文学书写与消费时代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中才能让北京无论是追忆过去还是面对现在都能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延续下去。
其次,因为这个城市有着稳固的城市文化品格和文化心理,所以对周围的文化具有吸附和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作家以北京作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时的特殊心态。北京吸引人们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商业气息,更多的是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气息。这是一个文化聚集和交汇的城市,集中了“全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9]。在他们当中有着北京城市文学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北京城市文学中的主人公。比如邱华栋、徐则臣、白连春、李师江等这些作家在北京扎下根前都曾有过在北京漂的经历,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如我(李师江《刀刃上》)、敦煌、边红旗(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民生(徐坤《杏林春暖》)、我(白连春《我爱北京》)等,多少都有自身的投影。这些多少有些诗人气质的文人成为北京的一个群落:“他们埋伏在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角角落落,像沙尘、扬花、空气污染和负氧离子一样,生命力强劲,时而有形,时而无形。……秋分过后,他们又纷纷飘落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红叶诗歌节里,踏着纷纷落叶,吃酒念咒,搅碎一地寺庙的清幽。这些人的人数之众,叹为观止。”[10]对于漂在北京的文人来说,到北京是一种皈依。这种皈依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对精神的追求,对物欲横流现实的反拨,像邱华栋所说:“北京是一种抵达,一种投奔。每当我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看到斑驳的阳光凝聚在那些陈旧的胡同中的老墙上时,一种快感立即就会笼罩我的全身”[11]。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北京的城市文学,不会像上海文学一样书写的都是浑身名牌的红男绿女,消费时代的繁荣能蛊惑和影响城市文学的走向。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北京就是一个承载传统的、可以存放人文理想的城市。北京城市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消费时代的宠儿和艳羡者,对文学的向往和对精神圣土的追随,让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自觉地与城市物欲化的一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二、丰盛下的匮乏:富足与空虚的悖论
回到文本内,可以看到北京的城市文学呈现的城市故事总是与这个大都市的繁华隔了一层。与上海不同,上海的城市文学中多少炫耀着海派的物质富足与对时尚永不疲倦的追求,而在北京的城市文学中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城市苦苦挣扎,但很少有人真正享受到在这个城市消费的快乐。不能完全融入到消费的快乐之中,但又没有批判的自觉。这一点让它与南方的城市文学也不同,广州、深圳等地的城市文学会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批判城市消费景观下的暴力。所以北京的城市文学陷入了一种尴尬,他们没有批判的自觉和勇气,更多的是没有分享到这个城市繁荣与富足后的牢骚和怨气。
在北京城市文学中消费时代物质丰盛的代价是人精神上的匮乏。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没有谁能在城市丰盛场景中过得如鱼得水,他们总是患得患失,在金钱带来的富足与空虚的悖论中煎熬。就像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中的瞿莉,身为身价十几个亿CEO的老婆越是有钱越是没有了安全感。自从有了钱,瞿莉就开始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在家与老公的不断争执,就是做头发,也和周围的美容店吵了个遍。她总是处在不停的担心之中,担心老公变心,担心门口钉皮鞋的换了,担心国家领导人变了,整个世界她都担心。生活的富裕非但没有带给她精神上的安全感,反而成为了她对这个世界不信任的导火线。而对于格非小说《不过是垃圾》中的李家杰来说,金钱带给他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他大学时代不惜用三年的时间苦追苏眉,因为当年苏眉的纯洁是“维持着我们这个肮脏世界仅有的一丝信心”[12]。为了追求苏眉,李家杰不惜追查一切与她有过亲密交往的异性,听说她崇拜运动员,就疯狂练上健美,在身上各处弄出十几块硬邦邦的腱子肉;听说她喜欢加缪,就搜罗所有加缪的书籍并做了1400张读书卡,连带还听上了法语课。可十几年后,身为千万富翁的李家杰,身患绝症后的最后愿望就是再见一次苏眉,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弄到手的东西弄到。结果,当年的纯洁女神竟在300万的诱惑下轻易地委身于他。一切都解构了,李家杰认为这个世界上仅存的、自己最留恋的、唯一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也是一堆垃圾。发迹之后一掷千金的富豪生活,并没有让李家杰在金钱、美女中找到精神的慰藉,相反物质的挥霍和享受带给他的只是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丑陋和自己在精神上的绝望。当纯洁的苏眉也成了他用金钱可以轻易买到手的货品时,李家杰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幻象也崩溃了,所以“他不让家人在墓碑上刻下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在厌倦中死去,不想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12]。格非在他的小说中再现了城市人的精神危机,物质的丰盛不仅不能阻挡人们的精神匮乏,反而会加速人们的彻底绝望。
三、身份认同下的个人危机
消费时代北京遭遇的尴尬还表现在这个城市中对个体身份认同的标准,不是以消费能力或是金钱的多少为标准,而是受传统的价值标准左右。
在北京工作和岗位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没有工作岗位的人即使那么热爱工作,即使不分白昼黑夜地在地下通道忙活,还是免不了被城管逮住的下场”。可是在北京有工作岗位就意味着你是“社会承认的人”[13]。“岗位”和“工作”在北京人的心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在这个城市岗位意味着一种身份和地位。而身份地位在北京又不是完全用金钱多少来衡量,这不同于消费时代用消费能力来评价人的等级。就像徐坤的小说《杏林春暖》中富婆美惠,虽然民生的年轻、帅气、精力旺盛给她带来了刺激和满足,但是当发现民生只是XXTV的一个打工仔,而不是电视台正式在编人员时,她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不舒服,因为她的家人把民生当做进京盲流一类。很多“漂”在北京的人都处在个人身份不被认同的焦虑当中。而如民生一样“漂”在北京的有工作没岗位的人,不仅没有享受到在这个城市消费的荣耀,反而时刻生活在不被这个城市认同的尴尬当中。像温亚军《北京不相信眼泪》中合租在一起的三位女性,都是生活在北京但由于身份的有待认同,而统统陷入能不能被真正接受的焦虑当中。郝倩倩虽然是软件公司的白领,但是在这个城市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人,还要时刻处在有可能被公司裁员的恐惧之中。齐静梅虽为人世故老练,但是终究在这个城市失去了爱人,想通过出卖自己找到一个留在北京的可能和依靠,最终得来的只是被当做妓女的羞辱。女研究生何婷婷,为了北京的户口和工作,与导师发生关系,希望能用怀上的孩子要挟导师离婚,结果却是流产、终身不孕和导师的抛弃。她们都为能在这个城市合理地生活下去奋斗过,但是现实给予她们的只是在这个城市永远的尴尬。在荆永鸣的《大声呼吸》中,饭店小老板刘民,在公园里玩音乐,结果不仅交到了一群土著北京歌友,而且作为指挥还被邀请参加社区里退休居民的“激情演唱会”。本来刘民很有参加的热情,甚至以为在北京找到了自信,从而有些自我陶醉。可是当退休干部老胡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时候,刘民才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北京非主流的地位。当得知刘民只是开饭店的,老胡不禁嘲弄:“我干吗尊重他?他是谁呀?啊?我就看他是个掂大勺的”[14]。刘民在挫败中彻底明白自己在公园里找当年在煤矿搞文艺时候的感觉是错的,在北京你就是个没有岗位、只有工作的外地人。
在北京没有被主流认同的身份,你只能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因为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让很多人为了争取在这个城市有尊严地活下去,而不得不背叛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徐则臣的小说《啊,北京》中,苏北小镇的中学语文教师边红旗,来到北京有着两重身份----“绝对的民间诗人”和“搞假证的二道贩子”。当他终于放下诗人的身段,干起了骑三轮车赚钱营生的时候,却在天桥下十分难堪地被警察扣留了三轮车。这时边红旗彻底发现北京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他悲哀地蹲在桥底下的柱子旁,有那么一会儿想到,即使他死了也没人会知道。……他觉得自己蹲在那儿像个委琐的农民,哼哧哼哧干了这么多天,一辆破三轮车一下子就把他送回了苏北的一个小镇上”[15]。可是当他与房东女儿发生关系,并打起了离婚娶房东女儿从而成为真正北京人的主意的时候,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和家乡。夹在北京和家乡之间的边红旗的身份是尴尬的,在北京他没有被人承认的体面身份,想通过出卖自己和家人来换取在北京的身份,融入到这个城市,最后却是连曾对他一往情深的房东女儿也抛弃他。所以北京文学中的主人公,很多都有着身份的焦虑。因为他们不是这个城市消费的主流,不具备从上往下俯视的资本,所以他们永远都处在从下往上仰视别人的尴尬之中。这种尴尬在压迫他们生活的同时也压迫他们的人格,最终成为他们定格在这个城市永远的生活状态。这些北京消费景观下的边缘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了尴尬的身份,连最初的抱怨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习惯和麻木。
通过对消费景观下城市文学中北京的文学呈现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在作家的笔下北京遭遇的尴尬实际蕴涵着一种价值判断。消费时代带来的是后现代的多元化冲击,对老成持重的北京超稳定性的文化心理构成了一种冲击和挑衅。但是人们还是沉浸在对老北京的怀念与依恋当中。有人曾经用茶壶比喻北京“就像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茶气还是在的”[9]。正是这萦绕不散的茶气,让北京人和写北京的作家退守在北京的怀旧中不能自拔,不自觉地对消费时代的种种讯息流露出一种抵触的情绪,从而忽视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可能。这种忽视导致了北京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消极的解构多于积极的建构的趋向。我们每个人都理应承担起传承历史与传统的责任。但是这种传承应该具有包容和消化的气魄,而不是以毫无选择地彻底解构当下,张扬假、恶、丑为代价。从文本中看,北京的城市文学缺少这种气魄,与北京城大气磅礴的皇家气象相对比,北京文学中透出的更多的是狭隘、固执的小文人心理。北京作家缺少对自我的冷静反观,将所有城市病都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压迫,自然就会像格非小说中主人公一样厌倦一切,唯独忘了最该厌倦和反省的就是自己。所以当我们沉浸在对古老北京过往辉煌历史的无限缅怀与想象的同时,也要警惕在这种怀旧下隐藏着不愿自省的固执与保守和对现实的逃避情绪。如果给新世纪以来的北京城市文学提出点建议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是不是更该思考如何用传统的城市文化心理来融合消费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冲击。唯如此,北京的尴尬才能化解在其大气的城市气象当中,北京的人文精神才能与北京的城市印象相融合。
参考文献:
[1] 让·波德利亚.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前言.
[2] 杜云南. 城市·消费·文学·欲望----城市文学的叙事特征[J]. 理论与创作,2009(2):48-49.
[3] 烘烛. 小院与大院[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92.
[4] 张抗抗. 北京的金山上[J]. 小说月报,2006(1):87.
[5] 于是. 戏说京沪流行地带[J]. 海上文坛,2000(7):24.
[6] 王小妮. 我就在水火之间[J]. 星星,2003(7):8.
[7] 陈丹燕. 上海的风花雪月[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59-160.
[8] 徐坤.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J]. 小说月报,2005(11):24.
[9] 冯唐. 浩浩荡荡的北京[J]. 人民文学,2005(10):111.
[10] 徐坤. 杏林春暖[J]. 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1):6.
[11] 邱华栋. 北京的驳杂[J]. 海上文坛,2005(7):6.
[12] 格非. 不过是垃圾[J]. 小说月报,2006(4):6-15.
[13] 李师江. 刀刃上[J]. 花城,2004(3):101.
[14] 荆永鸣. 大声呼吸[J]. 人民文学,2005(9):49.
[15] 徐则臣. 啊,北京[J]. 人民文学,2004(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