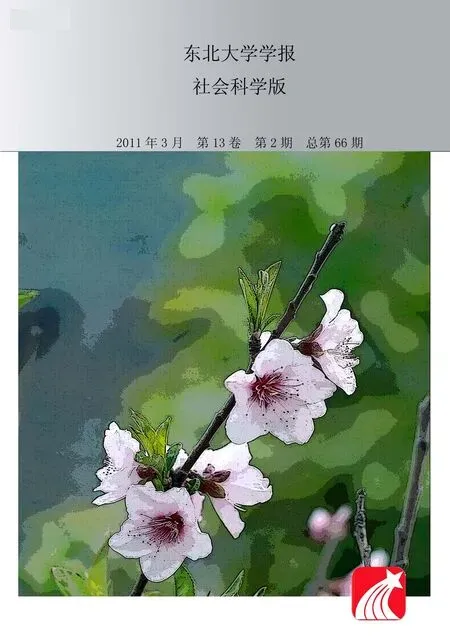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金敬红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本杰明的作品及影响剧增,使得本杰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及现代美学批评家之一。本杰明将历史唯物主义、德国的理想主义以及犹太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为西方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翻译了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风貌》(TableauxParisiens),而他为《巴黎风貌》所写的绪言《译者的任务》(TheTaskoftheTranslator)则体现了本杰明的主要翻译观。《译者的任务》是翻译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甚至有人将其喻为翻译界的《圣经》。德曼(Paul de Man)认为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非常经典,“在这个学科里,如果一个人没有对本杰明的这篇文章进行过阐释的话,那么他是没有地位的”[1]。
当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翻译《荷马》(Homer)时,给柏林顿伯爵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译者的描述:蒲柏问书商林托特,既然你谈到了译者,你是怎样管理他们的呢?林托特回答说:“那是一群世界上最令人头疼的人,一群无赖,他们饥饿难耐,还发誓他们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2]蒲柏想要表达的是:译者位于社会的边缘地位;翻译失败时,永远是译文、译者的失败。本杰明之后,这一“场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存在于作者和译者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分界线是没有道理的。
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纯语言”观,“纯语言”观挑战了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解构了译者的边缘地位,重构了译者的重要地位,而德曼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译者的任务》的阐释则证明了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者可以成为原文的“保护者”。
一、本杰明的“纯语言”观:“忠实”神话的解构
本杰明是犹太人,笃信宗教,几乎将宗教虔诚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其“纯语言”观受到他所信仰的犹太教的影响。本杰明的语言哲学的核心来自德国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犹太教哲学传统往往把语言的起源追溯到上帝,德国的这些哲学传统对本杰明的“纯语言”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本杰明也受到了如洪堡等学者的影响,洪堡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语言“共源”问题,对本杰明的影响很大。
和洪堡一样,本杰明认为语言和思维密切相关,致力于探讨语言“共源”(unity of language)现象。他认为“因为句子与思维相关,句子更能够清楚地体现语言的普遍性和可译性”[3]。对本杰明来说,“上帝创世”解释了语言“共源”和语言多样性问题。本杰明的语言哲学是:与“上帝创世”密切相关的语言“共源”在时间上先于语言多样性的出现。本杰明认为“翻译可以解释语言‘共源’现象。如果语言的多样性来自语言‘共源’现象的话,那么翻译不仅可能,而且是人类语言实践的独有形式”[3]。语言的“共源”现象是本杰明“纯语言”观的基石。
本杰明认为“纯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是由翻译体现的。本杰明提出的所谓“纯语言”就是体现在人类各种具体语言中的语言共性。本杰明认为“纯语言”在人类犯了“原罪”被从伊甸园赶出后就远离了人类。本杰明强调“‘纯语言’没有任何形式,除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听众。它意味着人与上帝交谈”[4]。本杰明也强调“‘纯语言’没有内容,是人类无法触及的,因此通常条件下不能够揭示语言‘共源’问题,只有在出现‘极剧烈的碰撞’的条件时才会出现,这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翻译”[5]。翻译须要在两种语言、两个文本发生极剧烈的“碰撞”的情况下实现,因此本杰明为翻译设定的目标比“达到交际目标”的浪漫观点更加浪漫,他认为语言交流只传达表面的意思,而翻译则表达各种语言间及各种语言与“纯语言”间的相互关系。
德曼是这样解释本杰明的“纯语言”的实质的:“本杰明认为翻译是一种破裂变为碎片的行为,正如瓦罐已经在不断地断裂,翻译是碎片的碎片。……但是从来也没有形成瓦罐,我们对瓦罐一点也不了解,没有一点意识,也不知如何接近它。”[6]91本杰明的“瓦罐之喻”显然带有虚无色彩,但是它体现了本杰明语言理论的基本主题:语言是破碎的,即“纯语言”已经破碎,破碎为人类的各种语言,但是“纯语言”的现实永远不会实现。“纯语言”瓦罐的实质是断裂的,翻译只是这一断裂的具体体现。因此,德曼的结论是:“本杰明没有说部分语言残片可以构成‘纯语言’的全部,他告诉我们残片只是残片,永远处于残片的状态。残片永远不会构成一个整体”[6]82。这就是“纯语言”的实质,它已经断裂成为一个个残片。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杰明阐述道:“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状态,因为人类有翻译能力,因此不同语言间的裂缝可以弥补,尽管这种弥补是有限的。将人类的各种语言拉得更近的翻译行为也把人类与‘纯语言’的距离拉得更近。”[7]本杰明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那个理想的“纯语言”。本杰明认为语言间存在一种“亲缘关系”,一种超越历史与认知的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来自于“纯语言”。“这种关系是每种语言都试图表达的‘那个东西’,但又不是任何一种语言能表达的,只能由所有语言的‘意图’表达出来。只有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文本产生冲撞时,不同的意思才会相互影响、产生变化,人类离‘纯语言’的距离才会更近。”[7]在本杰明看来翻译将人类与“纯语言”的距离缩短,但是却永远不能达到“纯语言”的境界,以此本杰明将翻译“神圣化”,而译者就是担负这一神圣使命的那个人。
但是译者怎样担负使命,实现原文到译文之间的转换的呢?本杰明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喻来说明译文和原文的关系:如果原文是一个圆,那么译文就是一条切线。切线不是试图模仿或者再造一个圆,切线只是在重要的一点上“掠过”,然后就朝着“无限”继续行进。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模仿再造原文,而是为了继续自己的旅程,在一个可以有无限个可能的小点上保留原文的意思,而无限的行程则显示出翻译是可以多么地自由。这幅图景中最漂亮的就是那个相切点。“切点在翻译的无限可能性上弹跳,而每一个切点,作为一个那条线上的无数点中的一个也改变了那条切线。这条线的无限是一个显示无限的信号,它总是存在,总是处于超然的状态,它就是那个存在于所有语言的内心深处的‘纯语言’。”[7]本杰明在这里阐明译文须要在那个切点上实现“忠实”,但是要求译者要达到绝对地“忠实”是不现实的。
本杰明认为破碎的各种语言也决定了原文本身就处于一种“偏离、迷失、永远的流离失所”(a wandering,an errance,a kind of permanent exile)的状态。虽然开始时有一个“纯语言”,而“纯语言”只是作为永远的“断离”(disarticulation)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中。这种“断离”当然也存在于自己的母语中,本杰明甚至极端地认为“自己的母语是最可能使人背井离乡、最使人觉得陌生的东西”[8]。所以译者的任务就是:“将流放在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体现在所译的语言中,将囚禁在作品中的‘纯语言’体现在译者创造的译文中。”[9]译者就是那个能够感悟到“纯语言”的人,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极大的自由的那个人。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杰明摒弃“译文必须忠实原文”的观点,认为译者的任务与诗人的任务不同,诗人的创作是即席的、形象的;而译者的任务是获得的、最终的。人用语言作为媒介记录自己的经历,而人类的苦恼也在于人类使用语言进行描写时,语言所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译者在两种语言间进行思考,译者注定对诗人是不忠的,就像诗人在描写自己的经历时不会是百分之百的忠实一样。其原因不是译者的失败,而是语言本身的变化莫测。德曼是这样描述翻译的:“译文揭示出原文总是存在无法表达的现象。”[6]82德曼坚持认为“这种失败的原因不是人类的失败,而是语言的失败”[6]82。
二、德曼翻译本杰明:译者可以使原文本“再生”
德曼之前,我们可能会认为:“翻译的每个定义都界定译者是失败的。任何一个译文就其原文来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6]80。德曼之后译者可以安慰自己,因为译文失败的原因是语言功能的失败。德曼在他的论文《结论:沃尔特的译者的任务》(Conclusions:Walter'sTheTaskofTheTranslator)中提出了译文给原文带来“致命性”的可能这一观点,这篇文章是德曼翻译了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写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本身也构成了一篇经典的关于翻译的论文。
德曼认为本杰明要强调的是:译者的任务与职责不是重新找到原文的意思,而是通过将原文还原到“纯语言”的方式完成使原文放弃它在译文中想要说一切的愿望。德曼在翻译本杰明的文章中实践了这一点,他是这样描述的:译者从原文中选择一个词或一个隐喻,“随心所欲”地翻译它。本杰明认为文学译本是文学作品的“再生”,在这些译本中,原作的生命得到了丰富,本杰明在文中称为膨胀、发展、变化、延续。德曼是这样解释本杰明的观点的,译文不与原文的生命有关系,而与其死亡有关系:“原文早已死亡,译文是原文的‘再生’生命,译文重申了原文已经死亡”[1]。德曼在翻译了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曾作过这样的论述:译文是死亡的先兆,“通过毁灭性地和恐怖性地使用语言,译文将原文从一个深渊扔到了另一个深渊,直到它消失在语言的无底的深渊,译文便以这样的方式杀死了原文”[1]。译者便以一种近似“暴力”的方式使得原文和译文都暗示了“纯语言”的存在。
对德曼来说,要暗示“纯语言”的存在,译者要采取逐字翻译,其目的是打碎句子的明显的稳定性,在其中引进一种使原文能量得到损耗的机制,由此原文的意思就会消失、隐没,对意思的控制也会消失。但德曼认为消失的意思很明显不是全部的意思,失去的只是自己在原文中的意思,失去的对词的控制也只是在原文中对词的控制,而原文对词的控制则体现在译文中。本杰明认为“原文的稳定性被解构了,而赋予译文一种最终的、经典的形式”[6]82。从一开始的迷失,译文反戈一击,将它的迷失、它的失败反射回了原文。译文似乎由于处于从属地位的失败揭示了一个实质性的失败,因为“纯语言”作为永远的“断离”存在于任何语言中,即任何语言的表达式都存在着其局限性。
本杰明是这样讨论“再生”的:与其说译文源自原文的生命,毋宁说它是原文的“再生”。因为译文晚于原作,译文标志着原文生命的延续。他的“瓦罐之喻”就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原作、译作以及“纯语言”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把罐子的所有碎片重新黏合成为罐子----实质上的另一只罐子,那么碎片必须能彼此吻合。同样,译作虽然不必与原作一模一样,但译者却必须将原作的表现方式准确地再现出来,从而使译作和原作都成为一种更伟大的语言----“纯语言”----的可辨认的碎片,好像它们原本就属于一个罐子似的。本杰明强调所有这些都是由译者实现的,译者实现了原文的“再生”。
三、德里达翻译本杰明:译者是原文本的“保护者”
同德曼一样,德里达在翻译了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也写了一篇关于翻译的论文DesToursdeBabel。与德曼不同,德里达在论文里探讨了隐藏在翻译的失败后面的“保护性”可能。德里达认为翻译的失败遮掩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个是致命性的,一个是保护性的。
德里达认为本杰明想要强调,翻译是“译者注定要承担,要进行投入的一个任务、一个使命,译者注定要投入精力、承担责任”[1]。德里达指出译者的责任是继承者的责任,是保证原文能够获生并且继续生存下去的获生者的责任。译者赋予原文的“再生”不仅仅是超越作者的生命和死亡的“再生”,它更是一种“生命后的生命”。德里达相信译者不仅可以使原文生存更长的时间,而且可以生存得更好,获得更多,而这些都超出了原作者所能及的范围。因此,译者的任务不仅仅局限在将原作的内容传达出去,提供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而是要保证原作“种子”的“生长”。斯坦纳也有同样的论述:译文可以回报原文,译文可以给原文后续的影响,使得原文在不同地域文化里“再生”,而这种能力是原文没有的。译文可以使在原文的外衣下被低估了的、被忽视了的作品获得应有的地位。斯坦纳指出:“福克纳的作品就是其译文在法国大获成功后才在美国得到了应有的反响。”[10]
在德里达所译的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中,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建立在它们的不同点上。这种原文和译文的联合取决于两个文本的差异:“当两个完全不同的双方结合到一起时,译文和原文就达到了一种结合,译文与原文相互补充便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语言’----‘纯语言’,在这个‘再生’的过程中,译文和原文两者都产生了变化。”[11]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翻译契约”。两个文本的“契约”以互补为基础,原文须要被补充,因为一开始时原文并不是没有缺陷,它不完整也不自立。译者必须通过在原文中增加或补充原文没有的东西来挽救译文和所要翻译的文本。这意味着译文不会像德曼所认为的那样,以译者想怎样译就怎样译的方式来翻译,德里达强调:“译文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成长----这就是本杰明的‘种子’逻辑----译文不是以任何随意的形式成长”[1]。语言的“偏离、迷失、永远的流离失所”不会使译文漫无边际地去任何地方,译文不会超出原文的范围。“种子”逻辑指的是译文必须从原文那得到成长的指令,必须保证译文是原文成长的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原文和译文是一致的,或者译文不会偏离原文。但是译文至少应该在几个点上与原文相符:分享与原文相同的目的,遵守原文的指令,成为原文的补充。译者通过从原文中解放出来译文,而使译文不走原文的路线的方式补充原文,保护原文。译者还可以用原文处于不被破坏、不被动过的方式构建与原文完全不同的译文,其结果是构建了一个作为“原文”的译文。一个文本因为只有自己是原文才能去补充另一个原文,才会反过来须要补充。也可以这样表达,原文因为另一个“原文”而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原来的生命也因此获得了“再生”。
德里达在他的文章DesToursdeBabel中将这些新但也旧的观点引入了翻译,这篇论文的英文译者格雷汉姆 (Joseph Graham) 发现题目可以有很多译法。德里达提醒我们在希伯莱文中,“Babel”既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巴比塔”,也是一个普通名词,意思是“混乱”。闪米特人的儿子们试图建造一个通天塔,给自己留一个名字,当上帝把塔毁掉时,语言就陷入了混乱。德里达论文的题目DesToursdeBabel本身就是一个“混乱”的例子,通过其题目的不可译性,德里达试图说明“后巴比塔时代”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不可能,语言本身表明意思时功能的不足,以及译者无法面对多样性而进行补充这一事实。
因此译者承担了一个“永无休止的任务”,翻译成为一个显示原文“内在不完整”的标志。而翻译的失败也是它的成功,因为语言和文本的不完整性,才使不同的文本、语言有了互相结合的必要和可能。译者“永无休止的任务”就是促进本杰明所说的“语言间的和解”,其方式是使每种语言都需要另一种语言,互相指引而走向一个永恒的“纯语言”,而每一种语言都是这个永恒的“纯语言”的一部分。
四、结 语
德曼对本杰明“纯语言”观的解释证明了译文可以颠覆原文,而德里达则证明了译文对原文的保护作用,两个证明看似矛盾,也正充分说明了本杰明“纯语言”观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本杰明的“纯语言”观及德曼和德里达的对“纯语言”观的阐释证明了译者的价值,译者成为那个通过翻译而将我们与“纯语言”的距离缩小的那个人,译者不必时刻戴着必须永远忠实原文的“紧箍咒”,因为原文开始时可能就有缺陷,语言功能也是有限的,如果译文失败,也不是译者的失败。本杰明的“再生”说和德里达的翻译的“保护性”彰显了译者的重要地位,将译者从文化的边缘地位拯救了出来。
翻译是一种作者、译者和读者卷入、介于两种语言的交际行为。詹姆逊(Jameson)讲到的“语言牢房”以及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说的“语言规约”是进行翻译时所有译者经历的痛苦的原因。译者以及译文决不会禁锢在一种语言里,译者要跨越双语(或多语)迂回在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与另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之间、一种翻译方法和另一种翻译方法之间。译者就是那个要讲两种语言,介于不同文化之间,介于不同文本之间,使用不同翻译方法,要对文本进行增补的那个关键的人。
当译者不能将意思完整地从一种语言的能指传达到另一种语言的能指时,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环境的语言结合到一起便成为译者的重要任务。在缺少合适的意思的情况下,当每一个单词都有众多可能译法的情况下,翻译不仅成为一个要翻译的那个单词里有什么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看到听到了什么的问题,更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没有听到什么的问题。翻译已不再被局限在单一语言结构中,而是一种译者会面临众多的可能性,使用不同翻译技巧的行为。
诚然本杰明的“纯语言”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他的论述“解构”了不少传统的翻译观念,本杰明关于原作和译作的互补关系,挑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原则,消除了长期存在于传统翻译理论中译作和原作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构了译者的重要地位。本杰明的见解独到,非常人所能达到。他的语言理论在时下将语言只作为工具的情形下----如赤裸裸的广告语言,穿上所谓网络语言的外衣对语言的扭曲与变形----将语言神圣化,这是我们不得不钦佩的。如果我们对本杰明的论述角度有不同的看法的话,至少他研究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参考文献:
[1] Bannet E T. The Scene of Translation: After Jakobson,Benjamin,de Man,and Derrida[J]. New Literary History,1993,24(3):577-596.
[2] Pope A. Letters of Alexander Pope[M]. London: Press of Oxford University,1960:92.
[3] Britt B. Romantic Roots of the Debate on the Buber-Rosenzweig Bible[J]. Prooftexts: A Journal of Jewish Literary History,2000,20(3):262-293.
[4] Boer R. From Plato to Adam: the Biblical Exegesis of Walter Benjamin[J].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2007,3(1):1-13.
[5] Benjamin W.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M]. New York: Schocken,1986:333.
[6] De Man P.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7] Smerick C M. “And G-d said”: Language,Translation,and Scripture in Two Works by Walter Benjamin[J]. Shofar,2009,27(2):48-69.
[8] McGuire J. Forked Tongues,Marginal Bodies: Writing as Translation in Khatibi[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1992,23(1):107-117.
[9] Bullock M,Jennings M W. Selected Writings: Vol. 1,1912-1926 [M]. Cambridge,MA: Belknap,1996:261.
[10]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416.
[11] Graham J.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