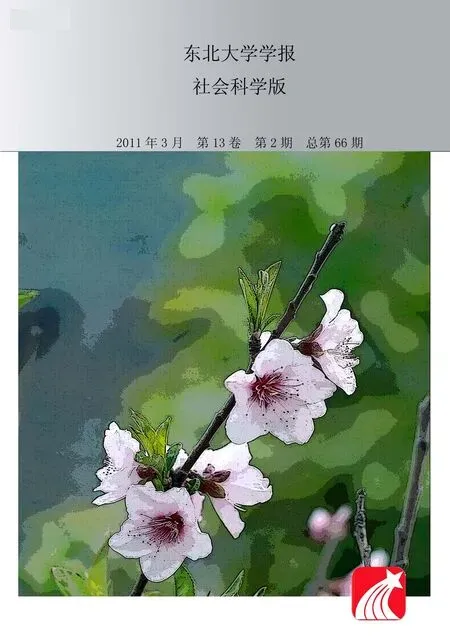作为历史意识的技术创新
陈玉林,尹恩忠
(1.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2.沈阳军区军械训练队,辽宁铁岭 112611)
国内一些学者呼吁,在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研究中,要用技术创新概念来取代技术发明和技术实体概念。他们指出当代技术创新研究主要着眼于“现实的创新状况的逻辑分析,缺乏历史感”,隐含着“现代性”前提和经济学视角;阐明了技术是一个过程,以及技术创新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地位[1-3]。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提供了启示。不过要把技术创新概念作为历史分析工具应用到技术史研究中,有些问题就还有待澄清。比如,为什么当前的技术史研究聚焦于技术创新?它将采用什么研究路径?技术创新范畴怎样才能适用于古代社会?这样,我们就必须跳出现代性和经济学的束缚,探讨适合技术史研究的“技术创新”范畴。这须要借助历史视角和文化多元主义视角。故而我们从考察人们理解技术的历史意识入手。
一、历史意识中的技术
所谓历史意识,就是将过去的时间经验通过身体体验、感知、回忆等转化为当下和未来生活实践导向的文化活动。因此所谓历史意识中的技术,指的是人们对于技术在这种联结过去、现在并导向未来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的各种心态和观念;涉及人们过去的技术经验、当下的技术实践以及技术的未来图景,是认知、审美与政治维度的统一。根据语言文化分析视角,下面我们对历史上一些进入到人们日常语言中的技术概念进行历史考察,以展示技术在人们的心态和历史意识中的变迁,从而思考“技术创新”进入当代历史意识核心的必然性。
在古代,技术尚未自觉进入人们的历史意识中。西方古代涉及技术范畴的一些概念中,指抽象技能的主要是“艺术”(arts)、“手艺”(crafts)和“技能”(techne)等;指实体的概念则主要与工匠的作坊、工具和制品相关。对于“艺术”范畴,社会精英着重强调的是与政治修辞相关的“自由艺术”(liberal or fine arts),而与军事工程相关的“军事艺术”(military arts)则直到中世纪才逐步成为日常用语,因为这时它已与逐步发展的技术教育以及一种职业(工程师)相关了。这些概念表明,与技术相关的范畴都是社会底层民众的事情,从而技术以及从事技术活动的人们都被排斥在历史意识之外,占据历史意识核心的是政治精英和战争英雄。虽然神话史、英雄史诗、传记谱系等历史叙事中也会涉及某些技术物,但相较传记主人而言,它们的作用完全被遮蔽;随后的编年史、叙事史也都完全没有涉及技术的历史作用。
随着技术教育的扩展、民用工程的发展、工业的逐步崛起以及技术革命的到来,与机械和民用工程有关的技术得到了发展。从而在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期间,“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s)和“实用艺术”(useful arts),“工业”和“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以及作为“军事工程”与“民用工程”之统称的“工程”概念进入日常用语中,并把传统的手工业领域的“技能”和“手艺”范畴驱逐到社会身份的更低层次上。“技术”这个词也于1615年首次出现在英国的文献中,是指关于艺术的描述,特指机械艺术。这些概念与当时技术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联。技术教育逐渐由在店铺中开展的学徒教育向在学校中实现的知识和技能教育发展,这些概念也就成为技术教育家和技术人员实现从“店铺文化”(shop culture)向“学校文化”(school culture)的社会转型的话语工具。这既与培根主义相关联,也与韦伯、默顿所讨论的新教文化紧密相联。在此过程中,技术作为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尘世生活的实用工具,进入到历史意识中。18世纪各种版本的《百科全书》、《艺术与工艺辞典》的出版以及它们在大众中的普及,就是技术的历史意识普遍增长的最突出证据[4]。到19世纪初,技术史专著也已在德国出现。这种历史意识既推动了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推动了技术精英主义文化的普及。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美国,机械艺术在技术物和社会组织两方面都以系统的方式得到组织和发展,形成为“社会—技术系统”----首先是铁道系统、装配线系统,后来则是电力网络、化学工业以及军事—工业—大学综合体的形成[5]。这种发展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精英主义相伴,技术作为一元的、理性的历史推动力进入到人们的历史意识中。典型的表现是:技术的“应用科学”文化占据了文化主流;“应用科学”、“工程科学”观念深入人心,它把科学理性当做技术规范,技术理性成为座架。科学知识及其教育体制日益垄断技术实践,技术和工程日益“科学化”和一元化[6]。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共同体和专家统治共同体日益庞大并牢牢控制着既成权力组织。这样,“技术”作为综合概念,就把知识、人工物、专家组织和实践活动建构成强调内在一致性的范畴,并牢牢掌控了人们创造历史的热情。技术成为具有自身内在发展逻辑并驾驭着历史进程的“勾勒姆”,这使技术本身免于社会学分析。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可以说是这种体制的最终总结[7]。
然而,该报告也激发了“二战”后人们对社会—技术体系的警觉意识。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则强化了公众对技术综合体的忧虑与关注,于是,一种新的批判性历史意识逐渐占据文化主流。人们质疑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线性过程及其前提----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在质疑的目光中,技术变迁与发展显露了它的本来面目----它是各种异质要素编织成网络的创新过程。它不仅涉及熊彼特狭义的技术创新所定义的企业家、资本与技术条件等要素,而且广泛涉及各种文化群体及其意识形态。因此说技术变迁内在包含着复杂性与多种不确定性,比如革新成败的偶然性、对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由技术引发的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性----即历史的不确定性。由此,人们不再信任由少数技术精英来决定技术的未来走向或任由他们来驾驭历史进程;也意识到技术已成为我们协商未来的强大资源,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这种协商。换言之,技术作用于历史进程的方式并非通过技术物,而是通过这一整个创新过程----历史语境中的技术是一个过程而非固化的实体。
无疑,这种技术历史意识不可能借助静态的“技术发明”或“技术物”概念来展现,也不能借助包含线性发展观念的“应用科学”或包含技术精英主义历史观并强调一元化的“技术”来得到体现。进而言之,休斯为技术史确立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虽然旨在系统分析技术—社会的相互建构,但却过于依赖结构功能论而对组分的冲突性、异质性和个体能动性失于考察。即使是建构论者提出的批判性概念“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也由于它主要集中于考察认知过程而忽略了改造世界的历史意义,所以也只能作为开启上述技术历史意识的先导,却不能全面涵盖这种历史意识。基于此,一些技术史家已敏锐地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化来表达这些历史意识,以填补话语空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技术创新概念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承担这种历史责任?
二、作为文化实践的技术创新
马克思曾给人下过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定义,即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表明,技术创新是自古伴随人类历史进程的;自古以来,技术发明就通过普通大众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使用中[8]。而以市场和企业为媒介的技术创新模式仅仅只是技术创新史的阶段与模式之一。这样,我们就能从人类创造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理解技术创新,虽然只是近年来更多人才认识到自己通过技术创新塑造未来的能动性。下面我们将要探讨的就是该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概念包含哪些重要含义。
1. 技术创新用历史过程的观念取代了技术的静态理解
远德玉先生的技术过程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技术形态论。“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9]其二,技术历史过程论。技术是目的与手段的动态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10]。其三,技术创新论。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11]在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从过程创新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12]25。其四,产业技术论。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社会化了的技术。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12]27。由此,王大洲指出,技术作为过程存在就意味着技术作为一种关系存在。远先生这样概括:技术过程论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技术存在于过程中;二是技术是一种过程性存在,……关键是引入了时间的观念,任何技术都有历史。技术是在形态转化过程中不断地负载了价值。如果起点上无价值,终点才有价值,就无所谓价值的异化。
上述过程论的重要贡献在于,用动态产业技术系统(建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统一了----更重要的是扩展----技术的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的观念,并引入了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这一理论堪与西方著名技术史家休斯(Thomas Hughes)的技术系统论相媲美。但是,笔者认为,两位技术史家的思想还有以下方面有待拓展。其一,两位技术史家异曲同工的是,都强调技术的系统论,带有结构—功能主义假设。因此,正如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所批评的,技术系统的结构并非稳固,系统的功能也非单一、有一致的目的性[13]。其二,隐含着企业家精英主义立场而忽视了用户、使用过程和其他普通大众以及文化的异质性对技术的作用。对于这两个主要方面,我们将通过文化实践概念来进行拓展,除此之外,还将重新审视技术实体的问题。
2. 技术创新是文化实践过程
为什么把技术创新理解为文化实践?这是因为如上文所述,现代性过程中对技术不确定性的轻视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已使人们质疑技术专家统治论的话语教条。技术并非其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也不是跟随纯粹的市场力量或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发展,而是深深嵌入利益争夺、权力分配、身份界定以及个人偏好之网中。从而,技术发展与变迁就应该是广泛的异质要素参与、协商和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已不能由原来的自然实在、技术实体、经济基础、国家与阶级、社会背景等实体性概念所涵盖,而必须寻求跨学科策略;也不能仅仅藉由结构功能统一性或目的一致性来得到说明,还必须考虑另一面即冲突性、异质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样,“文化”概念就凸现了它的重要性,即重构和融通社会科学的潜力[14]。在此语境下,技术创新作为文化实践来理解,有多方面的解释力优越性。
其一,从文化实践视角理解的技术创新,重构对技术物和技术知识实体概念的理解。远先生在阐述技术过程论时也声明并不排斥技术实体概念的解释功能,但他和休斯都未进一步深入讨论过程论如何重构对技术实体的理解。笔者主张,要把这些技术实体(发明、制品、技术知识)置于技术变迁、技术使用与日常生活化的过程中来理解,从而这些技术的静态特征就被一种历史意识所激活而成为人类日常生活和历史活动的流变过程的某些要素与环节。由此,一种精英主义被质疑:技术物就不再被视为不可更改的、由生产者所决定的功能实体;相反它们被使用者带入日常生活中,其意义和功能都依据具体情境而得到重构和修改(就像读者重构“本文”的意义一样),人们也由此意识到自身参与到技术创新和技术的历史意义的协商与再定义过程中。换言之,作为文化实践的技术创新所激活的历史意识能使人们自觉自信地意识到自身的参与性。我们以此意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我国许多传统工艺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实现创新的:在自然环境、用户的意见和其他生活情境共同构建的技术活动中,通过不断协商来实现创新。当今的许多创新也不例外:许多的技术物进入到使用者手中,其意义和功能不断得到协商和再定义并导致新的创新[15]。这样,与确定的精英相连的发明以及技术产品就显示出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本属性;技术也显现为多重意义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大众协商未来的重要途径。
其二,文化实践视角的技术创新凸现行动者个体创造历史的能动性。一旦文化视角质疑了关于“社会实体”的那一套话语,它就引领我们重新思考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思考的起点则是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形式。技术创新作为文化实践,则正是这种能动性的重要形式。按当前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套与个人或群体的所信、所行、所知、所感和所好相关以及他们怎样与他人、自然相连的意义所组成的网络,它表征的是一组一组的关系。这个意义网络唯有从行动者的能动性、意图、互动层面着手才能得到更好理解。因此文化视角就突出了行动者的地位。技术创新作为文化实践也如此。技术创新的文化视角不仅质疑了社会史视角中的技术制造者、控制者、辅助者等那一套以“经济基础”、“社会背景”范畴表述的社会结构与情势概念,而且质疑了社会建构论者的“相关社会群体”概念。由此,技术创新所展现的就是行动者调用技术、身体、自然、文化、组织等异质性要素建构“杂交体”的过程,该杂交体是一种意义网络,也是关系网络、权力资本分配网络(比如布迪厄的主张)[16]、信息交流网络(休斯的观点)*这里引用的是休斯的一份手稿: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A Historian's Perspective。在此特别感谢休斯先生惠赠这些重要资料。也可参见本文所引的休斯的其他著作。。关于技术创新的这种组织功能下文再详述,这里则旨在强调行动者的实践能动性。从文化实践视角考察技术,它就绝不仅限于少数发明家、企业家,而是涉及广泛的行动者即拉都尔所指的异质要素。技术创新局限于企业家行动过程的狭隘视野被大大扩展了,它不仅凸现了使用者(消费者、用户、具体使用者)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突破了“结束机制”这一观念的限制而展现出技术的意义不断得到解构与重构的永恒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视角下,以前被排斥在历史意识之外的普罗大众和他们推动技术变迁与发展及历史进程的具体过程就浮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正因此,笔者极力强调,必须深入到大众复杂的历史意识中去探寻技术的历史过程。
但是,对行动者的具体文化实践能动性的强调并不否定超越行动者能动性的宏观力量与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前社会史家乐于把这种宏观力量实体化为“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经济基础”、“阶级与集团”和“社会体制”,但如今这种静态的社会结构与稳定一致的功能系统概念逐渐为一种建构论视角所取代----概而言之,文化组织着实践活动。技术文化实践对应的正是这一新视角。从文化实践视角看,技术创新是一种组织机制。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指出的,科学知识的创新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内外组织认知秩序的过程。技术建构论者也已详细阐述了技术创新作为各异质要素的组织机制的性质。拉都尔、卡龙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描述的就是这样的过程。休斯对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技术系统(比如电力系统、化工系统、信息系统等)的深入研究更是系统展示了技术的组织机制。这些理论和经验研究揭示,技术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着,同时展现它的器物、内在功能与符号意义,也展现它在个体身体、自然、文化、社会组织方面的意义。换言之,技术既以作为组织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互动的媒介的方式发挥作用,也通过人们组织其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运作着,也通过建立技术系统的方式以及通过组织各种产业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方式执行功能,还以建构符合文化意义的方式起作用[17]。正是这种组织机制使得技术具有超越于个体能动性之上的宏观结构力量和不确定性。
三、技术创新作为当代人的历史意识
技术创新作为历史意识,表明的是人们并非为了技术创新而进行创新。就历史意识而言,人类行动的目的在于生存(此在—在世界中—生存)。在此生存过程中,历史意识的功效就在于组织要素的时间性即各要素在时间中展开的秩序,以此来显示时间与生存的意义。技术进入历史意识,即技术作为人类过去的生存经验,对当下—未来具有历史意义,它实现了一种文化功效,构建“技术文化”,其目标在于指导当下与未来的实践;技术作为生存手段和人类行动的要素,为的是人类协商未来,为自身及其后人的未来生存境遇进行谋划。因此,技术创新作为当代人的历史意识,表明的是人们运用技术过程论、生存论和文化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历史过程中的技术,并由此规划未来。上文对技术的历史意识所作的历史考察已指明,技术创新历史意识只是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但我们却力图用它来反观所有历史阶段的技术。
尽管技术现象学家伊德、博格曼等已指出,人—技术—世界是人的本体论生存状态,技术终究不是生存目的;但也正是技术作为居间调节的这种与人—世界的关系,使得人的生存实践时刻与技术相关联,从而这又使得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意地(更多是无意地)参与了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就以技术创新过程的方式,成为我们协商未来的根本途径。历史学家已就此开展了丰富的经验考察。人们借助技术来组织身份与地域边界[18],组织集体(社会)记忆*自2002年开始,Technology and Culture每期都设有“Exhibition Review”的专题,专门讨论博物馆的设计、展览对技术意象和社会记忆的制造。西方史学界对集体记忆的深入探讨主要是由纳粹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研究激发的。,组织生活空间[19],组织自然观念[20],……而到了今天,技术创新已成为我们生活、社会交往与组织社会系统的核心要素。无论从技术作为对人类生活的助益来看,还是从技术给社会系统与人的生存内置的一种风险与脆弱性来看,技术创新都成为我们协商未来的根本途径。比如说,美国9·11事件后,人们对“风险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技术—社会系统的脆弱性[21]。它突出表明了人们参与技术—社会系统的建构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这一路径,即现代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都处于由技术构成的“风险系统”(技术—社会系统)中,要想设计更加安全的未来,就必须参与技术创新与技术文化实践。
以上论述表明,从生存论和历史意识视角看,技术创新从各个层面组织人类实践,因而是一种文化实践。这种技术创新的文化视角对理解技术史更有助益。技术创新作为文化实践,是此在参与世界的基本途径;技术创新作为历史意识,是组织实践的机制。因此,探究技术创新就是探究人们参与世界的组织机制,其方法论是文化叙事学。这种叙事学是本体论性的。即叙事并非仅指以语言文本为基础,而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内在时间意识(空间意识)为基础,组织各种异质要素以建立生存秩序的过程。这些要素并非仅限于技术要素,还包括自然物、社会行动者(个体、群体或组织)以及特定的社会规则与文化传统。所建构的生存秩序就是日常生活,它既是认知秩序,也是审美和政治秩序,也是给世界创造一种秩序。换言之,叙事包括认知、审美和政治三个维度。技术创新研究就是要对技术创新的内容、形式与功能展开这三个维度的综合研究或在综合视角下分析某个维度。认知维度的分析就是分析技术原理和认识真理的过程,分析我们如何如实地言说技术创新。但是对实在的反映并非镜像表征,除了如实地言说以外,还存在什么才是合适的或具有美感的、引人入胜的言说的问题,这取决于文化传统、个体偏好、言说的具体情境,以及谁有权力来作出判断,这些涉及的是技术叙事的美学与政治学问题,是对技术创新进行审美和政治维度的分析要涉及的方面。笔者把这种分析称之为“文化叙事学”方法论。基于这种方法论,笔者曾讨论过技术文化研究的分析工具,如“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技术表象”、“切身体验”、“技术—社会”(technosocial)“杂交体”等[22]。
这些范畴引导我们去考察的是身体、技术、自然、文化和权力如何汇集到一起而制造了“合作者”(co-agent)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是情境性的、开放性的。技术创新作为杂交体的建构过程,是“情境化的身体实践”,包括切身体验、符号阅读、意义建构以及历史意识的形成等。从而技术创新就可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技术的、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认知的、利益的、政治的、情感的,规范的、个人意向的等要素具体地有选择地“接合”起来,生产、表达、使用、体验和重构“技术物及相关活动的意义”的“文化实践”过程。通过以上概念,我们就可以丰富地展现,技术创新作为文化实践和历史意识,它与人、社会和历史进程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相互作用关系与过程。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可以回答开篇提出的几个问题。之所以技术史现在应聚焦于技术创新,是因为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代人历史意识的主流。之所以须要采用文化研究路径,是因为该路径在融通生活化过程的各个层面,突出能动性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在构建大众参与协商的对话平台,在实现跨学科的整合策略方面都表现出巨大潜力。至于古代有无技术创新这一问题,从历史意识的历史变迁视角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去思考过去的时间经验及其与当下和未来的关联。技术创新作为历史意识,最根本的含义也就在于,技术成为我们协商历史意义、规划未来的根本路途。
参考文献:
[1] 远德玉. 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108-110.
[2] 李兆友. 从发明与创新的区别看技术创新史的研究[M].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22(4):106-108.
[3] 葛勇义,陈凡. 现象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M].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22(6):52-55.
[4] 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M]. 叶桐,顾杭,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426-430.
[5] Hughes T P. Rescuing Prometheus[M]. New York: Pantheon,1998:36-58.
[6] 陈凡,陈玉林. 技术概念与技术文化的建构[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25(3):41-45.
[7] 陈绍宏,陈玉林,李勇. 万尼瓦尔·布什与美国科技文化的建构[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6):480-482.
[8] 郑美珍,李兆友. 论我国古代技术创新主体[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10-12.
[9] 远德玉,陈昌曙. 论技术[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5.
[10] 远德玉. 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11] 李兆友,高菲菲. 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思想评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3):98.
[12] 远德玉,丁云龙,马强. 产业技术论[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13] Michael D G,Sam S. Thinking Systematically: Thomas and Agatha Hughes,“Systems,Experts,and Computers”[J]. Technology and Culture,2002,43(2):390-397.
[14] 马克·史密斯. 文化----再造社会科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15] Michael M. Reconnecting Culture,Technology and Nature: From Society to Heterogeneity[M]. London: Routledge,2000.
[16] 罗克·华康德. 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M]∥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 文化研究:第4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5-24.
[17] Nowotny H. Cultur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Quest for Innovation[M]. New York: Berghahnbooks,2006:18.
[18] 阿兰·科尔班. 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9.
[19] Wilson M A. Technically Together: Re-thinking Community Within Techno-society[M]. London: Routledge,2006.
[20] Nye D E. Narratives and Spaces: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Devon: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7.
[21] Bijker W E.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Technological Culture[M]∥Nowotny H. Cultur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Quest for Innovation. New York: Berghahnbooks,2006:52-72.
[22] 陈玉林. 论技术叙事的文化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4(6):3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