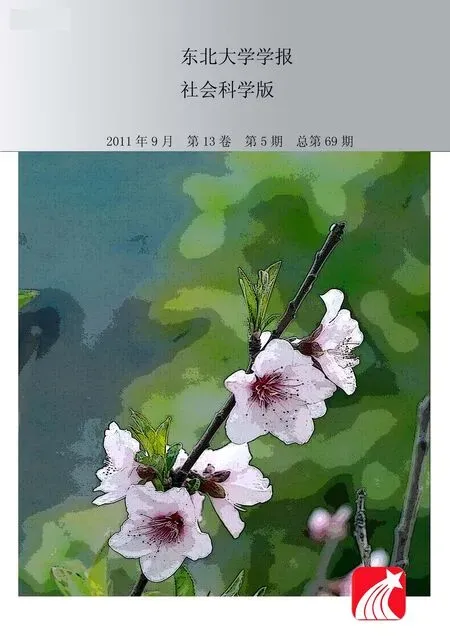一部认真的社会喜剧
----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中对传统的颠覆与重建
曲 彬,尹 丹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末期的王尔德在他的批评文章和作品中不断阐述和诠释着他的艺术主张,并用自己的一生将其充分演绎,成为19世纪末那场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将。从他1900年去世到本世纪初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的学者对王尔德的研究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得以发展,研究方法不断丰富。这使得对于王尔德及其推崇的唯美主义的研究更趋于客观和辩证,减少了对唯美主义的认识偏见,使人们能够将王尔德和他的唯美主义思想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研究,体会出王尔德思想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所在。
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艺术高于现实与自然,艺术与道德无关的美学观点以及他推崇的新享乐主义生活哲学究其本质都是对于现实中虚伪庸俗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一种颠覆,是对立于社会主流文化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话语体系。王尔德在他的《来自深渊》中说过:“我曾经是我这个时代艺术文化的象征”[1]118,“我生来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个标新立异、而非循规蹈矩的人”[1]122。作为唯美主义艺术化的个人,浪荡子的形象总是以他们的奇装异服、不凡的谈吐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出场,尤其是在他的最后一部社会喜剧《认真的重要》里,王尔德更是打造了一个纯粹浪荡子的世界。本文将深入探讨这部喜剧中王尔德如何在这个浪荡子的世界里从多方面实现他对虚伪荒谬的传统道德观念的颠覆,以及透过剧中浪荡子角色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情实意来感受作者构建理想道德秩序的渴望,体会这位世纪末的浪荡子身上可贵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维多利亚王朝晚期的英国社会和王尔德的浪荡子世界
《认真的重要》是王尔德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社会喜剧。表面上看,这部喜剧沿袭了传统文学中的婚姻家庭的主题,演出了一场上流社会绅士淑女的爱情闹剧以达到娱乐观众的效果,但这部喜剧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借助一群浪荡子形象对上流社会假模假样的认真和严苛不合实际的道德观、婚姻观、宗教观等诸多社会方面的嘲笑和批判。想要深刻地理解漫画般滑稽表演背后的批判价值和一个纯粹浪荡子世界的颠覆意义,我们须要对维多利亚王朝晚期的英国社会和王尔德倾力构筑的浪荡子世界首先作以分析。
王尔德进行创作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维多利亚统治的末期,随着科学技术领域不断有突破性的进步,英国不仅完成了工业革命,使机器生产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整个社会形态也迅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商业精神随之确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西方文化传统出现了断层。随着尼采发出“上帝已死”的呐喊,基督教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动摇,人的独立自主的自我观念不复存在,人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所异化了。而作为对资产阶级经济迅猛发展的应激反应,上流社会的贵族和精英阶层变得更加保守。这时,“资产阶级所占据的社会生活实际中的强势与贵族和精英阶层所占据的舆论上的强势产生了分离,于是就出现了行为上对原有道德体系普遍背离,而舆论中却对原有道德体系高调坚持的奇怪局面”[2]。显然,这种高调的坚持既不符合现实,也无法让人信服,人们的精神世界孤寂空虚,有如一片荒原。
面对着这样一个严苛的社会现实,面对着人类即将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作为社会精英艺术家的王尔德更是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感到了这“世纪末的悲哀”。王尔德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和经历,比一般人遭受着更严重的身份危机。相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来说,王尔德一直处在一种边缘的社会地位,对于“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有着更多的困惑。“他一方面扮演着英国上层社会的文化精英,宣扬风靡一时的美学思想,写出令伦敦上流社会大为赞赏的喜剧,成为当时的权贵们纷纷巴结的明星;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儿子,他身负母亲无形中给予他的民族情绪,对爱尔兰被邻国统治的屈辱历史耿耿于怀。加之他在壮年时又陷身于同性恋的地下世界”[3]16-17,所以对于王尔德来说,他一直体会着一个社会边缘文化体中的个体对自我身份确认的强烈渴望。
在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过程中,王尔德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的唯美主义运动中找到了与自己的契合点,将艺术作为重塑自我的载体。“……在王尔德心目中,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还意味着更多的涵义,即对‘自我’的重建,用他的术语说就是人们通过艺术实现自我,强化自己的个性。艺术因而成为诞生主体性的新的现实。”[4]王尔德不仅倡导唯美主义的艺术自律,形式高于一切,艺术超越生活,游离于自然之外,与道德无关,以及推崇抓住每一个瞬间来获取感官的享受,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生活模仿艺术”,以自身的实践将生活艺术化,把唯美主义奉为宗教信仰顶礼膜拜,将唯美主义运动推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做是因为“在我们变得高尚起来之前,它必须融合到人的本能之中,克己只不过是人们阻碍自身进步的一种方法。自我牺牲是野蛮民族自残行为的剩余部分,是对痛苦古老的顶礼膜拜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可怕事件”[5]。在王尔德唯美主义的主体建构中有一个代表了唯美主义特征的可以称为唯美主义艺术化了的人物形象,这就是一个浪荡子的形象。浪荡子实践着唯美主义的各种理想。王尔德本人就是19世纪末最著名的浪荡子。王尔德总是穿着设计独特的天鹅绒礼服,手里拿着一朵象征美的向日葵或者百合花,穿梭于伦敦的街头;同时这位牛津才子的妙语连珠、机智诙谐的悖论更是他用以彰显个性、炫耀自我的特长。他的新享乐主义生活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浪荡子诉诸感性,以及对瞬间感受强烈体验的追求。这种对形式、对感官、对变化的体验的推崇正是唯美主义浪荡子重塑自我、反抗社会习见的方式。“要有一种新享乐主义来再造生活,使它挣脱不知怎地如今又出现的那种苛刻的、不合时宜的清教主义。”[6]于是我们在王尔德的作品中看到了浪荡子以玩世不恭对抗盛行于维多利亚社会的假正经,以无所事事嘲笑上中层社会中的唯利是图,以感官的享乐来讽刺不合时宜的清规戒律。“他们这种反叛的力量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他们自身也处在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之中。这其实也就是王尔德自身生活一个写照。”[7]《认真的重要》这部喜剧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由浪荡子构成的世界。
二、对婚姻家庭、宗教和教育传统的颠覆
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达林顿勋爵、《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伊灵沃斯勋爵,再到《一个理想的丈夫》中的戈林子爵,王尔德越来越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个浪荡子的形象,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机智妙语给予中产阶级的庸俗虚伪痛快淋漓的讽刺,与剧中唯利是图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物质主义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浪荡子就是王尔德用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有力武器。这里的浪荡子(Dandy)并不是指花花公子、纨绔子弟,而是指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先锋。他们拒斥资产阶级的主流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反抗资产阶级工具理性和现代性,具有相当的思想修养和艺术追求[3]37。到了第四部喜剧《认真的重要》,王尔德创造了一个纯粹浪荡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物,不分主次,无论男女都过着浪荡子的生活。剧情围绕两对贵族男女的恋爱过程展开,这是一个很老套的主题,有趣的是,两位贵族小姐格温多琳和赛茜丽追求的都是一个名叫“哦拿实的”(Ernest)的爱人。“哦拿实的”具有“认真”的意思,对于她们来讲,名字比什么都重要,她们追求的就是嫁给一个有这样动听名字的人,这就是她们的伦理标准。杰克与爱尔杰龙是剧中的两位男主人公,杰克是受人尊敬的乡绅,他杜撰了一个城里的叫“哦拿实的”的弟弟,为的是可以随时到城里去玩乐,而在城里,他化名“哦拿实的”,常到朋友爱尔杰龙的寓所消磨时光。而这个爱尔杰龙谎称在乡下有一个叫“病不理”(Bunbury)的病人,目的是能时常去乡间游玩,与杰克的谎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格温多琳在爱尔杰龙的府上与杰克相遇,事先并不认识杰克的格温多琳听表兄爱尔杰龙说他就是那个叫“哦拿实的”的朋友时,便爱上了他。“我的理想一直就是爱上一个名叫哦拿实的的人。这个名字有某种激励人充满信心的东西。一听爱尔杰龙说他有个名字叫哦拿实的的朋友,我就知道我注定会爱上你的。”[8]366一直暗恋着格温多琳的杰克担心她如果知道自己并不叫哦拿实的,会结束和自己的感情,便隐晦地询问假如自己不叫这个名字,她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他。格温多琳坚持表达了自己不可能喜欢是别的名字的人,并说为那些没有嫁给“哦拿实的”的女人感到遗憾。爱尔杰龙趁杰克不在假扮他虚拟的弟弟哦拿实的来到乡下结识被杰克监护的女孩赛茜丽时,也发生了和杰克同样的遭遇。王尔德更是有意地将两位女主人公对名字的看重用一模一样的句子表达出来,进一步加强了其中的讽刺效果,暴露出维多利亚人注重外表和形式的虚伪面目。
除了这两对男女主人公外,剧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格温多琳的母亲布雷克耐尔太太。她在两对恋人的婚姻问题上均设置了障碍。首先,她对杰克的方方面面进行细致的盘问,其取向的庸俗虚荣本质显而易见。最终她发现杰克没有一个体面的家庭出身而拒绝同意他们的婚事。她不能让自己唯一的女儿下嫁到“一个行李寄存处,和一个手提包缔结一门婚姻”[8]370。原来杰克从小就被人遗弃在火车站的手提箱里。布雷克耐尔太太告诉杰克除非他能尽快地为自己找个父母,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那根本不重要。对于布雷克耐尔太太来说,体面的形式是最关键的。在她的侄子爱尔杰龙和赛茜丽的婚姻上,当她得知赛茜丽是拥有13万英镑公债的债权人时,立刻改变了立场,同意了她们的婚事。更可笑的是,她还为自己对金钱的追求一本正经地予以辩解。她告诉赛茜丽,“……爱尔杰龙一文不名,只会欠债。但是我不赞成唯利是图的婚姻。我和布雷克耐尔结婚时,也没有任何钱财。但是我从来没有让这个挡住我的路”[8]409。
通过布雷克耐尔太太的夸张形象,王尔德无情地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以金钱和出身为标准的婚姻概念;同时,当时的教育和宗教状况也被王尔德拿到剧中用讽刺的否定性目光加以审视。赛茜丽在她的家庭教师普利茨莫小姐的监护下,只能阅读那些枯燥的、保守的、缺乏想象力的书籍,这些书籍被认为是最适宜用来教育年轻人的。而如果任由赛茜丽的想象力不加限制地发挥,将是这个社会不可接受的。在维多利亚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中,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年轻人不要发问,不要对现存的社会体系提出异议。这一点同样也借助布雷克耐尔太太表达出来。她在盘问杰克的过程中说道:“现代教育的整个理论是极端地不正确的。幸运的是在英国,不管怎么说,教育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它真的有了效果,将对上层阶级造成严重的威胁,而且很可能会导致格罗夫纳广场上的暴力事件。”[8]368看来,英国的教育就是要稳固社会上层的统治,扼杀人们变革的思想和念头。对社会未来至关重要的教育,正是由于其腐败的性质令布雷克耐尔太太口中的话既显得可笑,又是那样的真实,其讽刺意义不言而喻。
前文提到,在维多利亚王朝晚期的英国,宗教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基督教的没落和腐败加之维多利亚上流社会对宗教信念的严苛要求必然导致人们对它的亵渎。这一点在《认真的重要》里面也明显地体现出来,成为王尔德嘲弄的主要对象之一。两位男主人公杰克和爱尔杰龙由于都不叫“哦拿实的”而在他们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因为谎言终将败露,格温多琳与赛茜丽在杰克乡下的宅邸相遇,以为爱上了同一个叫“哦拿实的”的人,而杰克与爱尔杰龙此时的不期而遇令他们杜撰假名字的一幕无奈收场。两个人都想出了同一个荒谬的办法,就是找牧师为他们重新洗礼而获得“哦拿实的”这个名字。基督教洗礼本是在孩子身上进行的严肃的宗教仪式,却被两个浪荡子变成了随随便便的事情。更令人吃惊的是,作为神职人员的牧师对此也乐此不疲。他不仅对教民的布道稀松平常,而且洗礼仪式也可以随时进行,一切皆可依据上层阶级的要求随心而为。就连这位牧师自己的生活也充满了对宗教的不敬,他虽然表面上遵循着一个牧师的清规戒律,却难掩对普利茨莫小姐的爱欲。剧中人物对待宗教极不严肃甚至令观众耻笑的态度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宗教观念的虚伪和作态。剧中的浪荡子们用反讽和夸张的方式把维多利亚人假模假样的“认真”态度和实质上对宗教的不敬表现得淋漓尽致。
剧中的浪荡子用随心所欲的行为和言语无情地撕开了上流社会的虚伪面纱,暴露出诸如布雷克耐尔太太的这些上流人物庸俗和唯利是图的本质。剧中的几乎每一处情节、每一段对话都无不渗透着王尔德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以及阶级矛盾等诸多方面的批判,构成了对维多利亚传统有力的颠覆。
三、 对建立理想道德秩序的渴望
王尔德称以艺术来构建生活,希望用艺术的世界构筑起一个新的自我,以反抗工业现代化和商业文明对自我身份的剥夺。他在剧中建立起来的浪荡子的世界就是这种自我构建的一种实践。就像王尔德在他的新享乐主义理论中所倡导的那样,这些浪荡子不仅用精致的外表找到对自我的感觉,而且用无所事事的生活和对不断的感官享受的强调确认自己的存在感,来达到颠覆社会习俗和重建自我的目的。这部喜剧看上去确实是摒弃道德判断而只为享受生活的一群浪荡子上演的一场闹剧,爱尔杰龙总是在大嚼黄瓜三明治的场景令每个观众和读者印象深刻,这种强调感官体验的唯美主义观点在王尔德的艺术理论中也是被清晰阐明的。可是王尔德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部喜剧里,在他构建一个浪荡子的世界以颠覆社会传统的同时,也寄予了对建立理想伦理道德秩序的渴望[9]。
当两位女主人公在杰克的乡间宅邸得知她们双双受到了欺骗,她们所爱的人并非真的叫“哦拿实的”的时候,她们没有让这段感情结束,而都将其理解为出于对方追求自己的真情实意。对于被欺骗的事实,赛茜丽和格温多琳本想装出高傲冷漠的态度,却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感情对她们的爱人诉说埋怨,言语中透出更多的宽容与爱意。
赛茜丽:…… 蒙克里夫先生,请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假扮成我监护人的弟弟?
爱尔杰龙:为了我能有机会见到你。
赛茜丽:那看起来确实是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不是吗?
……
格温多琳:…… 沃辛先生,你怎么向我解释你假装有个弟弟的事?是为了你能尽可能多地到城里来看我吗?
杰克:你能怀疑这一点吗,费尔法克斯小姐?
格温多琳:…… 他们的解释看起来很令人满意,尤其是沃辛先生的。在我看来他说的是真的[8]406。
的确,两位女主人公在她们的爱情发展遭遇困境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为对方的谎言找到善意的理由。而两位男主角也最终是为了赢得心中的爱情用“哦拿实的”这个名字来迎合两位女主人公,甚至在后来想要通过重新受洗的方式来达成拥有一个“哦拿实的”的名字的目的。剧中的诸多细节都让我们体会到两对恋人对感情的执著和认真。这不能不说是王尔德在刻意刻画两对男女主人公儿戏生活和爱慕虚荣的态度时对他们内心的认真态度的肯定和对爱情伦理理想的渴望。
情节在最后一幕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杰克的乡间宅邸,布雷克耐尔太太认出了失踪多年的仆人普利茨莫,原来她当年将布雷克耐尔妹妹的儿子放在手提包里遗落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之后便因为恐惧自己的罪过再也没有回来。杰克拿出了那个手提包,结果证实他就是布雷克耐尔妹妹的儿子、爱尔杰龙的哥哥,而他们曾是将军的父亲的名字就叫“哦拿实的”,本来彻头彻尾的谎言现在却变成了确确实实的现实!王尔德以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给予这个喜剧一个圆满的收场。这里不能不说寄予了王尔德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杰克的最后一句“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哦拿实的的重要”[8]419在王尔德的笔下完全可以理解为又一个双关语:拥有“哦拿实的”的名字重要,真正的认真态度更为重要;没有追求爱情的认真和诚意,恐怕剧中的主人公们也不会有最后的完美结局。
王尔德毕其一生的精力来构筑唯美主义的艺术理想,在他的最后这部喜剧《认真的重要》里成功地塑造了充分体现他的美学思想的浪荡子世界。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有对感官享乐的过分追求。但毕竟,王尔德根本上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是以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开始他的知识分子生涯的”[10]。他作为艺术家最本质的诉求是尊重人的尊严,给予人应有的意志自由,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以谋求人类更大的幸福。今天,我们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对于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体系的建设还尚处探索阶段。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王尔德对物质财富充斥下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因为这关系着人类是否能找到心灵的归宿而远离荒原。
参考文献:
[1] 奥斯卡·王尔德. 来自深渊[M]∥赵武平. 王尔德全集:第6卷. 常绍民,沈弘,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2] 吴刚. 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80.
[3] 李元. 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4] 周小仪. 奥斯卡·王尔德:十九世纪末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理论[J]. 国外文学, 1994(2):24.
[5] 奥斯卡·王尔德. 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M]∥赵武平. 王尔德全集:第4卷. 杨东霞,杨烈,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405-406.
[6] 奥斯卡·王尔德. 道连·葛雷的画像[M]∥赵武平. 王尔德全集:第1卷. 荣如德,巴金,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84.
[7] 陈莉莎,姚佩芝. 王尔德人文主义思想的颠覆性[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1):108.
[8] Wilde O.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M]∥Holland M.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5th ed.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3.
[9] 刘茂生. 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42.
[10] Bashford B. Oscar Wilde: The Critic as Humanist[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