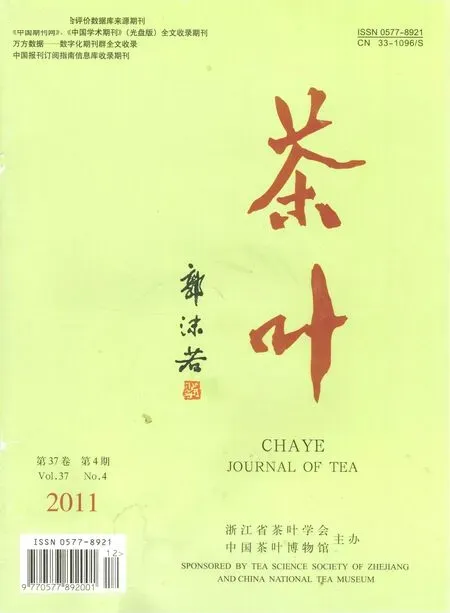“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回忆爷爷吴觉农的老朋友蒋芸生先生
吴 宁
蒋芸生先生是爷爷的好友,1971年他去世之后,蒋先生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儿子蒋同远把他的母亲接到北京住。每年春节过后,爷爷和奶奶都会请蒋师母到我家来住几天,散散心。老人们在一起多是忆旧,三位白发老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爷爷爱讲,奶奶和蒋师母爱听,而话题总是离不开蒋先生。
爷爷说芸生是一位“做办成很多事的好好先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解释道,“好好先生是不得罪人的,人云亦云,而且少做事,做事情就会得罪人嘛。而芸生却是不声不响、和和气气地办成很多的事。孔夫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用在他身上这儿是最合适不过。”
(一)
1930年秋,爷爷和蒋芸生先生是在从浙西回杭州的帆船上认识的。爷爷受浙江建设厅的委派在浙江各县考察茶叶生产,而蒋先生和几个浙大农学院的学生去调查衢州蜜桔,回杭州时同乘了一条船。爷爷说,芸生那时候还不到30岁,和他的几个学生年龄相近,加上他寡言,所以直到分手,他才知道他是带队的老师。在浙江建设厅,爷爷负责浙中农民银行下属的“合作事业室”的筹备工作,真碰巧,他的顶头上司许叔玑先生既是农民银行的主办人也是浙大农学院的教务长。当爷爷向他提起在浙西遇到了蒋芸生时,叔玑先生很是赞许:蒋芸生的园艺通论和柑桔栽培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他对学生又好,懂得因材施教,大家都欢喜他!刚来浙大农学院一年,就已被提升为副教授。
当时的浙大农学院,群英聚集,早年与爷爷一起在上海参加中华农学会工作的几位朋友,汤惠荪、蔡邦华、朱凤美先生都在那儿。爷爷知道,那里的教授多是留学各国的博士,相比之下,蒋先生却只有日本专科大学的学历,又是第一次在大学讲课。爷爷说,叔玑先生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农学家,中国农学会的理事长,农学界的能人他都熟,他眼力高得很,他能对蒋芸生这样称赞和提拔,这个人一定不凡!
以后,因为农学会、农村合作事业的各种活动,爷爷与蒋先生熟悉起来了。那几年,政治风云变换,爷爷说,他周围的这一帮年青人大都思想激进,各持己见,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在一起聊天,常会争论不休。而蒋先生从不参加争论,总是笑眯眯地听别人的。“可也真怪了,”爷爷说,“也许正是因为芸生话少,所以他每次说话,大家都会注意听,时间长了,发现他的几句话,挺透澈,所以就养成了要听听他讲的习惯。”
那一年,爷爷和蒋先生都在上海劳动大学兼课,两人常常同乘杭州到上海,上海回杭州的火车。爷爷这才发现,蒋先生也有健谈的时候,有一次讲起他在日本认识的柑桔专家田中长三郎,居然讲了一路。蒋先生是因为受了田中先生的影响才专攻柑桔的。田中先生研究柑桔的全部:从柑桔的历史、传播分布、原产地、种植、分类,他还自费到世界上的柑桔产地去做田间调查,也来过浙江,非常了不起。
还有一次是讲园艺。爷爷在去浙江合作事业室前,曾在上海的园林试验场任场长。他在那里读过不少园艺的书,能够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用上,他很开心,也引起了他对园艺的兴趣。一路乘车,正好听蒋先生讲的园林设计,爷爷说,他一边讲,一边画,因为我也在日本上过学,他还把中国和日本的园林设计做个比较,我听得真是有味道。
爷爷有拿不定主意的事,也喜欢和蒋先生聊聊。蒋先生是个好听者,嘴严,又守着中庸之德。两人在一起聊,蒋先生有不同看法,也会提出来,只是不爱辩论,每次当他意识到“辩论”要开始了,就会笑笑说,“我还要再想想。”就不讲了。所以,爷爷也只好闭嘴。
(二)
爷爷说,他与芸生性格不同而想法相近,所以是好搭挡。1942年,爷爷在福建的崇安办茶叶研究所,正巧蒋先生在福建永安的园艺试验场做场长,两人合作的机会终于来了。爷爷比当年刘备请诸葛亮还诚心,“五顾茅庐”把蒋先生从永安请到了武夷山。
福建永安是当时省政府的所在地,1942年秋,爷爷因茶树更新的工作,曾去那里四次,每次去他总是去看蒋先生,邀他去武夷山。开始,蒋先生对去茶研所当头儿有顾虑,他对爷爷说“我不懂茶,怎么好去“领导”专家们呢?”爷爷告诉他,所里已经有研究棉花的叶元鼎,有研究世界经济学的叶作舟,有研究基础化学的王泽农和徐大衡。他又讲起了研究所的长远规划说,茶叶研究所要发展,需要懂农业经济、农学基础理论、园艺学的专家们。
崇安到永安交通不是很方便:建阳乘船,然后改乘长途车,要走一天。1942年冬,爷爷又与栽培组的吕增耕一起去蒋先生处,还带着栽培组正在做的试验方案和计划。1943年初,当爷爷得到蒋芸生决定来武夷山的消息时,真是兴高采烈。不久,蒋先生全家从永安到武夷山,在赤石镇的木楼里住了下来。
武夷山的茶研所,有位很有才气,但性格“怪”的叶鸣高先生。他脑筋快,聪明,讲话直冲冲的,常会得罪人。就是近年来,当我去访问还记得他在武夷山的几位老人时,善意的用“迂阔”、“清高”来形容他,不友善的则说他“神经兮兮”、“不通人情”。
蒋先生到武夷山的那天,爷爷正在外地开会,他请管总务的汤成先生向栽培组介绍蒋先生。初次相会,大家都是客客气气,谁知叶鸣高先生当头就是一句:“不懂茶,怎么来领导我们呢?”本来同事们对叶先生是司空见惯的,可蒋先生却是第一次,大家都感到有些尴尬,蒋先生却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所以要向你学嘛,明天起,请你教罗。”
爷爷回到武夷山后,听到这一幕,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爷爷与叶先生熟,那时,他为我父亲吴甲选补代数,住处离我家不远,爷爷就去找他。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他看到了蒋先生和叶先生正说说笑笑地走来。原来,他们一清早就进山到水廉洞去看茶树了。叶先生对爷爷说,原来他们两人还是苏北的小同乡呢。以后的一段,蒋先生就一边了解岩茶树种,一边帮助叶先生做标本。他们在一起,选定了“名枞”,准备用杂交的方法培育新的品种。
1945年,茶研所结束后,蒋先生把叶先生请到他所在的福建省立农学院附属的农场,继续他的茶叶研究和茶树管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在浙农大,他又让叶先生去武夷山,把名枞的枝条带回杭州试种成功。
爷爷说,栽培组的人有好几个有本事、个性很强的研究员。在蒋先生来之前,他们在研究上不大交流,却常常为些小事情争吵,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爷爷还为他们调解过。而蒋先生一来,组里的空气大变,再没有争吵了,互相交流和通气也多了。爷爷与蒋先生开玩笑道,是因为他身材高大魁悟,把组里的人给“镇”住了。实际上,蒋先生话少,就是讲起来也和言悦色,组里的人,不管年龄大小,他都称先生。以后对组里的人和工作熟了,他又按计划和每人的兴趣,调整了研究题目,使得大家工作愉快。蒋先生不讲话,可他的性情和风格影响了组里的每个人。
记得爷爷曾对蒋师母说,芸生特别宽容,在武夷山共事,从来没听他讲哪个不好,也从来没见他生过谁的气,他问蒋师母在家里芸生发不发脾气,是不是会讲别人。蒋师母笑笑说,
“他在家里也不多话。晚饭后,管管儿女的功课,和他们玩,等我们都睡了,他总要看书到深夜。”
(三)
爷爷说,蒋先生在武夷山的时间不长,前前后后还不到两年,但所里的人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特别是和他一起做过事情的。爷爷的侄女婿吕增耕研究茶树栽培多年,喜欢钻研,动手能力强。但他没上过多少学,他所写的研究报告停留在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到了武夷山,他就打算自学植物学知识,找到了本日文的植物生理学边学日文,边读书。谁知那本书理论性强,又是外文,加上夜晚油灯暗,翻两页就直打磕睡。蒋先生到了栽培组后,曾与增耕做过一段茶树的光照实验。他们一起每天早出晚归地茶园中忙,当他了解增耕在学植物生理,有空闲,蒋先生就会给他讲植物学,从光的同化作用谈起,讲植物生理联系茶树的生长和栽培技术。受蒋先生的启发,那本书就不那么难读了。
当时茶叶研究所的工作分成制造、栽培、推广和化学实验四个组,虽然蒋先生担任副所长又具体负责栽培,但他对制造、生化也有着浓厚兴趣。爷爷常提起,希望年青人的学习路子要宽点,不要因为分组把自己圈在组里。蒋先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次,他请制造组的庄任和刘河洲先生去谈谈。蒋先生才来所不久,又是栽培组的,去时,他们以为不过是向他汇报一下工作进展,谁知蒋先生的桌子上摊满了红茶制造的书,有中文的,也有英文和日文的。在这之前,他不仅细读了庄任从万川寄来的几份报告,而且还做了不少笔记。那天,蒋先生问了他们不少问题,庄任和刘河洲有的能答,有的不能答。从蒋先生那里回来,两人都特别受启发,感觉要深入研究制造,也要像蒋先生那样,学习茶树育种、栽培和生化。
爷爷很感慨地说,芸生懂人,懂得管理的艺术,用提问题的方法,因势利导、启发人。和他比,我就不行。我话多,事倍功半,而他话少,讲求效果,事半功倍。
我奶奶记得,我家企山场的房前,有块地,种了各种蔬菜。蒋先生每次来,都给奶奶当参谋:茄子、西红柿种在哪儿,菠菜、刀豆种在哪儿,房边的果树上有了病虫害,他也知道怎么对付。
奶奶还说,她常做的几只苏北菜,还是在武夷山从蒋家学的。栗子鸡、菜根狮子头是跟蒋师母学的,最精采的涟水红烧猪蹄膀是蒋先生的拿手菜,用苏北来的佐料腌拌,烧出来酱色红亮,味道鲜美。
蒋师母说,在企山的那一段,他们一家也是蛮愉快的,和大家相处得好,他们的孩子与我的姑姑们一起去上学,成为好友。蒋先生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工资比较高,那是她们生活最宽裕的一段。家里人多,在大学教书时,省吃减用,可连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有困难。可是,协和大学和省农学院两次加工资,芸生却说,他在系里薪水是最高的,系里的其他老师工资低,比他更困难,所以他主动要求少加工资。那两年,家里经济紧张,大女儿同涟因为交不起学费,只好缀学,让弟弟们先去读。奶奶说,原来如此,在武夷山时,她一直纳闷,蒋先生的女儿同涟比我姑姑谷茗大两岁,怎么和我姑姑同班呢?
蒋师母还说,抗战胜利之后,蒋先生回到浙大教书,那几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大学教书无法维持生活,蒋先生就在南通农学院兼课。从杭州到南通不好走,坐火车到苏州,然后乘长途车到江边,乘船过江,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常常乘夜车,在路上打个盹,第二天一早就教课,辛苦。但他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起过。直到1949年解放,他们的经济状况才改变了。
(四)
提起五十年代初的事,爷爷总爱讲到蒋先生办浙江农学院茶叶专修科的经过。
1950年到1951年间,爷爷多次来杭州,每次来都会去看浙江农学院的老朋友蔡邦华和蒋芸生先生。蔡先生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院长,爷爷在1921年在日本就认识的。三人聚在一起喝茶,也就讲起了在农学院办茶学专业的事。爷爷主张从专修科办起,重庆复旦培养出很多茶叶骨干都是从两年制的专修科出来的。他说,茶学是动手实践的专业,一个学生只要有了基本的训练,对茶业有感情,主要是在实践中学。蔡邦华先生也很赞成,于是就由农业部出函,浙大农学院委托蒋先生去筹办。
1952年初,爷爷在北京听到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搬到沈阳、而复旦的茶叶专修科会留在南方时,他曾在北京呼吁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去杭州:浙江是产茶大省,浙大农学院又在蕴酿办茶叶专科,把复旦的茶叶系搬到浙大来是最自然不过的。这样一来,浙农茶学专科的老师问题也解决了。可当时安徽省省长曾希圣也看中了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到北京来极力游说,结果复旦的茶叶系并入芜湖的安徽大学。
同年春,当爷爷在北京得到茶叶专修科迁去安徽和浙农大的校长蔡邦华先生也要调北京中科院的昆虫所的消息时,他估计浙农大的茶叶专修科的计划一定会推迟了。谁想到,下一次他见到蒋先生的时候,蒋先生笑眯眯地对他说:“设专修科的计划不变,学生已经招了,我们九月开学。”“老师从哪里来呢?”爷爷问。蒋先生说,他已同农校的刘河洲先生联系,有些课请农校的教师来讲。杭州有那么多茶叶专家,不愁请不到老师。第一学期,他教茶叶概论一课没问题。
浙大的茶叶专修科1952年九月开学,浙大的胡月龄老师是那一届的学生。她记得,刚进校时,整个学科只有蒋先生一位老师,他给学生讲茶叶概论,没有课本,所有的讲义都是蒋先生一手编写的。所有的专修科的事情都是蒋先生一人负责,只请了农学系一位四年级的学生来专修科当生活辅导员。以后才有复旦茶业系的胡建程先生来做助教兼秘书,专修科才有了两位老师。
以后,爷爷每次去华家池,茶叶专修科都有新发展,先是建立制茶试验室,然后是开辟实验茶园。1952年春,在筹建茶叶专修科时,爷爷请陈观沧先生把他在杭州之江茶厂存下来的制茶机和茶叶书籍送到了浙农大,那年的秋天,蒋先生就用这套机械做底,开办了制茶试验室。下一次,蒋先生带他去看了刚在华家池建的茶园。爷爷说,怎么象变魔术一样,新开的茶园里已有成年的茶树了,还有从武夷山来的水仙、佛手和梅占。蒋先生笑吟吟地说,杭州在西湖边筹建西山公园(花港观鱼公园),要被开发的那一片土地上到处都是茶园,有很多茶树。当他发现华家池的土不适合种茶,他就请人把西湖边的一块茶园,连树带土都搬来了。
蒋先生说,自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爷爷却说,在中国办事哪有这样容易,把茶叶专科办起来,芸生花了多少心血。每件事,都要去很多个部门协商,敲上很多个公章才行得通。那两年,芸生一心只是要把工作做好,从不讲究排场,他每次去华家池看蒋先生,两人在食堂吃饭两菜一汤,出去看老朋友,还一起走路,乘公交车。
爷爷说,三十年代,我讲孔夫子有七十八个门徒,芸生是其中之一。现在看来,孔子还是提倡的是读书做官的,要被扫地出门了。而芸生只是利用他的“职位”,为茶业做事情,他是孔夫子加雷峰。
(五)
讲到蒋先生的最后几年,蒋师母说,芸生总是对工作太认真了,对自己的身体不注意。1964-65年间,医生已确诊他有严重的胃溃疡,建议手术治疗,但他考虑手术后要休养一段,不能上班,而当时正赶上茶学系准备搬去潘扳桥,工作千头万绪,他实在脱不开,就等一等吧。他还开玩笑地说,胃病多年了,不要紧的。别耽心,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说我是福像,是长寿的。
谁知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蒋先生被红卫兵“揪出来”以后,就没有动手术的可能了。是怕爷爷奶奶听了伤心,同远和蒋师母也一直没有告诉爷爷奶奶蒋先生在文革中的经历。关于蒋先生最后的日子是怎样渡过的,现在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了。
1966年夏,浙江农业大学红卫兵以他的工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学生”的罪名不断地批斗他,把他关牛棚。蒋先生因高血压晕倒了,才被送进医院,住院时,红卫兵在病房外面监视,连蒋师母和家人都不能进病房。有一晚,当他多年的好友和建系时的助手胡建程先生在黑夜里偷偷地去看他时,这位从来不轻易流露自己感情的老人与胡先生抱头痛哭。
以后,蒋先生的血压刚刚稳定,就被押到茶场去劳动。虽然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革委会”领导却不允许他去医院检查就医,只能在茶场医务室领一点止痛药和普通的胃药。后来在劳动时,他实在站不住了,还让他跪在地上拔草。直到1971年4月,浙农大的军工宣队才把蒋先生从劳改队“解放”出来,他被允许请假到儿子所在的部队医院去就医,检查出来已是胃癌晚期。蒋先生第二次在杭州住院是在1971年的7月,同年9月11日去世。
过去的三年里,每次在华家池的水边走过,我常常会想到蒋先生。
很多年前,听爷爷、奶奶和蒋师母的回忆,我心里已有了一个鲜活的,“谦和温厚”的蒋先生形象。到了浙江大学茶学系,才在墙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照片,只是比我的想象要苍老。多么安泰、和善的面像呵,的确应是享年百岁,无疾而终的,可他走得早了。
——写给我们亲爱的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