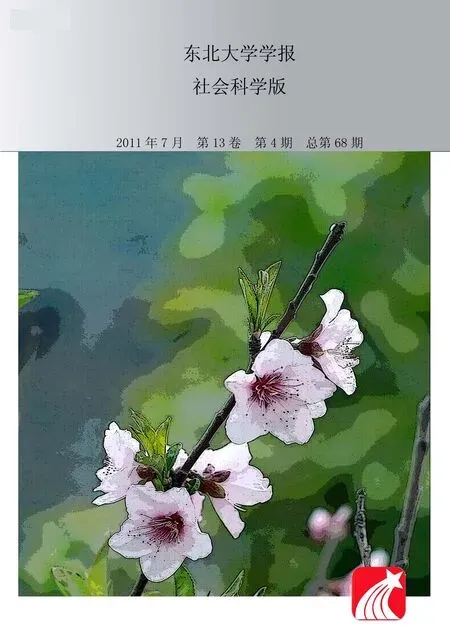沉默与逃避
——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风景
(1.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J.M.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正式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无疑是在他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库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焦点多集中于他的少数代表作,论文选题、观点也存在重复和扎堆现象,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布克奖得奖作品《耻》(Disgrace, 1999),《福》(Foe, 1986)和《等待野蛮人》(WaitingfortheBarbarians, 1980)。相比之下,库切的另一部布克奖获奖之作《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TimesofMichaelK, 1983)(以下简称《迈》)则受到了“冷遇”,仅有的论文多限于常规的主题分析,“拯救”也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①主要论文分别为:翟亚军、刘永昶的《无神时代的约伯——论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韩瑞辉的《种植与拯救——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K的园丁形象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S2期);高文惠的《规训、惩罚与迈克尔》(《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苗永敏的《自然之善:南非的拯救之路——解读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作家》2008年第11期);苗颖的《由〈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解读库切的自由观》(《电影文学》2010年第4期)。。那么,库切真是在他的小说中向读者传达南非的“拯救之道”吗?本文认为,“沉默”与“逃避”才是《迈》这部作品的核心议题。从表面上看,小说中的风景和主人公迈克尔一样沉默,但它在全书中是一种动态的建构,库切通过贯穿故事始末的风景,表达出他对于创伤、历史、权力、规训等诸多问题的反思,逃避最终成为了迈克尔唯一的选择。本文也试图从人文地理学对于风景的论述出发,解读小说中的风景以及迈克尔对于风景的感知与想象。
一、 风景与创伤
“风景”(landscape)又称景观,它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术语,指“一个地区的外貌、产生外貌的物质组合以及这个地区本身”[1]367。本文探讨的风景属于人文地理学上的宽泛定义,既指土地,又包括土地上的树木、草坪、植物、建筑等,侧重于它们的组合排列、外貌特征以及随之产生的意义。英文中的“landscape”从词源学上讲来自于荷兰语的“landschap”和德语的“landschft”,准确对应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地景或土地景观,最初指的就是某一视野中看到的一片土地。随着文学与生态批评、人文地理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学中的风景研究已为更多人所熟知,风景也演变成为一个总括性概念,用以指代“土地”、“地方”、“区域”、“环境”、“空间”、“背景”、“景色”等等,它甚至可以与“空间”、“地方”等词互换使用[2]。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说过,“风景是人的种种努力的聚合之处”[3]126,所以作为一种表征形式,它是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由地理风貌与文化景观叠加而成。
《迈》讲述了小人物迈克尔在充满战争、军队和种族矛盾的南非社会苦苦挣扎的故事。由于天生兔唇,迈克尔注定将不可能得到异性的爱慕和拥有体面的职业,这一无法修补的面部缺陷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从残疾儿监护学校毕业后,迈克尔进入市政园林处成为了一名花匠。后来他也在公共厕所当过值夜人,但他更喜欢美丽的园林,因为“那里有着高耸的松柏和开满白子莲的朦胧小径”[4]3。他对园林的偏爱源于内心的创伤和自卑,也是他沉默的天性使然。旁人总会对他指指点点、窃笑不已,面对鄙夷和嘲笑,迈克尔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缄默。小时候母亲带他去工作,他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母亲擦亮别人家的地板。明亮洁净的空间会将他的兔唇暴露无遗,嘈杂喧闹则令他紧张局促,唯有安静幽闭的园林才让他感觉安全。人文地理学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各种感受的综合就形成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迈克尔对于园林的依赖就是这种地方感的体现。开普敦带给迈克尔的只有痛苦,于是当生病的母亲向他描绘逃离城市返回乡下的计划时,乡村生活瞬间如荷兰风景画一般出现在迈克尔的心中:“一座刷得雪白的农舍,坐落在宽阔的草原上,农舍的烟囱冒着袅袅的炊烟”[4]9。风景在这里早已超出了视觉艺术的范畴,它是一种“头脑和感觉的建构”[3]89,不仅承担了疗伤的功能,还成了迈克尔母子精神的乌托邦。风景给予他们慰藉并让他们暂时摆脱现实的残酷,也为母亲死后迈克尔的一系列逃避行为埋下了伏笔。
研究者多倾向于在南非这一大的语境下对其作品进行探讨[5],解读《迈》中的风景当然也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南非素有“彩虹之国”的美名,地貌特征复杂多样,丛林、沙滩、草原、森林、高山一应俱全,号称“拥有全世界所有的风光”。可迈克尔在回乡途中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当他进入一所被人遗忘的房子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到处野草丛生,苹果园内“被虫子咬过的果子遍地都是”[4]47。他随后被警察毫无缘由地带走,和五十多个陌生人一道被赶上了火车,经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光秃秃没人照料的葡萄园”;他还被迫参与了铁路的抢修,亲眼目睹“铁轨被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的像小山一样的岩石和红色黏土盖住了,塌方在山脚处形成一道宽宽的裂缝”[4]51。无论是无人打理的空置房屋,还是荒芜凋零的苹果园和葡萄园,或者是山崩后布满伤痕的地表,这些风景描写绝非闲笔。它们既呼应着迈克尔个人的沉默无语,又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非社会的真实写照;既是殖民历史与动荡现实的象征,也是种族隔离与文化创伤的空间表述。W.J.T.米切尔认为,风景不应该被仅仅当做“看的对象或阅读的文本”,而是“社会和主体身份得以形成的过程”[6]。风景除了与地理描述有关,更应该与心理感知与文化建构联系在一起,它形象地阐释了居民的生产方式,反映着社会生活与人类的存在,所以迈克尔在观看风景的同时,也在亲历并审视着南非的创伤。库切笔下的风景没有诗意,也没有所谓的异国情调,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以冷峻的笔触勾勒出南非荒凉的地景,关注着南非的历史与现状。
二、 风景与权力
风景归根结底是一种观看之道,伯格指出:“我们‘看见’风景时,也就身入其境”,“倘若有人妨碍我们观看它,我们就被剥夺了属于我们的历史”[7]。伯格点出了风景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因此看到了什么、怎么看、什么被允许看、什么不被允许看,这些都是讨论风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时应当注意的问题。《迈》深入探讨了权力对于人的压迫与惩罚,书中沉默的风景同样也受制于权力的规训,是多重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除了废弃的农舍、果园,小说里还出现了各种以营地的形式存在的监狱和医院。逃离了修铁轨的人群,迈克尔在维萨基农场耕耘种植,又在山洞里穴居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了警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最后将其关进了安置难民的营地。这个营地看上去是个“黄褐色长方形”,让人误以为是建筑工地,周围全是三米高的围栏,“上面覆盖着一层蒺藜铁丝网”[4]90。营地的房子由木头和铁皮搭建而成,室内黑暗压抑,迈克尔只能走到营地后面的围栏,从那里凝视空荡荡的草原。福柯对规训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8]。随处可见的营地体现出库切作品的南非特色,它们的建造则是权力在空间上的“分配艺术”,象征着政治、军队和战争在人身上施加的规约。迈克尔在寂静的营地中失去了观看风景的权利,因为眼前除了铁丝网就是荒芜的草原,而当地理景观最终沦为规训场所的时候,权力也就完成了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和约束。
段义孚认为,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总是喜欢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扭曲并改造了自然的本来形态[9]。营地从地理形态来说就是权力对于自然景观的改造,作为人为搭造的建筑,它不仅破坏了大自然的原始风貌,而且强行把人与他们所处的环境隔离开,是强权政治在地理空间上的表征。营地的出现既象征着军队、警察对于赤手空拳的迈克尔所实施的规训,又突显出了人类对于自然地貌的摧毁,二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迈》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态文学中展示的现代工业对于自然环境的污染,却领略到了权力对于自然景观的征服和压迫:“每隔一两英里就会有一道围栏”,“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竖起一道道围栏,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4]120。迈克尔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尚未属于任何人的土地,即使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和边缘,也未必能够逃脱权力的掌握和监控。
福柯曾说:“权力必须被当做是可流通的东西来分析,或者是以链条的形式来运作的东西。”[10]简单讲,权力应该被视做动词而不是名词。风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米切尔提出风景研究的目的在于将风景由名词变为动词,所以除了关心“风景是什么”或“风景意味着什么”,还要询问“风景做了什么”。小说中的残疾儿监护学校——休伊斯·诺雷牛斯——是另一个重要的规训场所,各种残疾儿童在这里按要求学习文化并参加体力劳动。库切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描绘迈克尔在这所学校的经历,除了在梦境中,它的出现都与风景有关。迈克尔在营地内备受煎熬,于是想起了穴居的山洞,还有那里“奔腾不息的溪流”[4]91,他想象自己第二次回到了休伊斯·诺雷牛斯。脑海中的风景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迈克尔内心紧闭的记忆之门,让他重新回到了当年接受训斥和惩罚的地方。迈克尔在大山中发现“山腰上漫山冒出了无数粉红色的小小花朵”,在饥饿的驱使下吃了一捧鲜花[4]84,他也再次回想起了当年在休伊斯·诺雷牛斯的饥饿岁月,还有老师手拿戒尺在学生中巡视的场景。迈克尔后来不无感慨地想道:“我的父亲就是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就是“宿舍门上贴着的那些规定”[4]129。正是学校里的规章制度奠定并建构了迈克尔的身份,使他成为了权力规训的产物,也只有在面对风景时他才会浮想联翩。沉默的风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迈克尔自我的投射,因为它不仅被迈克尔“看”,而且还让他“看见”了从前身处权力约束下的自己。
三、 风景与逃避
逃避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处事方式,可是“一个人受到压迫的时候,或者是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肯定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迁往他处”[11]1。逃避的对象既可以是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可以是忍无可忍的规章制度,还可以是喧嚣的城市或破败的乡村。《迈》从本质上讲是一部关于逃避的小说,迈克尔就曾被新营地的医务官称为“了不起的逃跑艺术家”[4]203。城市在小说中意味着暴力和冷漠,无论在学校还是医院,城市空间都充满着权力的制约与监视,逃往别处才是迈克尔母子唯一的选择。是母亲首先提出逃离的计划,至于目的地是记忆中的沃斯卢或维瑟农场,还是迈克尔到达的维萨基农场,都已不再重要。库切作品的寓言性决定了他对人类处境、现代社会中人生存的悖论的关注。那么,风景对于迈克尔的一系列逃避行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又在迈克尔的逃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趁押送抢修铁路人群的士兵离开之际,迈克尔钻过栅栏上的窟窿,走向了沙漠中的绿洲。他找到了母亲所说的农场,再把她的骨灰洒进地坑。然后他成为了一个耕耘者,种下了南瓜、玉米和青豆。“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日落的时候,打开水坝壁上的开关,看着那清清的水流,汩汩地沿着水渠流淌,滋润着那干旱的土地,把它从黄褐色变成深棕色。”[4]73人类自古以来就有逃向自然的情结,久居城市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对乡村产生向往和亲近,但如段义孚所言,“人们逃往的自然必定已经被人文化了,且被赋予了人类的价值观,因为这种自然是人类愿望的目标所在”[11]21。逃向风景就是迈克尔躲避城市、战乱的动力,风景以想象的方式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庇护所。迈克尔曾有机会接触母亲的雇主被水浸过的书籍,他从不喜欢书籍,却花时间从插图书籍上撕下了一些风景照片,它们摄于爱奥尼亚群岛、西班牙、芬兰和巴厘岛等旅游胜地。南非动荡的现实剥夺了迈克尔亲历现场观看这些风景的权利,但并不妨碍它们以想象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内心。迈克尔羸弱的身体无法与强大的战争机器和权力话语抗衡,对美丽风景的渴望驱使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和一次次逃避,回归最原始本真的自我。看到农场从荒芜走向欣欣向荣,迈克尔感到抑制不住的狂喜,是变化中的景观让他被压抑的天性得以释放,他又恢复了园丁的本色,在开垦中享受着远离尘嚣的祥和与安宁。
巴什拉首次使用了“topophilie”一词,借以指代“场所爱好”[12],段义孚则率先将其英语化为“topophilia”(恋地情结),宽泛地定义为“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13],以此阐释人与地方之间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巴什拉意在突出人“与自然界和情感充溢的地方之间的感情联系所激起的诗意的幻想”,段义孚强调的则是“把个人、团体与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想象性体验”[1]737。“恋地情结”彰显了地理意识中的美学感知,并将其与怀旧、空想结合起来,是驱动人类环境行为和态度的力量,地方与空间也就成为了人们感受个人或集体身份的场所。在夜色的掩护之下,迈克尔伺机翻过了围栏,又一次逃回了维萨基农场,“在水坝前他感到像在家一样自然亲切”,他告诉自己:“我要永远住在这里,这是我母亲和姥姥生活过的地方”[4]123。尽管维萨基农场很可能并非母亲的出生地,“也许只是一个语言的恶作剧”[4]143,但在迈克尔心中,它早已与家园划上了等号。他合上双眼,在脑海中复原母亲故事中当年的场景,包括“那些土坯墙和芦苇盖的屋顶”、“长满刺梨的花园”以及争抢鸡食的小鸡[4]144。迈克尔的“恋地情结”源于大自然赋予的壮美与风景中感知的短暂愉悦,它们让他体验到了一种同样短暂却更加强烈的欢乐。除了视觉,这种反应同样来自触觉和听觉,在迈克尔感受空气,聆听并触摸流水、土地时,他也想象性地建构了母亲儿时生活的场所,并将其等同为自己梦想中的家园。是大自然的风景让他一次又一次选择了逃避,使他一边离现实越来越远,一边完全沉浸在了逃避所带来的欢愉之中。
四、 结 语
小说结尾,迈克尔在又一次逃跑后回到了熟悉的开普敦,故事在叙事层面上由此形成了一个无望的循环。迈克尔不是圣人,也不是拯救者,如果小说的情节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它必定会重新陷入逃跑与被捕的宿命轮回,有关沉默与逃避的讨论似乎也会无休止地持续进行。关于南非拯救之道的说法,其实只是个一厢情愿的臆测,而拯救神话的破灭恰好证明了对抗权力的必然失败。逃避的最终结果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迈》继承了笛福以来的小说传统,也蕴涵着卡夫卡、贝克特式的荒诞与晦涩。小说中的风景是无法被简单视为背景或陪衬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迈克尔的另一个自我,因为“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14]。人文地理学为解读库切笔下的自然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它能与生态批评互为参照、相得益彰,而对于库切小说中风景的研究也将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约翰斯顿 R J. 人文地理学词典[M]. 柴彦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 Mitchell W J T.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Landscape and Power: Space, Place and Landscape[M]∥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ⅷ.
[3] Tuan Y F. Thought and Landscape: The Eye and the Mind's Eye[M]∥Meining D W.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库切 J M.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M]. 邹海仑,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5] 段枫. 库切研究的走向及展望[J]. 外国文学评论, 2007(4):139-145.
[6] Mitchell W J T. Introduction[M]∥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1.
[7] 约翰·伯格. 观看之道[M]. 戴行钺,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5.
[8]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3:160.
[9] 段义孚. 人文地理学之我见[J]. 地理科学进展, 2006(2):1-7.
[10] Foucault M. Two Lectures[M]∥Gordon C.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1980:98.
[11] 段义孚. 逃避主义[M]. 周尚意,张春梅,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12]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23.
[13]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93.
[14] 唐晓峰.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J]. 读书, 2002(11):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