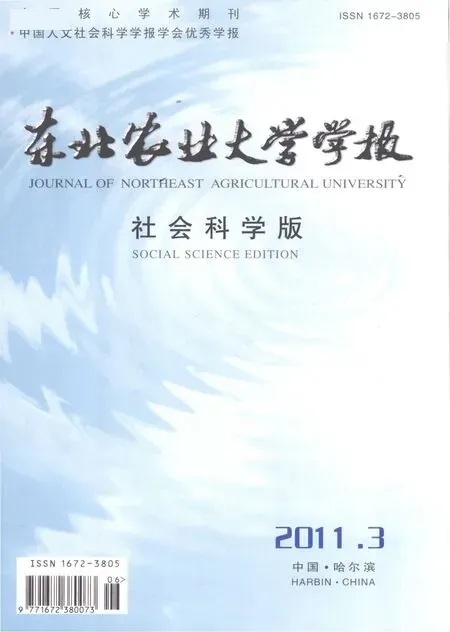“文化转向”视域下《围城》翻译策略的不确定性研究
肖琳康冰
(黑龙江科技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7)
“文化转向”视域下《围城》翻译策略的不确定性研究
肖琳康冰
(黑龙江科技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7)
翻译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翻译策略的可变性。翻译时如何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充分表达仍然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难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旨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入手探讨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论域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围城》翻译策略形成的影响。
翻译策略;意识形态;赞助人;论域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1989年,国际翻译研讨会在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召开,标志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一个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纵。
1990年,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二人合编了一本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1992年,勒夫维尔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他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思想意识和赞助人结合起来,研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制度、政府、学术界、赞助人等对翻译的影响。他认为翻译与权威和合法性有关,最终与权力有关,重写就是为权力服务的有效手段。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的支配(李文革,2004)。勒弗维尔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他指出文学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这个系统就是文化。而文学这一系统有两个制约因素:文学系统内部因素(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和外部因素(赞助人patronage)。当一些作品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相差太远时,专业人士会出来进行干预或遏制。另外,赞助者最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会严格加以控制,但是诗学方面的问题,一般会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勒弗维尔在阐述制约文学系统因素的基础上,还论述了这些因素对翻译形成的作用和影响。
1.意识形态在翻译形成中的作用。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并非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李文革,2004)。因而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
2.赞助人的力量。译文能否顺利出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赞助人可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政党、出版社、大众媒体等,赞助的力量可以由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三个要素构成。赞助人对译者施加权威的影响,一般不重视诗学,而是重视文学的思想意识,依靠译者使文学纳入自己的思想意识体系。因而赞助人是影响翻译策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论域。译者对于论语的态度,取决于原文的地位、目的语文化的自我形象、目的语文化可以接受的文本类型、措辞、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象及其所习惯的行为模式等(李文革,2004)。如果原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享有较高的地位,翻译时一般采取异化的策略,如果原文在目的语文化中地位不高或处于劣势,翻译一般采取归化的策略。同时,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译文也有影响,读者的期待与反应也是决定翻译策略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4.诗学。诗学包括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等文学要素和观念,诗学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甚至是由意识形态的力量所产生。译者常以自己文化的诗学翻译来满足读者期待,译者会在原作诗学和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寻求平衡,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力求创造一个既充满文化融合又具备一定诗学影响力的优秀译作。
二、影响《围城》翻译策略的不确定性因素
《围城》是钱钟书一生所著的唯一一本长篇小说,是作者“锱铢积累”之作,书中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再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该书涉及的知识面广,内容复杂,语言千变万化,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挑战。美国作家兼翻译家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美籍学者茅国权(Nathan K.Mao)将《围城》翻译成了英语,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焦点多集中在文化和翻译策略方面,译者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但有学者认为该翻译策略选择失当,译文存在很多缺陷。胡定邦先生认为译本中存在很多成语翻译是令人费解的直译,没有做文化调整,孙艺风先生也认为《围城》英译本中有汉语式倾向。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策略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新的研究视角,从意识形态、赞助人、论域等方面来看《围城》的翻译策略。
1.意识形态对《围城》翻译策略的影响。《围城》的英译本是1979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当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国际关系出现新的变动时期。中美关系日渐改善,这使得平等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成为现实。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排除非学术干扰,注重文学文本研究的强烈呼声,使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纷繁多样的局面(张泉,1991)。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此时美国也开始重新研究钱钟书的论著。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籍学者夏志清就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钱钟书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有关钱钟书的其他译著直到“被冷落的10年”以后,在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得以发表。具体到《围城》这部作品,杨绛先生在《围城》汉英对照的前言中提到,译者早在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信要求把《围城》译成英文,但正值文化大革时期,为此钱钟书受到“工人师傅”盘问,似有“里通外国”之嫌,因此作罢,直到1979年,钱钟书随同社会科学院访问美国,遇到译者,得知她已与茅国权先生一起把《围城》译成英文,并已找到出版社,钱钟书就授权出版社出版。这个英译本是《围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该译本正好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翻译理论承上启下的时期,翻译由传统的尊重作者、“求同”发展到注重读者、“存异”,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出发,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这种异化思潮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关(陈胜利,2005)。《围城》翻译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中意识形态的产物,译者顺应社会思潮采取了“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2.《围城》翻译的赞助人。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力不容低估,它也是影响翻译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围城》翻译的赞助人,杨绛先生在汉英对照本前言中也有提及,“钟书随代表团回国不久,他在美国认识的一群朋友到我家做客,包括出版《围城》的负责人和几位赞助的教授。有一位教授的夫人是无锡人,据说她家和我无锡老家是紧邻,只一墙之隔。”另外,译者在译序中也有涉及赞助人,并对七个人表示感谢,其中有六位的名字包含中国姓氏,这当中就包括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由此可知,《围城》翻译的赞助人多为海外华人学者,这些人热爱祖国文化,致力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异化是最能保持原语文化的翻译策略,那么译者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就合情合理了。
3.论域对《围城》翻译策略的影响。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李文革,2004)。原文的地位、目的语文化可以接受的文本类型、目地语文化的读者对象等影响着译者对论域的态度。译者在决定翻译策略时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然而不管钱钟书本人还是《围城》这部小说在西方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海外学者称钱钟书是中国“第一博学鸿儒”(《中国时报》1979年6月16~17日);由于他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他的长篇小说《围城》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夏志清在《论钱钟书的小说》中曾对《围城》给予很高的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对未来世界的中国读者,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弗兰西斯.兰德尔则称《围城》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它深奥微妙,发人深省,显示了作者的才能(陈胜利,2005)。“真正能够代表外国学者的”丹尼斯.胡,从语言文学角度研究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也给予了作品本身很高的评价(杨芝明,1992)。文化学派认为当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享有较高地位时,译者一般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鉴于《围城》在西方享有较高的地位,正好采用异化翻译。再次,从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来看,译者茅国权在《围城》英译本导言中说,《围城》是钱钟书1949年以前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是一部带有许多流浪汉故事式幽默风格的喜剧,也是包含着对恋爱婚姻的讽刺、评论和对当代人研究的学者小说。译者还指出,这种学者小说文体是用来满足特定的文人阶层在知识和文学的其他方面的自我表现的要求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文人、知识分子阶层具备特殊的文化底蕴,易于接受新知识和外来文化,能够尊重原著,异化的翻译在知识阶层中更容易得到认可和接受。另外,文化学者认为,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文学样式也有期待,译文文学样式也必须符合读者的这种期待,读者对象在决定翻译策略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西方,对《围城》这部学者小说期待最大的多是那些海外学者和海外钱迷,他们阅读译文也是希望借此欣赏原作特有的语言和风格韵味,进而了解中国文化,而这些读者本身有着一定的知识、文化底蕴,大多又得益于中西方两种学识,异化的翻译策略能保持原著特色,满足读者期待,使其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国语言与文化,可见译者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实是明智之举。
三、结束语
译者在决定翻译策略时,充分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接受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尊重赞助人的思想意识,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诗学之间寻求平衡,兼顾到译文读者对文本样式的期待与可接受性,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不但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与风格,还使作品涉及的中国文化得以彰显和有力传播。
[1] 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rdiscipine[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4:2.
[2]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5~221.
[3] 钱钟书.围城(汉英对照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3.
[4] 陈胜利.《围城》的翻译策略及其成因[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4):10~12.
[5] 张泉.钱钟书和他的《围城》:美国学者论钱钟书[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7~29.
[6] 杨芝明.《围城》研究综述[M].北京:三联书店,1992:238.
An Analysis on Uncertainty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Fortress Besieged from the Cultural Turn Perspective
Xiao Lin,Kang Bing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7)
The vari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on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ranslation uncertainty.The proper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ensuring the full expression of meaning in source text remains a problem for which culture re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This paper provides a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Fortress Besieged influenced by ideology,patronage and field theory,etc.from the prospective of culture re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trategy,ideology,patronage and field theory
I206.7
A
1672-3805(2011)03-0114-03
2011-02-20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语境阐释”(编号:11552260)
肖琳(1981-),女,黑龙江五常人,黑龙江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