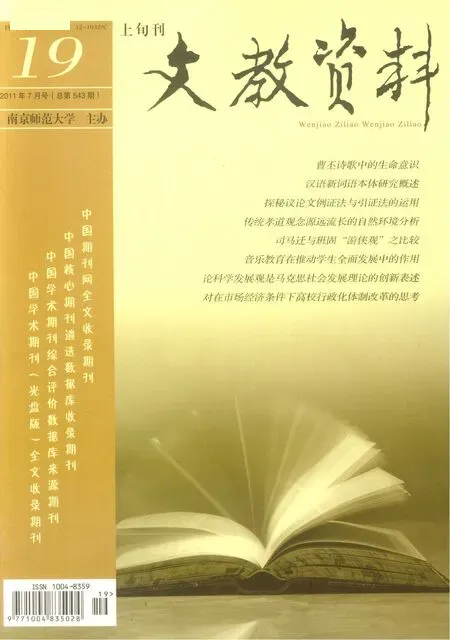一曲长恨歌,一场海上繁华梦——谈王安忆小说《长恨歌》
韩雅琪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有人说最能展现一个城市的历史莫如这个城市的子民,而在中国千百座或是古雅或是传奇的城市里,上海是最让人记挂的。半个世纪前,张爱玲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半个世纪后,王安忆谱一曲《长恨歌》,书写弄堂女儿的别样人生。在小说《长恨歌》里,我们看到了太多张爱玲的影子,流言、旗袍、爱丽丝,那些旧式的繁华和落寞,也因此王安忆为一些学者所诟病。本文主要对《长恨歌》中上海弄堂女儿形象的女性叙事分析和悲剧淡化处理两个层面进行细读。
一、上海弄堂的女儿
首先,细节描述向来是女性叙事的特征,因为细节同“国家”“统一”“革命”等宏伟的见解相抵触,它常常是感性的、繁琐的、冗长的章节。[1]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总是闭月羞花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上海的时装潮流,她们是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姐妹怯怯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2]小说一开篇用三个小节介绍“弄堂”、“流言”和“鸽子”,前三者细密地铺垫让主人公形象蒙上了一股温婉迷离的色调,半推半就间王琦瑶登场了。她是美丽的,乖巧的,谦虚的,不那么高不可攀的,可亲可爱的小家碧玉。用作者的原话说:“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的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做王琦瑶。”此时的王琦瑶还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偶尔同朋友吴佩珍耍点小心计,维持在小姐妹情谊间的优势状态罢了。最有意味的一处细节是王琦瑶在片场受挫的经历,当时吴佩珍的哥哥让王琦瑶去试镜,王琦瑶满心期待到了片场,当镜头灯光打照在她身上时,缺乏生活经历的她木然了,拍摄扫兴而归,为此她同吴佩珍的友谊也就撕裂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太没有面子了。
弄堂的女儿是富有心机的、爱慕虚荣的。和吴佩珍分手后,很快蒋丽莉成了王琦瑶红花下的绿叶,如果说开始住在蒋家里是蒋氏母女热情促成的,那么之后王琦瑶一面迎合蒋母,一面哄着蒋丽莉,都说明王琦瑶的深谙世故,利用她们家的优越条件,过她小姐般的生活。而后程先生同王蒋的“恋爱悲剧”,亦入木三分地展现了弄堂女儿的世俗面貌,不觉可憎,反而有些可爱的味道。及至同李主任相遇,有了第一段充满冒险的爱情,不得不说是一种虚荣使然。即使是成了女儿都出嫁了的母亲,她依旧憧憬着风姿绰约地吸引异性,依旧要在舞会和派对中缅怀往日的罗曼蒂克。
作者一次次写道:“王琦瑶的美不是那种文艺美,她的美是有些家常的,是在课堂供自己人欣赏的,是过日子的情调。她的美里缺少一点诗意,却是忠诚老实的。”[3]在这里,作者反复这样描写,正是为了表明王琦瑶虽然有出众的相貌,但至多不过是个平凡的女子,可以说已经暗暗埋下了伏笔,王琦瑶上不了大阵仗,抬不起大局面,她不属于十里洋场中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如陈白露、葛薇龙一般,爽爽利利过一把梦幻泡影的生活。她是上海所有弄堂女儿的代表,所以她是选美比赛的“三小姐”,冠以“沪上淑媛”的名目,“这名字有着海上生明月的场景,还是人海,月是寻常人家月”。[4]
其次,女性主义叙事在王安忆小说的创作中显现出一种普遍男弱女强的两性关系叙事模式,解构了传统的男强女弱的性别秩序,显现出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是王琦瑶,故事围绕她的一生进行叙述,从整体来说王琦瑶作为弄堂女儿的化身始终处于被高举的地位。虽然作者也揭露王琦瑶的弱点和她的市民气味,譬如描写她如何自甘自愿当李主任的情人,如何勾引毛毛娘舅,如何同芳华正茂的女儿斗气,但都是带着理解的温情笔调来叙述,并且十分明显地显现出一个弱女子在大时代中的随遇而安。值得一提的是,像王琦瑶似的女性,行走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一条路,既区别于女权主义作家笔下的“出走的娜拉”,投身革命事业或者现代化职业,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在家相夫教子的瑞珏。她受过高等教育,但她选择类似交际花的生活,似乎屈身了,似乎堕落了。
不过张爱玲在散文《谈女人》里说:“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徐图大举?”[5]屈从只是暂时的,沉默是更激烈反抗的前兆,王琦瑶是弄堂的女儿,身上散发着这个都市特有的物质气息和欲望气息,这是一个普通都市女性的平凡甚至平庸。这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作者自身的女性观,王安忆所认同的女性是那种内心足够强大,能强忍着压力面对生活的风云变幻,而不从道德的圈子对这个女性进行品评。
二、“悲剧”的淡化
哲学家叔本华在揭示悲剧内涵时,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其一是“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其二是“盲目的命运”;其三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6]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当推第三种悲剧,用今天小说的语境解读,也就是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自然生成的悲剧,包括意念悲剧、性格悲剧和心灵悲剧。
相比于白居易笔下的唐明皇与杨玉环的悲欢离合,我们在审视小说《长恨歌》的时候,会发现披盖在充满悲情意味名字下的这个故事似乎不是那么的感人肺腑,让人唏嘘怅恨。可以说,《长恨歌》所呈现的故事似乎刻意淡化了悲剧意味,她的一生也将只是平凡的,李主任的匆匆来去,犹如惊鸿一瞥,即便偶有波澜;同毛毛娘舅和老克腊产生的爱情,面对岁月沧桑的洗礼,同朴实的生活相比,也变得无足轻重了。王琦瑶式的弄堂女儿有几分浪漫,就有几分实际;有几分风光,就有几分惨淡。王琦瑶的人生既不是意念悲剧,又不是性格悲剧,更不是心灵悲剧,读完小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共鸣。
王琦瑶最后在“碧落黄泉”一节里死于小流氓“长脚”的手下,这也是长恨哀歌,繁华一梦中少有的一次怪诞之美与忧郁之力。和这个死亡联系起来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和一个妇女老态的细颈脖。没有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严肃意味,而留下了一种被轻侮的肮脏罪恶,这把小说先前各种美好流丽的画面全部瓦解了,这样的一种结尾处理是作者特意地反叛,因为王安忆本来就要写一部别样的上海故事,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是一个由“流言”编织而成的上海故事,它是小“历史”。
此外,不知道是否因为部分运用了文学经典《长恨歌》的名字和其中故事的意味,作者在叙述王琦瑶的故事时,时不时特意安排了伏笔,例如主人公一出场有一处闲笔写道:“爬山虎的长寿也是长痛不息上面写满的是时间的字样,日积月累的光阴的残骸,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是长痛不息的王琦瑶。”还有当王琦瑶逃难回到邬桥外婆家时,外婆有这么一番心理活动:“外婆看着眼前的王琦瑶,好像能看见四十年以后。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如此的经营描写,把王琦瑶的最后结局又推向了命运说。而这样的一种处理,同样也淡化了小说的整体悲剧意味,因为这不关乎王琦瑶在人生选择上的挣扎和抗争,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激愤。
三、结语
“张爱玲的人生观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实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是人生奈何的虚无”。[7]王安忆试图在张爱玲影响的焦虑之外另辟蹊径,《长恨歌》作为一种模仿中的创造可以无愧。但小说失却了艺术张力上的壮美和苍凉,精致装帧的图卷虽然极繁复极华丽,还是让人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
[1]周蕾.现代性和叙事——女性的细节描述.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2008:268.
[2]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19.
[3]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30.
[4]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36.
[5]张爱玲.谈女人.色·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红楼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
[7]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上海女性.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239.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