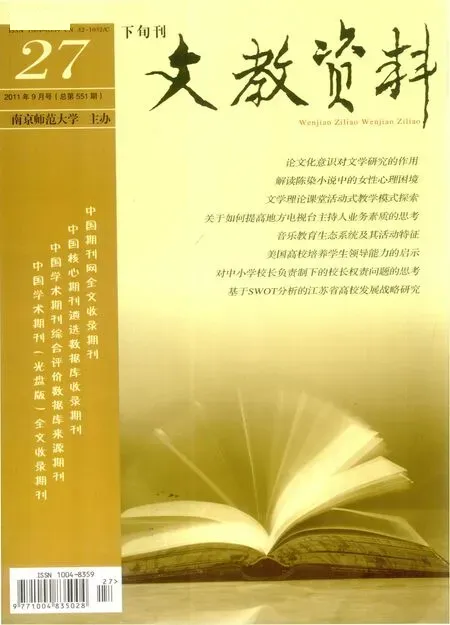艾拉白拉的另类胜利
郭高萍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淑和艾拉白拉,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两个女性是灵与肉的象征,或者是男性精神与身体欲望的折射。“事实上,淑和艾拉白拉是驾着柏拉图灵魂之车的白马和黑马,是高贵的和卑贱的两种本能”。[1]而且,在大多数评论中,艾拉白拉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是诱惑男人的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如果将艾拉白拉这个下层妇女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或许读者会理解这类中下层妇女在性别秩序中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痛苦。
《无名的裘德》的叙述主要围绕裘德、艾拉白拉、淑和费劳孙这四个人物的复杂关系展开,但在小说开头,叙述者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说明女人最厉害,可以让男子“丧失了神智”,“丧了命,栽了跟头,犯了罪恶”,说明此小说主要探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暗示女人对男人生活的破坏性作用。叙述这一女性具有破坏性的主题主要是通过裘德和艾拉白拉的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当艾拉白拉首次出场时,即当她用猪鞭这个性的象征打中裘德时,就表现出这个女人的与众不同,这就是她公然对男人发出一种性的召唤。小说中设置了对比的情况来表现,一边是裘德念念有词地计划自己的事业,一边是艾拉白拉和女伴讨论着影射肉欲的说笑,他没有听到她们的谈笑,而是沉溺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看”到自己的未来印在地上,是什么样的未来呢?他还未细看,就被猪鞭打了个正着。这里,叙述者将裘德正在计划的生活与现实中艾拉白拉和女伴的活动、声音等进行对比,暗示他将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俗世界发生联系,而这个世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裘德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艾拉白拉的出现似乎让他重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内心对异性的渴望也觉醒了,他本打算利用休息的时间读书,但是最后却是跑去和艾拉白拉见面。小说写出他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时的内心斗争。这里裘德显然是被对异性的本能欲望所捕获。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那个女孩子既然选了那样一种武器,向他进攻,那她绝不是什么祀神的贞女”,[2]但是他还是无法抑制想要见艾拉白拉的心情,他只觉得“现在出现了使他感到狂欢的新东西了,只觉得,他现在找到发泄感情的新出路了”,在艾拉白拉的性的激发鼓舞下,裘德被“捕捉”了。
小说中,叙述者有意识地将艾拉白拉塑造成一个肉欲的化身,从她的外貌到举止,都描绘出她身上所散发出的一种呼之欲出的肉欲之感。“她的胸部圆圆鼓起,嘴唇丰满,牙齿整齐,脸蛋儿像一个交趾鸡下的蛋那样红润,确实是一个健壮茁实、味道十足的雌性动物,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3]在文本中,叙述者多次用《旧约·士师记》中的参孙隐喻被诱惑的裘德,而用大利拉隐喻艾拉白拉,叙述者有意识地反复在文中强调艾拉白拉对裘德情欲的诱惑,对裘德人生的破坏性。
在文本的男性修辞里,叙述者对艾拉白拉的叙述多是“物化”的,她是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性符号”。叙述者不仅直接称她为“雌性动物”、“母老虎”,还多次把她和“猪”的意象联系起来,并着力写她的性感部位,从语言学角度而言,这都是一种隐喻,隐喻女性的肉欲。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表现性的欲望是男人的特权,如果女人表露出这种欲望,就会被社会视为不道德。虽然劳伦斯在创作中,尤其是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受到哈代的影响,但他也曾指出,哈代对艾拉白拉的描写是“哈代的败笔”。[4]这是因为,叙述者总是站在裘德这个男性的视角来批判与艾拉白拉的关系对自己理想和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而忽视真实展现艾拉白拉的自然本性和生存境况。
在文本中,艾拉白拉多数是处于“失语”状态,她做事的动机和生活状态多是借叙述者和其他人物转述的,她的内心世界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感到这个全知叙述者自始至终都一味谴责她对裘德的诱惑和欺骗性婚姻,这种叙事策略就使这个女性更容易被读者理解为不道德的诱惑者,而忽视她们在性别秩序中的困境和内心的痛苦。当我们考虑到当时下层妇女的社会地位时,就会对艾拉白拉有另外一种理解。艾拉白拉的个别言语也反映出她内心的隐痛之声。
19世纪的女性由于被逐渐排挤出社会公共领域,经济上、政治上沦为附属的地位,只能以主流文化的异己力量而存在。“嫁人”几乎成了唯一向女人开放的体面“职业”,艾拉白拉的父亲总想着要把女儿“打发”出去,出身下层社会的她想要过上体面的日子,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才可能实现,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也只能求助于婚姻。如果暂且不论当时的宗教对婚姻的界定,那么她的婚姻一共有三次,对象分别是裘德、卡特勒特、裘德,而不论是哪一次,都体现出一个下层妇女为了争取获得一种相对体面的生存状态而做出的努力,而不论她采取什么办法。
当艾拉白拉首次遇见裘德时,裘德正是一个勤学苦读的有志青年,有望迈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而她对裘德也颇有好感,虽然她原本想先好好谈恋爱再结婚的,但是她那些女伴告知她,可以通过假怀孕的方法,促使正派老实的裘德尽快娶她。当她听说这个办法后,第一反应是诧异,接着表示:“我是没有想到那样!……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去冒险!”可见,她并非天生就会勾引男人。她最终采用女伴教的办法,不过是希望早点嫁给裘德,离开缺少亲情的父母家,和裘德过上幸福的二人生活。
可是,贫穷老实的裘德缺乏较好的经济基础,缺少生活常识,认为艾拉白拉的欺骗性婚姻毁了双方,当初对她的激情也突然消退,所以艾拉白拉决定和父母移居澳大利亚谋生,并认为在那里将有着比在英国偏僻乡下更多的发展机会。文中没有交代在异国他乡她离开父母家的原因,只是告知无依无靠的艾拉白拉在悉尼接受了一个旅店老板卡特勒特的求婚,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回到英国的艾拉白拉在基督寺的一个酒店做女招待,偶然与裘德重逢,而此时的裘德并未改善生活环境,也未提升社会地位。当艾拉白拉用学监、牧师、绅士一一询问裘德时,他仍旧是以前落魄的样子,只是心中充满对另一个女人淑的爱恋。所以当澳大利亚的卡特勒特到伦敦新开一家旅店,邀请艾拉白拉过去一同经营时,她同意了,并写信希望裘德保守她重婚的秘密,以便她能继续过着体面舒适的生活。
当艾拉白拉成为寡妇后,她心中又重现燃起对裘德的感情。当她的财产被父亲拿走,并被父亲粗暴赶出家门以后,她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完全失去了生活支柱,所以才向裘德求助,她在心理上也感到,在全能的上帝眼里,裘德才是自己唯一的丈夫。而且,她对裘德仍存有旧情,如果重新与裘德结婚,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上和名誉上的不利地位。所以,她进而促成双方的第二次婚姻。在裘德临终时,她也开始寻找下一个结婚对象,并自言自语:“唉!可怜的女人,总得事先就提防一下。我楼上那个可怜的家伙要是不中用了……我得先开个门儿。我这会儿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挑挑拣拣的了。找不到年轻的,只好弄个年老的了。”[5]如果说她两次和裘德的婚姻中还有一些喜欢对方的成分,那么这里就完全是为了谋生而结婚了。
叙述者对艾拉白拉的谴责,主要是她与裘德的二次婚姻改写了裘德原本的求学之路,使他不得不年纪轻轻就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而放弃人生理想。可是,深入文本之中,就会发现裘德的人生失败并非因为艾拉白拉的偶然出现,而是因为在当时不公平的社会中,像他这样的下层青年无法对抗传统落后的习俗势力,所以在事业和婚姻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所以,将裘德的失败归于女人,尤其是艾拉白拉,实在有所偏颇。
从艾拉白拉的生活经历看,她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女人,从一开始嫁给裘德,她就养猪,和裘德共同经营家庭;发现裘德不爱她时,她就跟随当时的移民浪潮,和父母移居到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希求到海外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从澳大利亚返回英国后,她选择到一个别人不认识自己的地方,通过做酒吧女招待维持生活。可以说,她一直秉承一种实用主义的生存哲学,努力自主去谋生,虽然在她心中,她也希望有个能干的丈夫可以依靠。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被男人所控制和支配。但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艾拉白拉在每一次与男性的角逐中,都成为胜利者,原因何在?她的胜利在于她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利用两性游戏规则,奋力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可以说,这是作为社会弱势一方的女性利用性别秩序的另一种“现实”,婚姻首先是男性话语保护男性权威的利器,但是同样可为女性所用,谋求一份既定的保护和生存。
可以说,艾拉白拉窥破了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和各自角色,并出色地扮演了男权社会秩序为其规定的女性角色,从而在两性角逐中成为一个主动的被动者。与淑相比,她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芒;与苔丝相比,她不受道德主义的束缚,从资本主义道德的角度讲,她不是一个“贞洁”的天使。这是因为,出身低贱的她也希望活得体面一些,通过合适的婚姻来摆脱缺少亲情的家庭,改变低贱的身份,跻身中产有闲阶级,所以她只是尊奉较为功利的实用主义,通过以身试“法”,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赌博,利用男权话语和两性秩序迫使男人就范。这种举措所挑起的侵犯攻势让她成功地利用男权秩序达到自己功利的目的。通过艾拉白拉屡次赌博式的婚姻,我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被社会公共领域拒绝的下层妇女所面临的实际生存问题,以及她们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状态的另类挣扎。
[1][4][英]A.阿尔瓦雷斯.无名的裘德[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81.
[2]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9.
[3]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6.
[5]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