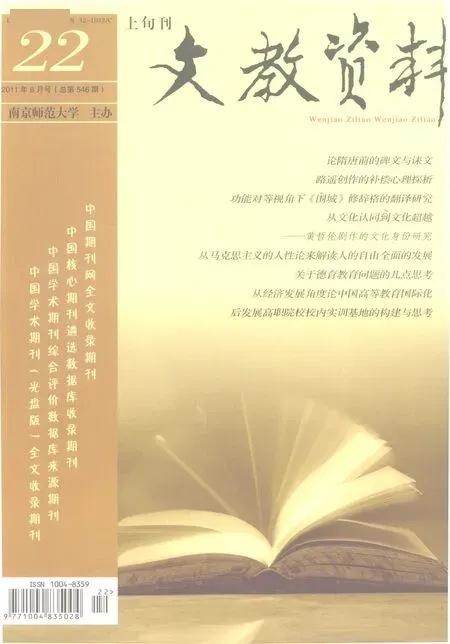浅论宋代僧词对词体功能的拓展
王池琦
(中山大学 中文系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广东 广州 510620)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之日开始,便没有停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受到佛教的影响。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而在佛教与文学融合的众多文学现象中,僧人作词是值得关注的。现存的宋代僧词作品题材涉及阐明佛理、写景咏物、言情、酬唱等,而其中,佛理禅意词就是僧人对词体功能拓展的一个重要尝试。
一、宋僧佛理禅意词对词体功能的拓展
至有宋一代,随着都市的繁荣,作为娱宾遣兴功能的词也显示了其重要的作用,加上文人士大夫的推动,宋代的词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升斗小民,都乐于接受词这种文学样式。因此,僧人也不例外地受到这个影响,僧人为了向世人宣扬佛理,亦采用了词为弘法的载体。“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拈椎竖拂、语言文字种种方便,去圣逾远,诸方学徒忘本逐末,弃源随波滔滔皆是”。[1]随着禅宗的盛行,“语言文字”也是僧人悟道、传道的方式之一。僧人作词,或阐释佛理,或于词中透露禅意,令读者意会。这是僧词的基本题材之一。这类作品,有的大量引用佛教词汇,于词中阐明佛理,摒弃词的抒情功能,而直接作为宣扬佛理的工具;有的则受禅宗思想影响,引禅入词,使词充满禅意。我们将其定义为佛理禅意词。
例如以下这首词,就是直接阐释佛理。佛教认为,人生苦短,苦海无边,人如果不戒除“贪嗔痴”,就无法摆脱现实中的苦难,超脱“六道”轮回;佛教认为“四大皆空”,主张看破放下,皈依佛门,通过修行得以往生西天极乐世界。
娑婆苦,长劫受轮回。不断苦因离火宅,祗随业报入胞胎。辜负这灵台。
朝又暮,寒暑争相催。一个幻身能几日,百端机巧哀尘埃。何得出头来。(净圆法师,《望江南》)
这首词写的是婆娑世界的有情众生,因为业障而受六道轮回之苦,无法得以解脱。“不断苦因离火宅,祗随业报入胞胎。”阐明的即是佛教的“因果观”、“轮回观”,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因果,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涅槃经·遗教品一》:“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
除了直接阐明佛理之外,宋代僧词中还有一类词,通过词来叙述佛教故事,描摹菩萨形象,以叙述来间接起到阐明佛理的作用。如:
深愿弘慈无缝罅。乘时走入众生界。窈窕风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
清冷露湿金襽坏。茜裙不把珠缨盖。特地掀来呈捏怪。牵人爱。还尽许多菩萨债。(寿涯禅师,《渔家傲·咏鱼篮观音》)
相传东海之滨的人们身居化外,不知礼仪,观音菩萨便化作一个美丽的渔妇前来点化。菩萨承诺谁能背诵她所教的佛经便嫁给谁做妻子,结果有一个叫马郎的渔夫如愿以偿,并最终得到了菩萨的点化。表示众生做任何事都要有信心,只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就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同时也能影响周围的人们。寿涯法师的这首词,就是以词来写鱼篮观音的典故,赞颂观音变幻不同的身份来点化信众。
而以下这首词,则是一首充满禅意的词:
咄这牛儿,身强力健,几人能解牵骑。为贪原上,嫩草绿离离。只管寻芳逐翠,奔驰后、不顾倾危。争知道,山遥水远,回首到家迟。
牧童,今有智,长绳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终是不生疲。直待心调步稳,青松下、孤笛横吹。当归去,人牛不见,正是月明时。(悟则禅师,《满庭芳》)
此是将牧牛之词寄以《满庭芳》调,用牧童牧牛,对“回首到家迟”的牛用智慧去调教,来做一个隐喻,比喻人若能修养自己的心性,才能明了自身本性,这和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张是相契合的,禅宗认为应该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晓莹评曰:“世以禅语为词,意句圆美。无出此右。”
从以上词可见,僧人作佛理词,是词体功能的一个新的尝试和拓展。在“以诗为词”观念的影响下,词可言志,甚至可以宣佛,宋代僧词为词体功能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其背后有特有的历史文化因由。
二、宋僧佛理禅意词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
虽然五代时北周世宗曾给予佛教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在宋朝建立政权之后,“就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2]宋朝统治者认识到了佛教对于政治的作用,便停止了对寺院的破坏,通过实施各种扶植、利用的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宋代寺院经济力量相当雄厚,实行试经制度,经过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剃度为僧,但是此制度进入僧人队伍的名额并不多。若要想出家还有两种方法:一是买度牒,成为正式的僧人;二是逃避徭役,“窜名浮屠,号为出家”。[3]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迫于形势和生计而“遁入空门”。佛门出家众鱼龙混杂,显得既不纯洁,清规戒律也不被严格遵守,有些一般的僧人戒行低劣且不说,士大夫式僧人在个人精神生活方面追求享受和奢靡也就成为必然。
另外,随着“三教合一”趋势的增强,佛教(禅宗)越来越被主流社会所重视。禅宗提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心即佛、即心即佛”的思想,主张“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运水搬柴、皆成佛道”,僧人不需要拘泥于念经、打坐等修行形式,有些僧人或放浪于闾里巷陌,或寄形于自然山水,或出没于皇宫侯门,无论是“于云水而得自在”(《五灯会元》卷五)的怡乐之情趣,还是与文人士大夫酬唱的会别之意绪,甚或是对现世的黑暗或个人的不得志的发牢骚、抒愤懑,都比世俗文人来得更自在、更直率,一切都是“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古尊宿语录》卷四)。
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之下,僧人与士大夫也经常交游,宋代禅僧士大夫化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葛兆光说:“经过唐五代禅宗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与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不同,他们不仅历游名山大川,而且与士大夫们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生活安逸恬静,高雅淡泊,又风流倜傥。”[3]士大夫们乐于与僧人交往,僧人也乐于向士大夫谈经论道,因此,佛理禅意词应运而生。
三、宋僧佛理禅意词是词体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代僧人佛理禅意词的创作,是词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词因为其自身强大的娱乐功能,在五代、北宋时期迅速兴起。欧阳炯《花间集序》言:“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千千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直言词在文人士大夫社交宴饮中的娱宾遣兴作用。王国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5]到了南唐,词人寄托的身世之感使得词的内容和意境得以拓宽,词的内容不止是风花雪月、卿卿我我,更也有涉及严肃的生死主题,所谓“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李煜入宋之后的作品,将亡国之痛的大题材作为主要的抒写内容,使词的题材从单纯表现男女恋情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了,与此同时,词已然超脱了其原有的歌唱功能,成为一种广泛的包容性更强的文体,既可以歌唱,又可以抒怀,词开始走向自我化、个性化的发展道路。词至宋初,沿袭了五代传统,早期词人如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作词基本上还是以应歌为目的。宋初词人虽然还是在为曲配歌,但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的词创作中,词作已经开始融入创作主体个人思想、情感等因素。例如,柳永的一部分羁旅行役之词,饱含着词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后来,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对词境又有新的开拓,引入了军旅生活、塞外风貌,注入家国之叹、政治感慨。至苏轼,苏轼重视文辞的主体性胜过音乐性。他提出“以诗为词”的主张,主要有两个中心:一是不守音律,二是扩大题材。也就是说,凡是诗可以写的题材,都可以用词来写。可见,苏轼对于词之功能的认识是抒怀胜于娱乐,吟咏胜于演唱。宋人词体观建构的动力来源于词体内部的矛盾性,表现于词学批评与创作的互动,以及创作中文人词与民间词的互动。苏轼的“以诗为词”固然有他个性因素,但从全局及历史的角度看,它是词功能嬗变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产物。词作为一种诗、乐相互融合的艺术,诗的因素与乐的因素各占一定比重,当词发展到北宋时,诗的比重开始由小位上升到与乐的相同位,且有进一步增长,超过音乐因素的趋势,这时作为综合艺术的词,其中诗的因素必然会表现出它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随着佛教世俗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词这种文体的嬗变内因的驱使,宋代僧人也对词创作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他们将个体对佛学、禅宗思想的理解融入词的创作中,目的是宣扬佛理,吸引信众,同时,也是僧人自身修行生活的体悟。尽管这一类词在数量上为数不多,在艺术成就上未必能与其他类型的词相提并论,但是其在词体功能上的开拓是前所未有的。宋代僧人佛理禅意词,从对词体功能开拓的角度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罗湖野录(卷一).
[2]吕澂.宋代佛教.《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出版社,1991,VOL5:2991.
[3]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4296.
[4]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3-44.
[5]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