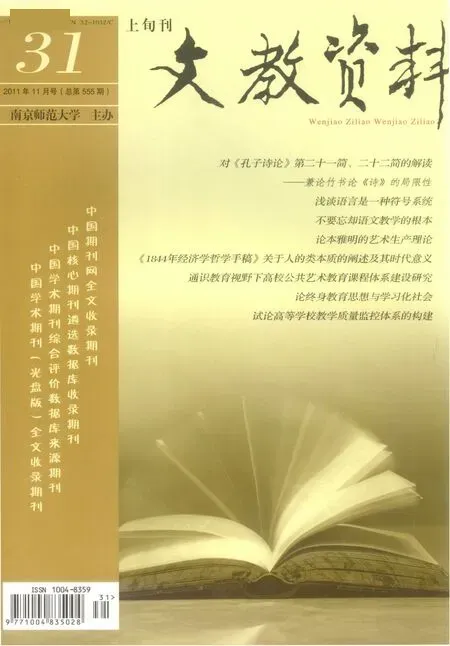探寻女性觉醒的轨迹——论《玫瑰门》中的女性形象
孔 玲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现代文明社会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调,但在封建思想濡染的旧中国,对与男人共同组成社会成员的女人来说,“平等”是遥远得近乎陌生的字眼。受着封建文化的浸润和压迫,女人的奴性迫使她们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在狭隘而畸形的生存空间里苦苦挣扎,却始终逃脱不了男人施予的压制、蹂躏和践踏。她们当中的一些人试图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然而终究挣脱不了女性宿命的桎梏。铁凝以庄家三代女性为落笔的小说《玫瑰门》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真实复原,作家以客观的态度审视特殊历史天空下的女性命运,并以理性的思维寻找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
女性自我意识解放问题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话题,当我们在纠缠于“谁是女性悲剧命运的酿成者”这个问题时,是不是该更加关注女性的自省与批判,质询女性自身?在《玫瑰门》中,铁凝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眉眉,可以说她是铁凝的化身。眉眉,庄家的第三代女性,她是庄家女性故事的陈述者和体验者。而对于整个故事的呈现铁凝也是借由她的成长铺展开来的,从年幼的眉眉到成熟的眉眉,这个人物形象见证着庄家上两代女性悲剧的始末。在这些悲剧的背后眉眉深深地自我反思着,并以跳跃式的眼光审视女性觉醒过程中,庄家上两代女性所遭受的挫折与苦难。
一
婆婆司猗纹是整个作品中最重要,也是极其复杂的女性形象。她出身显赫,聪慧且开朗,跟着家塾先生熟读过四书五经,而后父母将她送进当地著名的教会学校。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与现代文明的新鲜成分在司猗纹的血液里激烈地撞击,司猗纹由此开始了全新的人生历程。“两年的学校生活使她接触了现代文明,使她认识了许多从前她不认识的人,懂得了许多从前她不懂的事”。[1]也就是在这个懵懂的时期,司猗纹遇到了华致远,但她的热恋遭到了父母的规劝和阻止。她生命历程中最初的、也是最决绝的一次反抗是她对自己18岁时爱情遭遇的捍卫与守望。[2]但这一次反抗也只是以司猗纹嫁入庄家达成母亲的夙愿而告终。面对丈夫庄少俭的侮辱,司猗纹竟然遗憾自己的“不洁”,她反省着自己曾经那场美好而又不真实的梦。
纵观司猗纹的一生,是奋斗与抗争的一生。戴锦华称司猗纹是“一个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的要在时代的剧变中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一个绝望地试图作为一个‘纯粹的女人’进入(挤进)历史的女人”。[4]司猗纹的大半生都在积极地活动着,但强大的男权秩序和特殊的岁月冰冷地拒绝了司猗纹的强势超越,她渴求在生存的罅隙间寻找到一丝阳光,巨大的阴影却牢牢地将她包围,司猗纹最初的灵魂在生存困境里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司猗纹是觉醒着的,她折腾一生只为替自己找到话语权,女性主体意识已经在她的身上蓬勃萌动。面对社会和周遭的压迫,司猗纹学会了抗争和还击,在她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股强烈的女性自我保护意识,或许这只是司猗纹出于本能的自我反抗,然而就是这个突然的爆发为女性解放的曲折轨迹添上了一抹希望。虽然司猗纹幡然醒悟,但她并没有萌发健康的女性主体意识,反之,在压制下她选择了相对变态的手段,强烈控诉压迫她的社会和男权制度,这种不健康的报复手段扭曲了女性主体意识解放的正确轨迹,日益畸形的心理将她推进了女性宿命的深渊。
二
“那是一个男人,不,那是一个女人,不,那是一个男人。她不能立刻确定他的年龄,他个子偏高,驼背,无胸,留下一个耳朵也遮不住的分头,耳垂儿肥大。”[7]这是眉眉第一次见到姑爸时对她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反复揣摩和猜测之后,眉眉肯定了姑爸的女性性别。年轻时的姑爸并不是这样的:“乌黑的大辫子,丰满的胸脯,不胖不瘦的身材,不长不短的脖子,不粗不细的腰,不宽不窄的鼻子。”伴随着姑爸豆蔻年华的时代,命运的扭转应该是从姑爸做新娘开始。当姑爸满心欢喜地坐上扎着红绣球的汽车,却不知命运给她安排了三天的时间就将贤妻良母这条路走完了。她在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做了一件令人着实讶异的举动:改名为姑爸。姑爸,“这是一个自我声明,是一个对终生的自我声明。也许还不仅仅是自我声明,这是册封,是宣判,是庆幸,是哀歌,是进入,是逃脱”。[8]“姑爸”这个称呼让她在听觉上享受着平常女性无法领略的声誉和权利,而为了在视觉上跟这个称谓彻底的般配,姑爸全副武装自己:剪掉两条大辫子,穿上西装马褂,迈起四方步,烟袋整日不离手,让自己变成平胸甚至伛胸。很显然,姑爸做着对自我性别角色和整个社会最决绝的超越,她试图用这样的方法谄媚地向男权社会靠拢,却不知这样的方式只是蒙蔽她自己而已。
不管她如何改变自己的外观和生活方式,姑爸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外表之下隐藏的仍然是一个女性的躯体,她选择给别人挖耳屎这样变态的方式来反复地肯定自己的存在感,亦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逃避,不断地催眠自己,使自己的性别意识得到平息和淡化。在封闭的自我空间里,姑爸甚至将自己所有的生活情感都寄托在一只“男”猫身上,“大黄,黄黄,黄乖,乖黄,黄宝贝,黄贝贝……”这些昵称是姑爸用尽了人间所有对爱的形容表达对这只“男”猫溺爱的无极,她的生活中心和重心都围绕着大黄。然而,大黄的闯祸为姑爸平静的生活画上了一个不漂亮的句号。“大黄在号子声中被撕开了,大黄的脚各奔东西”,[9]这不仅仅是撕裂了大黄的生命,更是撕碎了一个女人的所有,姑爸彻底崩溃了。长夜里一声声尖细而又凄厉的嚎叫其实是一曲女人的哀歌,它叫出了强旺的女性本能与无法更改的社会角色之间的长久搏杀的无奈和悲戚。[10]
姑爸嘶哑的叫骂声换来的是小将们的“打、骂、罚跪、挂砖”,和“两腿之间直挺挺地戳在那里的一根手指粗的通条”,历史的暴力赤裸裸地还原了姑爸的女性性别,这是对姑爸穷其一生装扮男人逃避自我性别的最大嘲弄。姑爸试图改变自己的命途,但她将这种改变仅仅寄托在女性性别的抛弃和背离上,或者说她觉得命运的不公只是既定的性别带来的,这种解决办法限制了所有的可能,掩盖了姑爸所有的退路。在男权和性别压迫的社会制度下,姑爸连为自己争取话语权的意识都没有萌生,她从来没有意识到为自己去争取些什么,或者向无情蹂躏她的这个混乱年代反抗过。人格与尊严被肆意地践踏也丝毫没有唤醒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姑爸从头至尾都是沉睡着的,她一辈子活在自己替自己营造的安全小岛上,活在自己的牢笼里,这样的姑爸是悲哀的,悲哀到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悲剧,姑爸成为了悲剧时代下畸形的缩影。
三
“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里,所有的女性似乎都难以逃脱失败者的角色;男权社会的蛛网不会因女性的无畏和热忱而灰飞烟灭,它依然顽固地弥散在女性生命之途的每个角落,随时都可能将她们堕入万劫不复的苦难轮回”。[14]庄家上两代女性命运似乎都在这样一个轮回里不停地画着圈,女性性别带来的挫败感和流离感将这些苦难的女人牢牢地困住。面对牢固而强大的、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她们凭借自己微薄的自以为是的力量试图逃脱已经设定好的性别角色成为妄想,而盲目挣扎的举动带来的是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变质,正常的心理也在压抑中非正常化。这群苦难的女人在命运的嘲讽和捉弄中遍体鳞伤。
反观眉眉本身,上两代女性的悲惨境遇深深地烙印在眉眉的心底,在眉眉的心里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是狂乱的岁月和婆婆的巨大阴影的化合物。在创伤中长大的眉眉,看似成功的事业和家庭背后,还是抹上了一抹悲剧的色彩,与叶北龙的爱情注定毫无结果,与丈夫的婚姻也平淡得缺少激情和爱。在眉眉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她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作品中标有“5”的六个章节是眉眉对自我内心的剖析和修正,这是新时代下女性主体意识的砰然觉醒,女性主体意识的种子已经在眉眉的心底播种。在沉痛的代价之后是清醒的道路,眉眉总结前两代女性悲剧的缘由,避免悲剧的重复上演。眉眉成长过程中的渐变似乎就是在告示着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明朗化,从年幼到成熟的每一步,眉眉学会关注和重视女性的自身价值,她勇敢地直面女性真实而又丑陋的灵魂,她专注且理性地思考女性的主体地位,女性主体意识在眉眉的身体里生长并茁壮起来。眉眉在对上两代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思索的同时,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在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探寻女性主体意识的轨迹,这是新时代下女性的全新征程和阶梯式进步。
时代在进步,女性自我意识解放势不可挡。女性必须充分了解自身的缺点和认识自己的本质,挖掘自己内在的潜质并获得更高层面的自我觉醒,用女性自身的阳光驱散男性意识形态文化的巨大阴影,在灰暗中找到自我生命和存在价值,从而抛开自身对男人的奴性和依附性思想。或许这样,女性才不会被囚禁在男权领域,而是以同等的生存姿态与男性并存于全新的时代下,获取一种精神和灵魂上的浩瀚,人格上的独立和女性的永恒,逐步走向或者走完女性自我救赎的道路。当然,女性完成自我救赎的这一过程无疑是曲折而漫长的,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摸索,有时还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或许逃避能忽视暂时的痛楚,但痛楚的积累却是新一轮的轰炸。所以与其逃避,倒不如选择勇敢面对,女性要相信自身强大的爆发力和可塑性,带着一股永不退缩的韧性去追求女性主体地位。在探寻女性主体意识的路途中,挣脱加在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以女性强有力的姿态推倒男权的樊篱,走出头顶那片阴影笼罩的天空,沿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轨迹去书写不一样的女性未来。
[1][5][6][7][9][10][11]铁凝.玫瑰门.作家出版社,2009.4,第1版:59,28,39,110,27,358,358.
[2]齐红.拒绝与诱惑——《玫瑰门》与当代女性写作的可能性.齐鲁学刊,2001,(1).
[3]朱桂林.女性命运的历史演变——简析铁凝《玫瑰门》.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5).
[4]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
[8]耿英春.《玫瑰门》女性形象探析.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5,第14卷,(1).
[12]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