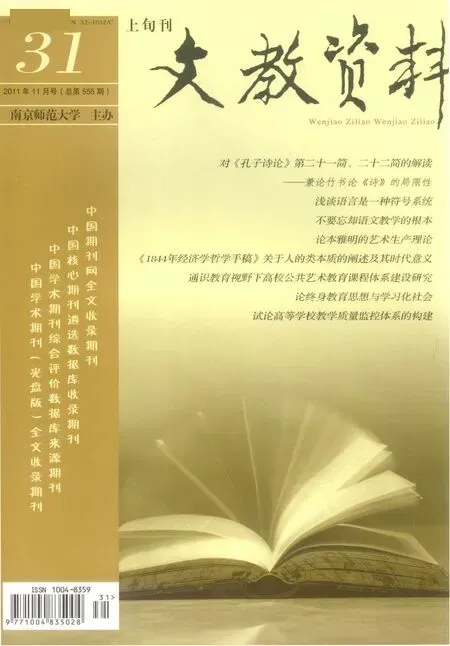晏殊婉约词书写与北宋文人文化
杨风银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寒士的悲苦有生活根源,艰辛的生存决定他们的生命意识里储存着先天的忧伤。在那些朝代更迭频繁的时代,朝不保夕,为全身远祸而焦虑,为报国无门而愤懑,为生活难以为继,如此等等都迫使他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由之产生的人生空漠感自然是深沉的、浓烈的。在北宋建国后,经历很长时间的太平岁月,加之文人的生活优裕,应该说有宋一代文人是舒服的、滋润的,可文学史现实恰好相反:北宋文人“道貌岸然”的表象之下是挥之不去的悲情意绪,在大多数文人的心底里都有一股冷气在袭着他们,尤其是高官文人。
以晏殊为例。少年时以神童招试,赐进士出身。宋仁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兼枢密使。当时名臣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和张先等均出其门。晏殊《珠玉词》凡134首,多感时伤事之作。从《珠玉词》来看,晏殊婉约词书写的愁苦悲情亦普遍而浓烈。再看其门下的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的词里那些大量存在的惆怅悲情,虽无泛滥之势,但也涓涓长流。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1]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月落红应满径。 ——张先,《天仙子》[2]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无重数,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3]
这些被延续了的悲情书写,我们不排除人生挫折感的根由,而是要寻找有没有除此之外的缘由。上面列举实例只是对这种词风书写存在的一个证明,这里还是解决比较源头性的晏殊的婉约词里的这些内容的问题。
刘攽《中山诗话》谓:“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4]论起与南唐宰相冯延巳的词风渊源,应该是不难的:同为高官,位及宰相,生活优裕,仕途宏达,都写怅然若失、无由解脱的愁苦之情,都不失富贵气。论起时代条件,可谓优越,人生又无大挫折,词作里的那种感时伤事悲情书写源泉在哪里呢?冯延巳的南唐和晏殊时代的真宗、仁宗两朝比起来,真可谓天上人间。晏殊的时代在北宋开国后的“太平日久”的时期,这是冯延巳所没有的历史境遇。
我们不妨先看文学史的结论。
第一种解释儒家的 “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心忧天下”的风范为他们所崇尚。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加之,宋代的国势已远不如盛唐,开国之初,北方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在辽人的统治下,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驩州一带已属越李朝的版图;被辽和西夏两强敌威胁,文人治兵的制度使得宋代的军事孱弱。惧内强烈,战事败多胜少,对外的巨额岁币和对内的冗官冗费,内忧外患的现实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第二种解释就是宋代对佛教的保护和鼓励政策。[5]佛家的出世思想和对彼岸世界的关注,这对中国文人是个提醒:从充实现实人生转而开始关注后世,这本是个古老的话题,可没有像佛家那样认真严肃地理性思考过。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在儒家那里是回避死亡话题的,死是被搁置了起来的一个思考命题,尽管可能很有价值,并且直接面对每一个生人。而佛家的重新出场会直接地唤起北宋文人的这种“空观”意识,人生里的那些往日镜像带上伤感的色调与心底的那种人生空漠的悲情意绪在这个层面讲应该是合理的存在。
我们要是细心思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不是少了一个反面,如果辩证地看,决定事物存在的可能性因素都该不止上述几点的。一味地从悲苦的角度思考悲苦,这种思维惯性是不是让我们忽略了什么?比如,人生大致通达、身居高位、一生亨通,生活的时代又是太平盛世,那么这些因素有没有对这些人物的心底的悲情意绪产生过影响?
有人认为,晏殊在富贵气下的怅惘之根源,是宗法伦理在文人性格构成中有先天规定性的压抑性存在,是抒情主体的思想体系和个人人格的一种裂变,由之形成的一种处理美的冲突的思想方法。[6]也有人提出说,一部《珠玉词》,既是晏殊对人生、生命进行思考、探求的心路历程的艺术再现,又是人类面临生死问题时的焦虑挣扎的真实记录。[7]这样的界定是粗放的、暴力的、不说明根由的。一个时代的某种情绪不能简单地在一个时代的作品里找缘由。说晏殊生性敏感,有比常人更深重的时间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个不是结论的结论,也是个定论,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诗人。要说身居高位的晏殊的理性呢?这样的前提下,只能在“诗余”的词里表达更方便和随意,这不更能说明问题吗?一个时代的繁华难道只供物质的丰腴而不对一个时代诗人的心灵产生影响,连潜移默化的、隐性的都没有?这是个大问号。
讲到宋代文人性格的形成与构成,都得谈到儒释道的融合对其的影响性构成,都得讲到孔孟思想对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结构的先天性影响。有宋一代的繁华,从物质和娱乐角度客观地讲,一点不比盛唐逊色。宋初百余年,国内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8]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对当时的生活盛况有详细的记载,城池规模、市井分化、节日宴游、杂耍、婚丧嫁娶等都在列:“灯霄月夕,雪季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9]这样繁华的都市,提供的生活的丰富程度是不难想象的,创造的娱乐空间和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享乐之风的盛行除却了皇帝的提倡之外,这样富足的环境自身也能孕育出。“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0]在娱乐中度过悠闲的日子该是那些都市人的基本生活方面。而宋代文人的消费能力和参与娱乐的热情根本就不用怀疑。再就“词”这一文学体式本身而言,其为“艳科”或“诗庄词媚”的先天规约,就与娱乐有着不可断绝的因缘。
这里我们该珍视一个简单的现象:商业时代的更迭速度。商业时代的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太快。城市的繁荣和娱乐业的兴盛,普遍的不受重伤的悲欢离合是频繁的。人口的剧增、流动也是必然的。从人的心理上,在大都市里,生人最多,熟人最少。这是个基本事实。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那种陌生感的激化和加强是预定的。“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晏殊,《拂霓裳》),在人际交往上是这样,熟悉的一转身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面对离别,“美酒一杯留客宴,拈花摘叶情无限。争奈世人多聚散,频祝愿,如花似叶常相见”(晏殊,《渔家傲》),只能以此安慰自己。在这样的时代里,因之而生的这样一种涌动的底层情绪逻辑上说是普遍的。
繁荣的城市经济生活和丰富的娱乐生活,这是北宋晏殊时代的基本日常。当然,繁荣的城市经济生活应该是丰富娱乐生活的一个前提。本文在这里试图分析娱乐作为北宋文人工作之外的基本生存内容,找寻一种时代生活语境对时代人物的心理影响。这既是个外因的考察,又是从心灵内部进行探寻。
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揭示了娱乐的一种影响规律: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结束了都带有“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式的邀请。所有刚才的一切在上演中都被不当真了对待,[11]所有一切都被当成一种事来对待,而不再成为一种必然的担当,这是娱乐时代给人的最大的影响,应该说,“拿别人说事”成为娱乐时代人的一种生活惯性,一种不自觉。而对北宋那些高官文人来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么?他们不会像普通人一样,在勾栏瓦肆里流连而忘返?他们对一个时代的不断变化是不会没觉察和感知的,尤其是作为父母官,这样的眼光和关注是少不了的,也是其职业修为内定的。这是常理。晏殊的“闲愁”“清泪”的自然书写就很恰当地印证了这样一种时代人的心理特征。那样的婉约书写是轻描淡写的,不伤及肺腑的,但也是绵长的。叶嘉莹在《大晏词的欣赏》提出“理性诗人”一说,解释晏殊词“情中有思”之特色,分析晏殊作为“成功型”诗人一类是为其根源。[12]这一外围的解说很有价值:成功词人的婉约词书写中理性因素的加入,凸显了晏殊词的个性与不同,同时开辟了从反面思考的新途径。
这个逻辑上,我们再回来看,晏殊作为高官文人的心底的那些悲情忧伤的基因,在变化面前,在涌动的陌生潮流里,沉淀在心底的还能藏得住么?所以晏殊会在《浣溪沙》里自然地吟出“小园香径独徘徊”的忧伤。那是一种面对变化的时代带来的陌生随之涌起的孤独,一位不会伤及心脏的,无大碍的,可以感染人的,继承了前辈文人传统的“哀而不伤”忧伤的雅致。这是我们诗歌传统里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它在晏殊的时代里有了晏殊独有的个人特色,也是被延续着的一种诗歌命脉。
北宋晏殊时代的娱乐文化为文人增加了一条舒展的渠道,为宋代文人的情感的正常抒发提供了真实的可能。也是北宋浓厚的娱乐氛围造就了晏殊婉约词的特质。它与文人遗传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佛学对死亡的激发等一同铸就了有宋一代在晏殊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铸就了晏殊独特而不俗的婉约词书写。
[1]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
[2]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
[3]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
[4]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 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M].北京:高教出版社,1999:6-7.
[6]孟楠.小园香径独徘徊——论晏殊词作中富贵气下的惆怅之情[J].文教资料,2007,7,(21).
[7]田干生.人类灵魂的焦虑与挣扎——论晏殊《珠玉词》的生命意识[J].江淮论坛,2002,(5).
[8]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9][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1,序.
[1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1.
[11][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吴艳莛译.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7.
[12]叶嘉莹.嘉陵论词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