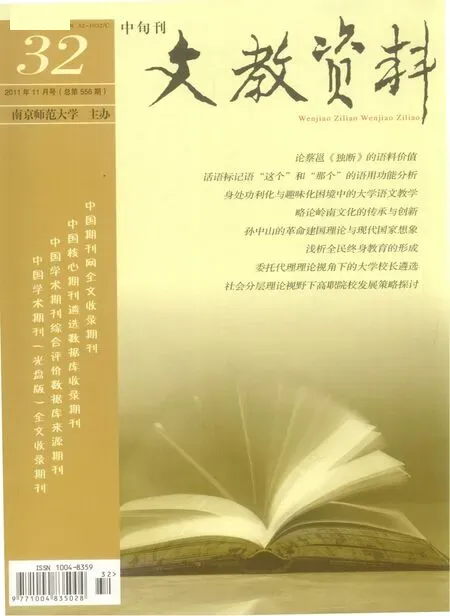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印记、姓名和身份
冯 英
(咸宁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0)
一、前言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小说情节支离破碎,时间和空间并置,多角度的叙事风格,以及人物形象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等都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碎片化的拼图式不仅运用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作家同样也用百纳被的方式来拼接人物形象,从而体现人物身份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莫里森通过人物的名字和他们身上的印记等诸多属性来拼接人物的身份。在莫里森小说中人物身上的印记和名字都有某一特征,而这一特征又与黑人民族、文化相连,使得黑人身份的构建成为一个关联概念,而不是孤立的个体自我价值的构建。
二、印记
秀拉是同名小说《秀拉》中的主人翁。在莫里森笔下秀拉是第一位要过实验性生活的黑人女性。她从儿时起就发誓要成为自己,在自己的姐妹内儿也走进了其他黑人女性生活模式后,她毅然离开家乡。经历了十年的游学,秀拉依然没有找到自己所要的身份。她回到故乡,在自己的社区掀起反叛的波澜。莫里森讲述秀拉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她的内心是矛盾的,她的行为是离经叛道的,她的性格是多元性的。秀拉的外表就体现了她的与众不同,而她的这些形象并不是作家告知读者,而是作家透过不同人的视角来感知人物的个性。秀拉的左眼睑到眉间有块暗色的胎记。她的胎记在社区不同的人看来有着不同的印象:在夏德拉克看来那是小蝌蚪;在好友内儿看来是一枝带刺的玫瑰;在裘德看来是响尾蛇;在社区的人看来是秀拉母亲的一小撮骨灰。[1]这样多样的理解是秀拉多元性格的体现。正如麦克道尔所言,秀拉的胎记是她多样性自我的暗喻。秀拉的胎记是她多样性自我的象征。[2]
《所罗门之歌》里的彼拉多是自主、自信与智慧的一个角色。在莫里森笔下她的身体特征同样与众不同:首先她在母亲死去后才自己爬出来,生下来就没有肚脐眼。因此她被视为不祥之物而被社区排斥。她索性丢掉她学得的任何一种假想,从头开始。然后花力气弄通她为什么要活,什么对她来说是有价值的问题。“我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悲伤,区别何在?活下去我需要知道些什么?世上的真实是何物?”[3]P149没有肚脐眼成了彼拉多莫里森笔下的万物之母。
莫里森用印记、标志甚至烙印给笔下人物贴上不同的标签。秀拉的胎记,彼拉多的无肚脐眼,波琳的跛足,伊娃的断腿,塞丝乳房下的曼陀罗,森的长发绺,等等,这些残缺的身体标志并不是莫里森用来区分黑人个体,而是用来象征黑人民族的整体身份。正如塞丝的母亲告诉她的一样:“如果我发生什么事,你不能从我的脸上认识我,但你可以从我的印记上来认识我。”[4]P61这些标记是象形文字,象征着黑人民族,因为黑本身就是一种印记,是黑人文化的暗喻。[5]P39这些印记标志着黑人是奴隶制的牺牲品,是对他们极端生存环境的诉说。这些印记既标志着他们身体上的残缺,诉说着他们心理上的残缺,更暗喻着他们自我身份的残缺。
三、姓名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哈利《根》的问世,掀起了黑人寻根的热潮。而寻根首先冲击的是对黑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寻找,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寻找。与身份相连是人的名字。莫里森曾说:“如果你来自非洲,你的名字就消失了。问题是不仅仅你的名字消失了,你的家族、你的部落的名字都消失了。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名字,你死后,如何与你的祖先相连?这是黑人民族巨大的心灵创伤。”[5]P40《最蓝的眼睛》里完全接受白人文化的切丘无法挥去心中的疏离感,他意识到黑人放弃本民族文化,追逐强势文化而引起的价值错位和迷失。他在写给上帝的信中无助地追问:“你叫什么名字?叫你摩西?你会说我就是我,你担心他们知道你的名字而认识你,从而不再怕你了吗?”[6]P12莫里森字里行间显示出:名字是身份的象征。
在奴隶制社会中,黑人女性只是生育的工具。她们所生的孩子大多没有姓氏,因为黑人女性的孩子可能是几个男人的,她们无法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或者她们随时被卖掉。黑人孩子无从知道自己的家族姓氏。《宠儿》中的塞丝是幸运的。她的母亲被白人强暴生下几个孩子,都被扔进海里。因为她知道塞丝的父亲是黑人而给她取名并留下来抚养,所以塞丝拥有名字是对黑人生命的认可,代表了黑人的属性和文化,是与黑人相关的身份的标志。根据《圣经》故事,塞丝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孩子。他的降临体现了上帝的宽容与爱。而莫里森加字母e在男性名字后为人物取名,凸显了爱之化身的塞丝在奴隶制下爱的扭曲和对奴隶制的反抗。
《所罗门之歌》里的彼拉多的名字是她不识字的父亲随手翻开《圣经》而选择的一个名字。在《圣经》里彼拉多是对抗上帝的人物。在小说里,彼拉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耳坠里,并要求侄儿奶人也这么做:“你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你就必须牢记它,因为如果你不用笔写下并记住,你死了,它也就跟着消亡了。 ”[3]P333在彼拉多看来,她的名字连着家族、连着传统、连着历史,记住名字就是记住自己的根。肉体死亡后名字是自己身份的重要载体。奶人牢记姑姑对名字的理解,在地名、人名的指引下找到了自己种族的身份,具有黑人祖先飞翔的能力,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构建。
姓名是符号,是家族的传承和血缘关系,具有个人、家族和社会价值,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7]莫里森小说里的姓名指向黑人种族的身份。柏油娃里森(Son)的寓意就是儿子的意思。森讨厌北方城市的生活,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他有一种疏离感。他对白人文化持排斥的态度,他整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是黑色的味道。一回到故乡,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漂亮。森是被白人文化抛弃了的黑人文化的守望者,他是非洲裔黑人的“儿子”。
在 《柏油娃》中莫里森给所有的人物都取了两个名字。森对岛主瓦莱里安自称威廉·格林,而对雅丹则是森·格林。雅丹于自己的叔叔婶婶则是雅丹,而于斯特里特先生则是杰德。瓦莱里安是骑士岛的主人,瓦莱里安这个名字取自于古罗马的一个皇帝名字。骑士岛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包括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玛格丽特·斯特里特,一个是玛格丽特·勒诺。玛格丽特出身贫寒,因为美貌而嫁给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瓦莱里特,但她和岛上其他人一样没有话语权。由于瓦莱里特的独裁,她的天性被扭曲——偷偷用针扎自己的孩子。勒诺这个私下的名字正是她美丽外表下玛格丽特个性的体现。莫里森给予小说人物两个名字旨在暗喻人物的分裂的自我。森无法融入白人生活的北方城市,只有在自己的故乡埃罗他才自在;雅丹是黑人文化的孤儿,迷失在白人文化价值观里。莫里森通过人物名字的描述来表现在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青年男女在自我身份构建过程的矛盾与挣扎。
如果说在《柏油娃》里莫里森给人物取两个名字是为了说明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下的人格分裂的话,那么在《最蓝的眼睛》里波琳改名则是对自己种族和文化的抛弃。波琳和丈夫来到北方城市,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她开始厌恶黑色,把黑当成丑的东西。出于对白人文化的崇拜,为了讨好主人,她不惜缩短自己的名字,在干活的白人家里她自称波莉(Polly)。波琳的改名在莫里森看来就是对自我的放弃,对黑人属性和文化的放弃。
命名在莫里森小说中是一种自我主体性的体现,也是一种权利的象征。《秀拉》里的伊娃是莫里森笔下代表男权观的女性人物。伊娃用一条腿换来的钱养活一家人,同时还收养了三个流浪儿。三个男孩年龄、长相都不同,而且之前各有名字,但伊娃给他们三个都取名为杜威:“何必把他们分开?甚至名字的首字母都不大写,都成了露水儿(dewey)。 ”[1]三个男孩成了三位一体:“他们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脑子思考,保持着一种令人恼火的不受侵扰的自由。”[8]P39在丈夫离开后,伊娃带着恨在生活,她用恨来定义自己,界定自我,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她的不安全感让她学会要拥有权利,去控制别人。授予一个人名字,规范他而且控制他是一个人权利的象征。[5]P44这也是伊娃从白人那里,从男性那里习得的经验。
四、结语
非洲裔美国黑人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奴隶制压迫,他们身体上、心灵上的创伤无法忘记也难以诉说。废除有形枷锁后无形枷锁的压迫使得黑人民族文化和身份的重建步履维艰。而这些难以诉说的心理疤痕在莫里森笔下映射到人物身上印记、姓名,以及诸多能代表黑人文化属性的东西上去。莫里森把黑人寻找自我、求证自我身份的过程通过黑人身上的印记、黑人的名字等来反映他们人格的分裂,身份的塑造,以及民族意识的觉悟。印记、名字等代表黑人特性的碎片构成黑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代表着黑人历史、文化和集体意识。每个黑人个体自我的构建都和黑人民族身份的重建不可分离。这种自我是一种关系概念,是关系到整个黑人而不单单是单个个体。在莫里森关于黑人身份重建的思考中,这种关联自我旨在说明黑人个体身份的构建需要黑人间强大的纽带和黑人种族身份的重建。[5]P45
[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McDowell,Deborah E.The self and the Other:Reading Toni Morrison’Sula and the Black Female Text.In CriticalEssaysonToniMorrison,ed.Boston:G.K.Hall,1988.
[3]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Morrison,Toni.Beloved[M].NewYork:Knop,1987.
[5]Barbara H Rigney,The Voice of Toni Morrison.Ohio StateUniverstyPress,1991.
[6]Morrison,Toni.The Bluest Eye.New York:WasingtonSquarePress,1970.
[7]潘惠霞.解读《宠儿》中黑人姓名的隐喻意义.外语教学,2007,(3).
[8]托尼·莫里森著.胡允桓译.秀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