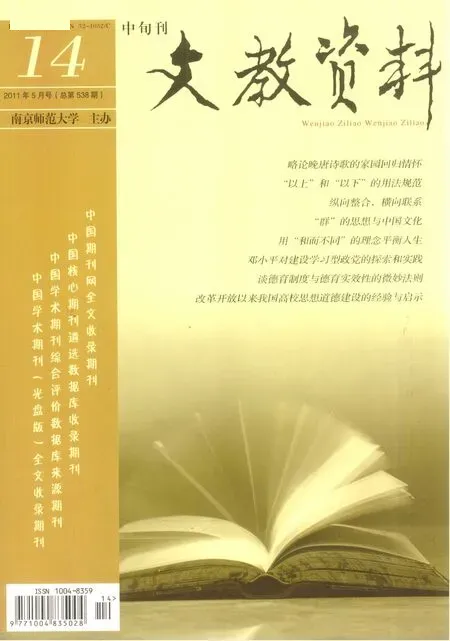“群”的思想与中国文化
陈曦 胡碟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尾 516600)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群”的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对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的品行要求,历经数千年,至今仍被人们所恪守。与“天”、“仁”、“礼”、“诚”等其它传统思想一样,“群”的思想从先秦诸子时期起,就已牢牢地占据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层,并向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辐射、延伸。
一、释“群”
《说文解字》释“群”谓:“辈也,从羊君声。 ”“群”的本义是指羊群、兽群。《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礼记·月令》:“玄鸟归,群鸟养羞。”由此而引申出人群、族群等意义。《礼记·檀弓》:“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由此又引申为动词“合群”、“乐群”。 《荀子·非十二子》:“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礼记·学记》:“三年视敬业乐群。”孔颖达疏:“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在这里,“群”字意指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其实,“群”所包含的这种朴素的伦理要求,是先民时代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与自然斗争的结果。《荀子·王制》云:“(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个体的自我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古人清楚地知道,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能群,只有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合作,才能使自己成为万物的主宰。
二、“群”的思想在哲学上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互辩,为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提供了享用不尽的思想源泉。然而,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礼崩乐溃的大时代,如何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生存下去,如何重建一种和乐友善的社会秩序,这是古代思想家们无法逃避的历史问题。因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从其产生伊始就有着强烈的世俗关怀,与对现世伦理秩序的关注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群”的思想也不例外,它也带有浓厚的人伦色彩。
如前所述,“群”的思想包含着人们对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的美好追求。古人理想中的“群”应当是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下和悦、相亲互爱的人群、族群。不难看出,“群”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中“仁”的思想是相契合的。《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仁的本义是人的复数,即人们、人群之意,从词源上言,“群”与“仁”是相通的,只是人之众谓之“仁”,兽之众谓之“群”。“仁”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论语·颜渊》说仁者“爱人”,《礼记·经解》曰:“上下相亲,之谓仁。”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看作为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并以此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汉书·刑法志》云:“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可见,“能群”的前提正是“仁爱”,而其目的则是通过“胜物”来实现“养足”,即人的生存发展。
个体的人离开了群体是无法独自生存的,群体的意义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体的生存,实现个体的价值。如何处理“群”与“己”的关系,也是中国哲学一直试图解答的问题。关于群己之辩,中国哲学总体倾向上是重群轻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对个体价值缺乏重视,只是对个体的关怀最终是以对群体秩序的关怀为目标的。孔子的群己观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对于“己”,孔子强调要以“仁”为行为准则。《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要求人的社会行为必须遵循“仁”的道德规范,把“仁”内化为一种人生的审美态度。对于“群”,孔子则突出“礼”的重要性,要求建立一种群而有分、上下有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的秩序是每一个社会群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因此,孔子把“仁”和“礼”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把是否遵循“礼”作为判断“仁”的标准。 应当说,“孔子的‘仁’和‘礼’,代表了他对群己关系的基本思考:前者着眼于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后者着眼于外在的群体秩序,二者结合起来,就是理想的‘群己和谐’”。然而,当自我与群体发生矛盾、产生冲突时,个体就必须通过“克己”来“复礼”,维护群体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综观孔子的群己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仍然是:把“群”的价值抽象化、神圣化为一种先验的社会生活秩序,对个体的价值则采取克制、泯灭的态度。《论语·子罕》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熹注曰:“绝,无之尽者。 毋,《史记》作‘无’是也。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一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始终,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四书章句集注》)这种“毋我”的精神状态正包涵着对人的欲望的压制。然而,这种思想倾向在孔子那里仅仅是一种思想雏形,但到了宋明新儒家那里,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群本位原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使群己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相互对立状态。
三、“群”的思想与古典文论
“群”的思想对古典文论的最大影响要数“诗可以群”命题的提出。“诗可以群”一语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关于《诗经》的批评(“兴观群怨”说)中的子命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虽然郭绍虞先生怀疑“兴观群怨”观点“早已存在于《诗三百篇》中”,“不一定是孔丘创造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兴观群怨”说在孔子诗论中的核心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古人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孔安国把“群”解释为“群居相切磋”(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朱熹却说“和而不流”(《四书章句集注》)。由以上两种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前者侧重于诗的交际性和参与性,强调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后者则偏重于对社群成员的意识观念、精神修养的塑造。尽管如此,儒家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即强调诗歌的团结教育作用。所以,“‘诗可以群’反映出儒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某种需求,也就是通过文学艺术而达到上下和悦、互相仁爱、协作团结的特殊作用,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即真诚互爱的仁爱精神在美学上的反映和要求”。
自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这一命题之后,历代学者对此加以讨论,绵延了数千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以诠义之开拓、运用之广泛而言,当首推船山。此一概念于船山诗学意义之重大,亦非比寻常”。方孝岳先生说,王夫之论诗“一切拿‘兴观群怨’那四个字为主眼”。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开篇就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并在《诗译》中再次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见,强调诗歌的“兴观群怨”正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那么,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论又有何独特之处呢?我们先不妨来看看他对孔子“兴观群怨”的注解:
《诗》之泳游以体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其相新以柔也,迩之事父者道在也;其相协以肃也,远之事君者道在也。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以“情”为核心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情是“兴观群怨”的内在基础,而“兴观群怨”则是情的外在表现,彼此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把诗教和性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调和互补,这正是船山诗论的创新之处,同时也反映了处在古典文论总结期的清代文论的时代特点。在对“兴观群怨”的创造性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群”和“怨”的理解。显然,王夫之是把“群”和“怨”当作一组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来阐发的。“出其情以相示”强调的是诗人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含其情以不尽于言”强调的是诗人情感的郁愤与寓寄,不同的情感表现联系着不同的社会作用。王夫之从诗歌的情感表现方式而非思想内容着眼来解释诗歌何以能“群”、“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路上的创新。另外,在对“群”和“怨”的把握尺度上,王夫之也有所强调。他指出:“可以群者,非狎笑也;可以怨者,非诅咒也。不知此者,直不可以语诗。”他评价《古诗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着”。不难发现,对于“群怨”,他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突出一个“宜”字,也就是要“温柔敦厚”。
总之,在古典文化中,“群”的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结构自足的文化概念。但是到了近代,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变革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外在刺激的作用下,“群”的思想在许多层面上产生了新的异质,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1]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2.
[2]刘晓虹.从群体原则到整体主义——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群己观探析.文史哲,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