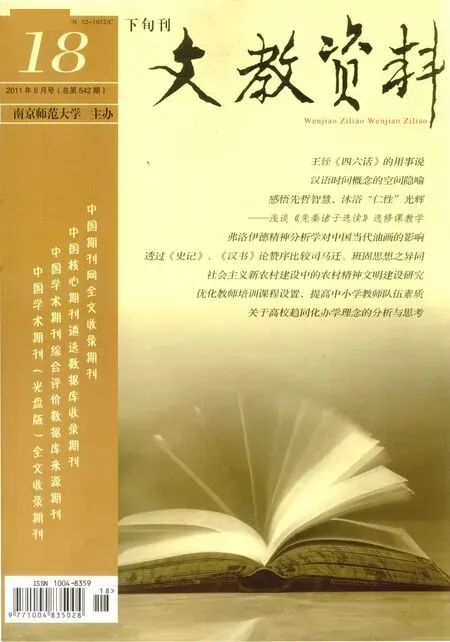论新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的原因
王永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的刺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商业各方的策划运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再次出现一个创作高潮,特别是随着同名影视剧的改编、红火,更加促进了这一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代表性作品有《我是太阳》、《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八月桂花遍地开》等,跟“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较而言,这一类型的小说同样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革命历史进行再书写,同样认同革命历史的必然进程,但是由于时代政治文化语境和作家主体的原因,这一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呈现出跟“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被一些研究者称为 “新革命历史小说”。[1]新革命历史小说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新时代的因袭与变异的结果,它既有革命历史小说的某些因子,又有新的时代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特质。在世纪之交,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一度出现热潮,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文化心态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建国以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非常重视文艺创作的政治功能,因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和作家主体主动迎合之下出现了一系列“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2]的具有浓烈意识形态味道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历史小说,诸如 《林海雪原》、《创业史》、《红日》、《红旗谱》、《红岩》等一系列所谓“红色经典”的作品。不论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无不散发着浓浓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味道,文学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和御用工具。1978年以后国家工作的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结束了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干预也有所松弛,但是这种松弛只是相对的。当文艺创作触及到主流意识形态所不提倡的领域时便会遭到一系列的干预措施,甚至是以政治手段直接介入方式的进行干预,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主流意识形态更加重视文学创作的宣传性和舆论性,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所涌现的英烈的颂扬和对他们的忘我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的讴歌。
无论是在江泽民时代还是在胡锦涛时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文艺的政治宣传功用,“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4]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李长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中明确提出文艺要讴歌英雄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以用来激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和奖励措施来引导作家的创作。
在作家作品的审定和出版上,作家的创作不得触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得涉及具有政治敏锐性的领域,否则出版发行状况便会受到影响,“商业化的文学、艺术创作者若想取得商业成功……它不能违反 ‘主旋律’的意识形态前提、预设,否则其创作、发行等环节将面对各种‘不安全因素’和不确定性,影响到其商业性的实现。”[6]不仅如此,国家对宣扬革命精神的作品给予一定的奖励,例如1990年中央多部门联合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审查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发行。同时还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奖励措施来奖励诸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 “主旋律”作品的创作,这些奖项本身又是体制评价新闻出版机构的重要依据,因而新闻出版单位极力策划和改进“主旋律”文学的创作,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为“主旋律”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成为出版机构策划的重点。在这些作品出版之后,主流意识形态还动用各方力量对这些作品宣传报道、组织研讨会等,扩大其影响力。在这些政策和奖励措施的激励下便出现了一系列获奖作品,包括《我是太阳》、《走出硝烟的女神》这两部“新革命历史小说”。其中《我是太阳》获得了多项大奖: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全国十佳长篇小说奖、屈原文学奖;入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国五十周年五十项献礼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十部献礼长篇小说嘉奖、武汉市“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武汉市文艺基金特别奖、首届湖北文学奖荣誉奖、首届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荣誉奖。《我是太阳》诸多奖项的获得是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历史才小说创作释放的一个重大信号,也是对其他作家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激励和引导。
二、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文学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喜欢与习惯于视觉刺激,这一时期影视艺术迅速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新革命历史小说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世纪之交的因袭与整合,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商充分利用了影视艺术这一市场消费的潮流。作品能否出版,出版后能否拥有大量的读者,销售量问题是作家不得不考虑的,作家的创作能否被影视传媒集团购买也是作家考虑的因素之一。因为借助于影视艺术才能实现作家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还是《亮剑》,无一不是在影视艺术的带动之下,发行量剧增,作家名声大噪。在市场化的今天,只要不违反有关法规的情况,作家也是要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军歌嘹亮》的作者石钟山说:“以前,作家往往都是埋头码字儿,几乎不关心市场化问题,但是现在文人谈钱谈市场就庸俗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7]因此从作家主体来看,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畅销,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支持,实现名利双收的目的,就不得不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不得不取悦于读者,为此新革命历史小说家采取了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处理方式,而是根据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与臆想来完成革命英雄人物的叙说,消解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身上的神圣光环,于是便有了姜大牙、李云龙等一个个活生生的作为“人”而非“神”的英雄人物。这些都是作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新革命历史小有着不同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审美特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出版事业也被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出版商的重要目标。因此出版商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不得不考虑一本书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能否成为畅销书。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出版商往往会使用多种手段策划和包装图书。封皮的视觉效应和夸大其词的点评甚至于书的名字都是出版商进行炒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历史的天空》在出版的时候曾经经过几个编审的手,作者徐贵祥根据要求作了相应的变动,书的名字没有改动曾一度是编辑担心销路的重要原因。[8]《我是太阳》版权一方状告《激情燃烧的岁月》抄袭侵权,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版权的相争,倒不如说是经济利益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畅销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菲,因而出版商热衷于出版这类作品。
同样,影视媒体作为一种商业机构,善于发现与捕捉人们的喜好心理,把一些能够迎合观众品味作品搬上荧屏,当然,作为商业媒体,他们考虑的自然是收视率,只有高的收视率才能实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有着国家和政府最强大后盾的中央电视台节目每年都会根据收视率进行评审改编,更何况作为商人的影视制作商了,“由于电视制作的投入很大,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被引进,电视的产业化也必然与商业化成为合谋,即使是传统的国家电视台、公共电视网也不得不考虑它们的商业回报和观众收视率的实际情况”。[9]制作商认识到,在当代怀旧版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书写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因而他们选择了这一领域,进行发掘,使得《亮剑》等创下一个个收视纪录,也带动了文学作品的再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更多的作家创作新革命历史小说。
三、大众文化心理的促使
中国曾经有着漫长的红色生活,革命历史拥有固定的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革命英雄人物成为激励几代人奋不顾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这些在给人民带来精神的“圣洁”的同时带来的还有审美的疲劳。所以当市场经济降临的时候,原有的信仰基础和红色秩序被商业经济大潮冲垮,人们挣脱了“红色束缚”,尽情地沉浸在物质享受里,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再度回首,蓦然发现精神生活的空虚与生命的困惑。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人们为了生存下去,逐渐磨掉了性格的棱角,甚至于有些“犬儒主义”,曾经的生活尽管物质贫乏,但是却很有激情也很快乐,于是人们开始怀念那些革命英雄人物,他们的激情和强旺的生命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在这个年代,我日益感到父亲身上所拥有的东西,比如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像生命一样珍贵的荣誉感、坚强的信念,一辈子都不动摇的信仰,等等,对我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他们比我们坚硬得多,至今还顽强地坚持着他们的信念,这种精神让我钦佩,现在这种人已经越来越少了”。[10]因此也可以说对今天人们生活的不满的一种发泄是新革命历史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经历了红色经典的人们对于以往的风格早已产生审美疲劳,再加上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的革命历史观念的反叛,人们需要的是不同于以往的那种“高大全”式的的英雄人物,而是作为普通凡人的英雄人物,于是便有了新革命历史小说中不同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
怀旧情绪与好奇心理也是新革命历史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由于未来的不可预测,人们通常采取的本能的应对方式是‘向后看’,即感叹现实生活的诸多不如意,暂时不去理会麻烦的未来,把安慰寄托在对已然消逝的黄金岁月的怀想之中”。[11]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甚至于腐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怀念红色时期的生活,红色时期尽管没有充裕的物质享受,人的生活却是那么快乐那么有激情,也因此红色时期成为了某些人向往的乐园,特别是那些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更加怀念那个时期,于是新历史小说家抓住大众的这一文化心理进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使大众重温当年的激情生活和再度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当中,因而必然会得到他们的热烈回应。年老一代对红色生活时期主要是回忆,而年轻一代主要是对革命历史好奇。在以往的历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年轻一代被灌输的是传统的革命历史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人们不再满足于既有的革命历史观,对革命历史充满了好奇、猜测和臆想,当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对革命历史的种种猜测,革命英雄人物形象不再是“神”,而是变成了“人”;革命历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诸多偶然性、阴谋、错误的,这无疑正好满足了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一代的好奇心。有了年老一代怀旧情绪和年轻一代好奇心的驱使,许多作家便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在创作,于是便促进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产生与发展。
综上所述,新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出现一股创作热潮,主要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和引导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在大的环境上给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诸多便利和实惠;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消费心理特别是影视艺术的介入使得新革命历史小说迅速传播,并反过来促进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进一步繁荣;同时大众的文化心理,特别是人们因对现实不满而生的怀旧情绪和对历史的好奇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发展。
[1]邵明.“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策略[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5).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
[3]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J].中国比较文学,2003,(1).
[4]具体内容参见中国文联网站:http∶//www.cflac.org.cn/.
[5]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J].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00.
[6]李瑛.两个出版社同出.军歌嚓亮.书名相同不算侵权?[J].北京娱乐信报,2003.8.3.
[7]脚印.《历史的天空》另外的故事[J].出版广角,2006,(1).
[8]金丹元.关于电视产品的生产与观众接受[J].上海大学学报,2005,(5).
[9]邓一光,韩晓惠.关于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对话[J].当代,1997,(7).
[10]胡铁强.怀旧情结与红色经典改编[J].长沙大学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