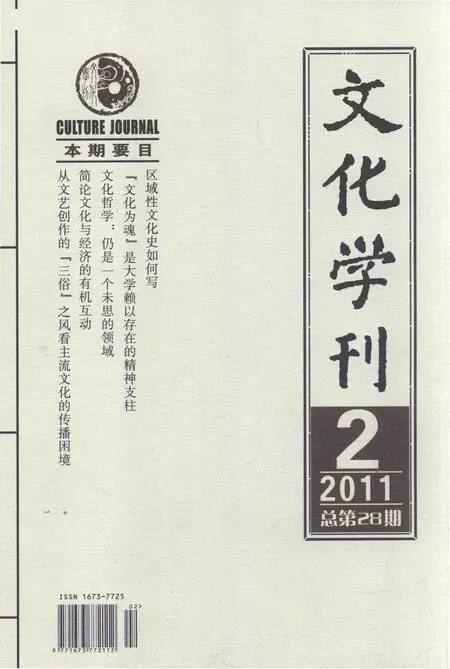云锦天机妙手裁
——《缘斋诗稿》序
王充闾
云锦天机妙手裁
——《缘斋诗稿》序
王充闾
一
李仲元先生以《缘斋诗稿》见示,余固乐其丰盈大有而先睹为快也,欣然受之。可是,先生马上补充一句,看过之后要写一点东西,弁诸卷首。听了,我不禁摇首咋舌,心想:这可是个力不从心的苦差使。
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其意在于为读者从茫茫书海中梳理出一些头绪,为理解与接受指引出一条路径,起到津梁与导航作用。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仲元先生腹笥丰厚,学富五车,面对他的诗集来说三道四,确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句,“碔砆”,石之似玉者,意谓元稹品评诗圣杜甫之诗未能得其真髓,下语似是而非。其实,这类指引路径的文字,最好还是由作者本人去作。“甘辛谁解味?机杼自家知”。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不是说“知子莫如父”吗?尽管如此,但既承错爱,却之不恭,便只好唯唯从命了。
《缘斋诗稿》收诗近500首,均为近体,七言、五言绝句约占十之八九。按题材分类,厘为三集。一曰《辽海行吟》,地域涵盖整个东三省及部分内蒙地区,时间跨度过亿年,从形成辽西古生物化石之晚侏罗纪,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或古迹,或人物,或史乘,或风光胜览,或稽古钩沉,或轶闻逸事,具见乡邦文物之盛,搜罗撰述之勤。一百八十首七言绝句,一题一事,后面附以言简意赅的“本事”,概要地写出一部堪作标准教本的生面别开的东北地理历史,洵为开创性的胜业。二曰《题咏赠答》,三曰《胜迹游踪》,前者映现人文交往,后者藻绘江山胜概,各擅胜场,相互生发。作为知名的诗赋大家与书画艺术家、文物鉴赏与考古专家,仲元先生题咏赠答,范围极广,举凡海内文朋诗侣、艺苑名家,以及诗书画艺、学术交流,亲情忆昔,庆吊往还,都有诗作酬应。与此相联系,先生不仅万卷罗胸,而且游踪不知其几万里也,屐痕处处,遍布神州。临风纵目,兴会淋漓,一一发而为诗。如果说,“行吟”组诗重在咏史,着意于缅怀古迹;那么,“游踪”与“赠答”则以情怀、理蕴取胜。三卷相生互补,汇成一部泱泱乎、沨沨乎的五声和乐。
二
仲元先生为著名学者,多年从事考古文物工作,沉酣典籍,出经入史。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此类诗后面大多加注,或为题解,或为纪事,实际上起到“本事”作用。所谓“本事”,亦即以事诠诗,通过标举故实以求诠释诗之本意。这种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诗史融合、诗史互证的手法,不仅有助于彰显作者的题诗本旨,而且,同史籍一样,可以发挥“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鉴戒作用。
用事、使事问题,作诗、读诗中可以经常碰到。宋代学者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指出:“诗人岂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则反为事所使。”作为学人之诗,缘斋喜欢并且长于使事、用典。七绝《燕丹》:“乌头马角客秦难,一匕功亏咫尺间。饮恨长河魂不去,风涛夜夜涌狂澜。”寥寥28字中,隐含了3个典故:燕太子丹在秦为人质,求归,秦王说乌鸦头白,马首生角,方可放还;太子丹使荆轲剌秦王,咫尺之间竟未剌中;后据辽东抗秦,秦兵追逼,匿身于衍水。这3个事典,为后世人所熟知,但若将它们编到一首七绝短章中,用来表述太子丹的奇崛生涯,而且,还要敲金戛玉,意兴悠然,却迥非易事。本来,诗写性情,并不专恃数典,但因古事已经凝结成饱含意蕴的典故,早已约定俗成,作诗者不妨借彼之意,写我之情。他人数十百言未能尽意者,而一典置之,三数字即可了却;且能使其内蕴深厚,耐人寻味,所谓“胸中有书,腕底有力”。
诗家不忌“脱胎”,有时还可以参用成句。缘斋为诗,由于古代诗文烂熟于心,上下古今,充塞胸臆,名章、词汇,信手拈来,暗用、化用诗古文辞,浑然天成,一似自然流洒,毫无窒碍。七绝《博斯腾湖》“瀚海晴波无限酒,莼鲈同醉五湖秋”;《山海关》“一时行尽天涯路,风雪弥空过大关”;《古堡影视城》“分明一个荒城堡,演绎悲欢入镜来”之句,都像曾在唐诗、清诗中觌过面的,可是,真个蹑履追踪,却又捕捉不到,只能说是“神情仿佛”。
这里,还印证了另外一层理念。我一向主张,学诗必须提倡背诵,会背了,闲暇时间在心里暗诵,余韵悠悠,它有助于掌握音韵格律,学习遣词造句的技巧,特别是体会和玩味古诗的韵味和妙处。古人诗读得烂熟,深得其音节、章句、气味之妙,于不论平仄中,却有一种自然之平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适意的要求。所以,清代学者方南堂断然地说:“未有熟读唐人诗数千首而不能吟诗者,未有不读唐人诗数千首而能吟诗者。读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笔,音韵、神致,脱口便是。”
缘斋诗才气纵横,吟稿中有大量组诗,同一形式,动辄十数首、二十几首,篇篇相连,意蕴错综,分之自为一题,合之章法联贯,构成一幅完整浩大的艺术画卷,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风貌、特征。如《新疆游吟》24首,前有小序:“甲申初秋,远游新疆,领吐鲁番之民情,探阿勒泰之奇秘,越天山,穿戈壁,下伊犁,走喀什,览西域之风光,望昆仑之高耸。心胸朗阔,不亦快哉!沿途有作,以志行程。”而《名僧赞》二十首,则自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到东晋高僧慧远,一直写到清末画僧虚谷和民初的弘一,历时1890年,俨然一部概要的中国佛教史。而《题古书画》(11首)、《临池放歌》(10首)等组诗,则突出地彰显了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与学术水平。
三
诗本性情,诗贵清新。《缘斋诗稿》中最为难得的一点,是许多诗篇能够“不为理拘执”、“无理而妙”(清·贺黄公语),显现出兴会淋漓、诗情横溢的特质,使读者于“正声雅奏”之外,领略其风华蕴藉,天然逸趣。
这类的篇什主要分布在《胜迹游踪》和《题咏赠答》中。诗人旷达的心胸、丰富的艺术涵养,氤氲于山川秀美的灵气和真情灼灼的衷怀,洒脱、隽逸之清词丽句立刻油然而生,奔赴笔下。有一些是充满谐趣的,如《题冯大中双虎图》:“兴风惊落木兰花,一啸霜林冷月斜。昨夜缘斋门未键,何来双虎到吾家。”《山溪落水》:“蓦然翻作落汤鸡,幸濯清流冷水溪。剥去缠身名利索,解衣盘礴是男儿。”《阳关》:“曾扼西行天外路,残烽衰草远秋山。今朝也作他乡客,手把文书过古关。”有一些诗在深情雅致的描绘中,常常流贯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和生活哲理,如《鱼头宴》:“三尺金盘馔,肥鲢荐巨头。莫怀生死恨,嗟尔自吞钩。”《飞龙潭瀑布》:“幽涧淙淙戛玉声,龙飞千尺碧云惊。在山泉水从来净,一到人间便不清。”《鳌头峰》:“轻步悬阶向玉京,澄心云影共峥嵘。鳌头一笑高千尺,莫叹人间路不平。”诗的意蕴与理趣,或指事物的规律,或指人生的况味,人生的境界,总之,是要穿透现象,揭示社会、人生百态的本相。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对于“遮蔽”的敞开,这是诗的很高的境界。
诗缘情,最根本的要素,或曰构思的基石,是诗人的真情实感。王士禛认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一首诗要有魅力,要能吸引人,左右读者的心灵,靠的是灼灼真情,也就是唯情是依,情文双至。缘斋之诗冷静中往往放射着一种柔肠慧致的情感冲击波。有一些诗抒怀寄慨、意存针砭,如写井冈山《茨坪》的七绝:“到处楼台起玉墀,升平歌舞信由之。百年弹指风情异,只有青山似旧时。”《麦积山石窟》:“妙相庄严万品经,慈悲看似救生灵。人间恁有千般苦,佛面悠然笑未停。”看后令人想起元好问的名句:“天公醉着百不问,汝偶而偶奇而奇。”语似庸常,而实奇警。仲元先生早岁从戎,身经战阵,古稀所作尚有陆游“骏马宝刀俱未老”的豪迈之概。三首《咏马》诗中,有“金鞭一指黄尘起,卷地风惊万壑雷”;“如今老卧斜阳里,犹自神驰万仞山”之句,一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势,不妨把它看成是诗人的自况。当然,话是这样说,实际上,仲元先生并不属于“登车揽辔,澄清天下”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所谓“性情中人”,道地的学者。
四
诗学讲究才气,更看重积蓄,一如刀刃贵薄,而刀背贵厚。凡有重大成就的诗人,都须重视培植根柢、增长识力、积理养气。古人特别重视养气。韩愈有言:“气盛,则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皆宜。”苏轼说得更生动、形象一些:“气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于平地,无难一泻千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一日数变,而不自知也。盖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耳。”仲元先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学术积累,又夙喜游历,周览四海名山大川,钟灵毓秀之气浃骨沦肌、交契会悟,宜其诗赋“气盛言宜”,沛然可观也。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已为世所公认,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随意书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缘斋诗稿》的面世也有其重要价值。仲元先生幼承家学,受过严格的国学基础训练,作为久历骚坛的“斫轮老手”,其近体诗格律精严,晚节为诗,诗律尤细,堪称无懈可击。细细玩味,我们可以从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等方面,悟出许多章法、许多理路。
这里只说一点。作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古人说,五七律最争起处,贵用料峭之笔,洒然而来,突然涌出。缘斋《自编书法作品集问世》起句:“偶弄临川笔,星驰四十年。”《嵩山》:“少室嵯峨太室雄,四方岳镇尽朝宗。”《天游峰》:“峥嵘万仞莫生愁,一径通天此壮游。”都有这样的特点。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仲元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曾从沈从文先生游,后访其故居,有诗云:“一别京华三十载,我来故宅拜先生。百年世事存公论,水远山高霁月明。”一声响遏,余韵悠然。再如《曹娥江》五绝:“孝女今何在?江帆远影微。停车空伫望,细雨鹜孤飞。”以景结情,有余不尽。
仲元先生同时又是国内著名的书法家,而且精于绘事。诗、书、画三者原本就是互通的。中华文化强调整体观照,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和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追求一种物我交融、情景交融、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使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诗书一律,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而作诗、写字、绘画,用的乃是同一种性能的毛笔,所以,又有了以一颗心灵、凭一管毛锥,自由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的物质基因。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意象、性灵的体验。中国历代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两晋的陆机、王羲之,到唐代的张旭、颜真卿、柳公权,再到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和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无一不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后世若了解其书法,不可不熟读他们的诗文;而要深谙其诗文奥蕴,也往往要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这些,对于仲元先生来说,都是一体遥同,恰中肯綮的。
承命作序,谊不容辞,今兹涂抹,实愧荒芜,聊充唣引已耳。
庚寅冬月于沈水之阳
(作者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作家)
【责任编辑: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