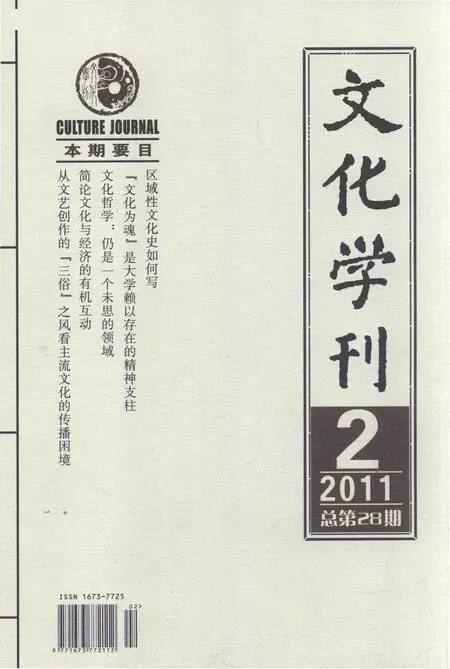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后现代文化语境
王 宁
(辽宁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辽宁 沈阳 110041)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后现代文化语境
王 宁
(辽宁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辽宁 沈阳 110041)
村上春树作为日本当下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作家之一,在后现代语境中着力探寻人的灵魂世界,引起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读者的高度共鸣。本文主要以其短篇小说为蓝本,分析其对异化状态下心灵的深度刻画及精微的文体表达,并进一步探讨村上春树的小说对当下中国小说的启示意义。
后现代文化语境;人生体验的共通性;人类心灵的虚无与缺失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
在众多的日本当代作家中,村上春树可谓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一位,三十多年来他为读者提供了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随笔谈话集、童话、文学翻译集等在内的作品六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畅销书,单单一部《挪威的森林》发行量已逾1000万册。“村上春树现象”已经跨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影响着上世纪70年代乃至当下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甚至被作为“小资”的标签,进入时尚领域。爵士乐、啤酒、意大利面,酒吧里的迷离情愫,男女间若即若离的关系,青春的失落,虚无的人生,心灵无根式的漂泊,构成了村上式的故事元素,“‘生活在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中的年轻人的世界’,倘若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上内心‘失落’的年轻人形象,简直就是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1]
村上春树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开始,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凭借个人独特的艺术造诣,获得了多项国内、国际文学大奖,在年满60岁时获得了旨在表彰作品涉及人类自由、人与社会和政治间关系的耶路撒冷文学奖,更证明了他的作品引发的世界性共鸣。从爱读书的日本关西少年,到戏剧专业的大学生兼爵士酒吧的老板,再到弃商从文的专业作家,他的人生轨迹正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全面高速发展阶段的大背景相吻合。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快速变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而全面进入消费社会,正如詹明信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2]后现代主义在文化诉求上正趋于解构“现代”:呈现了物质化、符号化、多声部化、价值的混搭,无中心化、无秩序化、众声喧哗式的形态。虽然,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相对固定的理论体系,也较难加以界定,但是后现代正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获得自身独立的地位,同时又与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角度看,可以说,后现代文学作品保留了形式革新、反讽、变形、含混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审美要素,同时又在张扬主体、培植精英文化、强调审美自律等方面挑战现代主义的信条。村上春树,正处于一个新兴时代的旋涡之中,加之大学时代还经历了1968年的“全共斗”学生运动,之后并未成为传统的“团块世代”(进入大公司服务),而是与妻子一同创业开办酒吧,在近30岁的时候突然对自己的青春岁月做以倾情记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可以认为,村上春树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与传统日本文学背离的道路,他反映了在新的文化形态下,即消费社会文化潮流下,人内心世界最真实的样态,并保持着作家特有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村上春树创作了诸如《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海边的卡夫卡》等多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以各异的艺术方式倾诉着青春一代的苦闷与失落。从洗练的都市文学,到对社会的“介入”姿态、寻求作家社会责任感的新世纪,他走过了一条不断超越自身,追求艺术更臻完美的道路,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评介资料也极为宏富。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较之长篇小说,更具有象征与隐喻意识。正如詹明信所说的“叙事是社会象征行为”,是政治无意识的体现,而村上春树恰恰以对政治貌似“不介入”的姿态完成了对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的“介入”。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和阪神大地震的关注,更证明了他作为作家对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感的深思。他的短篇小说主要集中于《再袭面包店》、《去中国的小船》、《旋转木马鏖战记》、《电视人》、《东京奇谭集》等小说集里,这些看似疏朗写意,实则具有极高艺术表现力的小说,从不同角度再现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困境,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内心的虚无、情感的缺失、精神的麻木、孤绝的挣扎。他甚至放纵想象力的羽翼营造出一系列诡异、阴森的故事,其内核蕴涵着对人与人之间地狱式冷漠的拒绝,渴求温情、理解、关爱和内心灵魂的真正自由。村上春树用生活中的“极端”(不惜夸张、变形)表达内心的“绝望”,人坠入地狱里的心灵缺失,无处遁逃,渐入绝境。村上春树为了反抗生活中的“绝望”,采取了颠覆性的文本策略,在某些精神层面上与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有相似之处,也许孤独与伟大的灵魂自有其相通之处吧。
收录在小说集《电视人》、《旋转木马鏖战记》里的短篇小说,正是对后工业社会时代病将人类身心蛀空的一个突出的展示、解剖和回应。这十几篇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现代人被生活高度挤压下人性的异化与变形,或者人自身与异化的环境所做的困兽之斗,至于孰胜孰负,村上春树并不给出直接的答案,而是将生活的本来面目合盘托出,所以说,村上春树的小说能够正视人生之困,对人生的“虚无”,主体存在的“失落”问题开掘至深。小说《电视人》正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生活的一种夸张表现,主人公一如村上春树小说中贯常的形象,在公司谋职的疲惫的中年人,家庭生活索然无味,却被突然闯入生活、无孔不入的“电视人”所搅乱,他们完全漠视“我”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存在,只是不停地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当我忍无可忍时,却已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这是典型的工业生产时代,人的本质力量被剥夺,异化为与机器人一般的物的存在,渺小又无意义。《眠》里生活安逸的中产阶层少妇,无缘由的失眠,对生活的一切渐渐顿入“虚无”,寡然无味,完全迷失了自我,尽管知道“有什么在出错”,却只能顾妄焉之,最后被困于午夜的汽车中,将要被两个神秘男人掀翻车子。这固然是心灵无处遁逃的一个恐怖的隐喻,却有着真实骇人的威力。《行尸》、《加纳克里他》里更为恐怖的情节更将这种威力演绎到了极至。饶有意味的是,一篇名为《我们时代的民间传说——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史》的小说,更构成了绝妙的反讽。一对男才女貌、情投意合、从高中时就谈恋爱的情侣,由于女孩奉行绝决的贞操观,“婚前一直是处女”而不得亲近,渐渐疏远。但女孩结婚的对象并不是这个男孩,她在结婚之后又千方百计地寻找男孩企图和他发生性爱,但是心灵的疏远和孤独已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也许,在日本这样一个性比较开放的国度,女孩的行为看似真的像“民间传说”,史前的圣处女,但是实质上是她对人生的恐惧,对人的不信任感、危机感所致,即便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因为担心分手),也不肯交付自己的一切。这个故事于波澜不惊的叙述之中体现了后现代文化中的“平淡感”,人生的“幻灭感”,即人内心最重要的东西无端失落,自我常常又虚弱得无能为力,类似的表达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俯拾皆是。
如果说村上春树的小说有超越于日本同时代其他作家之处,那么他小说的世界性目光和开放性创作心态则值得提及。面对村上春树的作品,众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他与日本传统文学的割裂,而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村上春树本人也承认他受菲茨杰拉德、卡波特、鲍奈加特三位作家影响最深,尤其是属于“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都市气息”最受村上春树喜爱。他作品中对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市文明的物质化、符号化、隐喻化的书写直接成为村上春树小说的谱系,而村上春树小说所涉及的主人公面对丰富的物质世界,内心的失落、迷惘、在战后物质富足之下的心灵创伤,无不与“迷惘的一代”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认为,村上春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用本属于极端自我的方式表达出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体验的普世生活,在观照个体生活中隐喻历史思考,在个体多声部的故事叙述中结构一种状态感,具有自我人生的指涉性,人生究竟何去何从,无法解答的题旨。
村上春树最早的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或可视作他国际化开放性创作心态的一个表达。“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旧时歌谣”。伴随着舒缓、悠扬的节奏,作者以追忆的目光打量着自己记忆之中的中国人,无论是小学里的中国老师、还是打工时认识的中国女孩、干推销员的中国同学,他们都是诚恳的、认真的,又充满了一丝丝感伤。“我”甚至有可能和那个女孩发展成恋爱关系,但是却丢失了写着她电话的火柴盒,那种无以名状的愧疚、淡淡的哀伤久久索绕在文字当中,与自我当下的心理体验找到契合。黑古一夫认为:“村上春树用‘中国’这个隐喻来表达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当然,这段引用中的‘中国’即使换作‘美国’、‘俄罗斯’也可以。”[3]作为一个读过从《史记》到《西行漫记》等许多中国书籍的部世界的关系,他常常采用碎片式的、割裂式的短篇小说构造方式,简洁的对话和情节来推进故事,或者转述他人的故事的视角,或者套用一些外国音乐的情节与小说故事营造成相似(或互不关联)的情感氛围双线索地结构文本,造成叙事上的“间离感”式的戏剧化效果。看似不经意的文体表达,实则经过了高度的艺术审美滤化过程,这就是读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为什么存在有尽而意无穷之感的缘由吧。高超的艺术技巧往往看似无技巧,他的小说往往有美国式小说的硬朗风格、多义的意旨和人,村上春树的内心是:唯我一个人能够读懂中国。他复杂微妙的情感隐含着日本对中国的反思和惭愧,亦有对历史的一种后现代式的平淡化的解构。加拿大学者哈琴提出的“后现代诗学”理论指出,后现代小说的历史不是对真实历史的回归,历史是以含混、暂时和不确定的面目出现的。村上春树式的历史正是个人生活片断感受中的历史,不再拥有现代性宏大叙事式的结构,而是片断式的、情绪化的。可见,村上春树的特殊的写作道路令他并没有囿于狭隘的国家观念、纠结于传统的思维定势,而是客观地表达出一个作家内心真实的历史感受。
如果说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在思想意蕴上表现了后现代社会人类心灵被蛀空之后的虚无感,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文体则呈现出一种在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基础上高度抽象化的、隐喻化的精微而简洁的文体表达。从村上春树小说的受欢迎程度来看,他的确拥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有着对各个阶层读者的吸引力。有研究者认为:“他注重故事的独立性,同时加强趣味性、可读性的创作方式既是对日本传统纯文学的一种挑战,也反映出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大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界限的一个特点。”[4]众所周知,日本文学有着“私小说”传统,多有凸现个人情感、内心世界的身边故事,小说主人公与作者自身的关联度往往很高,常常有着细腻的情感表现,日语本身又是一种充满了晦涩、模糊、多义的语言,因而导致了日本小说成为“象牙之塔式”的文章。而当西方迫使日本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得到高速增长之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文学也开始了相应的改观。村上春树的小说主要关注人内心世界与外贴切的比喻。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创作能够从个体内心世界出发,探索整个灵魂的未知性与丰富性,揭示了一个时代中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人性特质(主要是孤独感与存在感之间的矛盾)包括他以世界文学眼光而进行的文体实验,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得到世界文坛的瞩目。反观中国当下短篇小说创作态势,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示显得更有意义。中国当下正进入一个类似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逐步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在正在退居边缘,作为曾经先锋文体的短篇小说正在陷入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与商业化、消费化的文学出版环境相关,长篇小说的生产得到长足进展,每年三千余部的产出数量和畅销书的策划、市场码洋的份额均为可观。短篇小说,作为文学中高度艺术化的文体则沉寂得多,更多的读者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更愿意转向长篇小说、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的欣赏,短篇小说与诗歌等一同成为小众化、寂寞的文体。这当然与文学的大环境息息相关,但是作家本身的理念与实践也影响着文体的发展。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具有不可剥夺的艺术魅力,最关键是他深刻的时代感,对时代之病把握得准确,“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看似老套,实则深刻,唤醒时代病笼罩之下每一个读者的共鸣。而中国当下的许多作家(我们并不排除一些优秀者)在都全球化、消费化的语境中,进入了一种盲从的、自发式的写作,个体独特生命体验匮乏,能表现生活表象,而不能深究其里,面对浮泛的大千世界、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表现,而没有能力在精致短小的篇章内捕捉时代的本质(或是本质的一个侧面),缺乏灵光闪现,叙事能力明显暴露出相当虚弱的倾向。短篇小说既要求经验的丰富,艺术的敏感,也要求结构、语言的智性品质,甚至先锋实验的特质。小说家必须能够通过自己的文本,探查到当下社会人生、人性内部的存在细节和真相,不断地探索和寻找关于人的生命力量、悲愤的社会现实批判力量,以及由此昭示的生命与哲学的高度。村上春树在艺术上保持的先锋性和对小说文体的自觉,以及相信文学对世道人心的力量,正是值得借鉴之处。一个作家应该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生命力,不断超越自我,提升自身修养,形成开放式的胸襟与气度,担负道义与社会责任,彰显文学的力量都将是至关重要的。
[1][3][日]黑古一夫.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M].秦刚,王海蓝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05.108.
[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18.
[4]杨炳菁.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91.
【责任编辑:刘 强】
I106
A
1673-7725(2011)02-0124-04
2011-01-18
王宁(1975-),女,辽宁沈阳人,作家,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