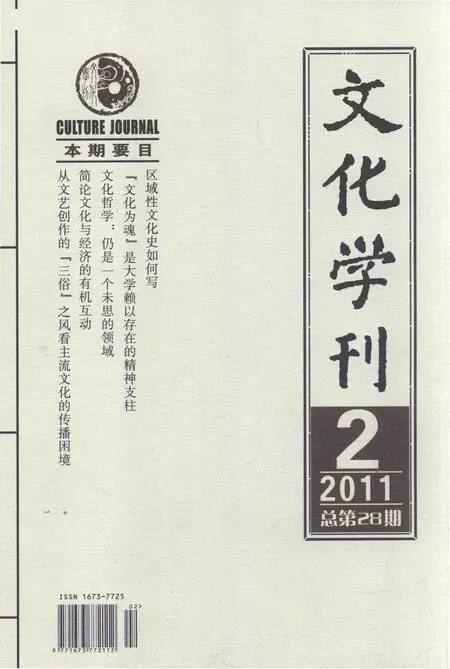质疑花木兰
石海雄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质疑花木兰
石海雄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传统认为花木兰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优秀代表,这种观点是缺乏理性分析的。历史上的花木兰可能是一个身体畸形的“男性假两性畸形”人。战功赫赫的花木兰并不美丽善良,她是嗜血的。花木兰“女扮男装”参军打仗,她的成功代表着男性的成功。“花木兰”误导了中国当代的“男女平等”。花木兰是“女性自然肌体”与“男性社会角色”的嫁接与融合。明清时代的舞台上涌现了更多的花木兰式的女英雄,这种现象反映出男人内心的恐惧和软弱。
花木兰;畸形;男女平等;男人;软弱
花木兰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①1993年,虞城县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木兰文化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聚集在商丘,一起分析了《木兰辞》内容和尚存的元碑记载。一致认为,花木兰是河南商丘虞城县人,已确凿无疑。本文采信这一说法。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形象。从北朝《木兰诗》开始,花木兰的故事就一再被重写,传唱。
人们把花木兰定义为英雄人物。认为她美丽善良,勤劳勇敢。说她是中国北方女性的优秀代表,是人民心目中女性的理想化身,是东方美神,是女性追求解放的先驱。并认为花木兰形象的出现,冲击乃至颠覆了父权文化,从而开辟了男女平等的新纪元……。②此类说辞已充斥于各种有关花木兰的研究资料之中,这里仅取代表性的两例: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的定论花木兰“表现了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东方美神花木兰》,现代语文,2010年10月,谢建丽。看得出,无论作为现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艺术符号,花木兰在主流话语中都已光彩照人,意义特殊,几乎成了高居云端的神人。花木兰真是如此完美吗?我们能否让花木兰走下神坛,还原到其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去加以审视呢?在此,我想试着从以下几点入手做一些分析,力求在花木兰的世界里增加一种更为理性的声音。
一、花木兰是女人吗?
作为文学形象,追问花木兰的性别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如同我们没必要搞清观音菩萨究竟是男是女一样。但当我们把她视为一个曾经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时,质疑花木兰究竟是“她”还是“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木兰辞》中描述花木兰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伙伴与她“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这可能吗?
首先,在战争这种人类最残酷的游戏里,在农业社会极端落后的后勤条件下,一个女性去沙场征战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建立赫赫战功更无异于天方夜谭,花木兰何以如此幸运和例外?其次,“军队作为一个团队,它以团体的方式进食、睡眠……”,[1]花木兰如果真是一个女人,在面对无处不在的男人们时她如何去应付一个女性最基本的生理代谢而不被发现,刁兵武夫们随便一个粗鲁的玩笑都岂不会让她原形毕露?还有,在以命相搏的战争环境中,机敏与迟钝的瞬间之差所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生死之别,任何与厮杀无关的“啰唆”都意味着生命的损失,那么花木兰是如何做到既能“扮男人”又要打胜仗的?
笔者以为,当一群久经沙场的老兵与一个“假男人”相处十年而没发现她的异常和破绽时,我们怀疑的不是这些历经战争淬炼的老兵们观察和感知世界的能力(在这里我更愿意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不会赞叹花木兰有着超人的伪装技巧,而是怀疑她本质上就不是“假男人”,而是一个“假女人”,即现代医学上所谓的“男性假两性畸形”人。①参见中国司法鉴定资讯网:身具此种畸形的人,由于外生殖器官呈女性特征,因而生下来以后,容易被父母当作女性来进行抚养和教育。
一般来说,社会对一个人的性别认定最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认定发生在他(她)刚出生的那一刻,第二次认定则是在其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之后。人在孩童时期性别特征分化本来就不是很明显,营养的缺乏则更会使人发育缓慢。古代北方,民风粗犷,如果花木兰身体有点畸形,在医术落后的时代她在家中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女孩子是有可能的。木兰性别的第二次认定应该是在其从军以后跟战友相处的这十多年里,从时间上推算也就是在她大约十五六至二十七八岁之间,②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记载,汉代结婚年龄女子是十三四岁,晋武帝下令女子出嫁不得超过十七岁,后世基本类同。从她既能从军又未婚配的状况来看,年龄应该在十四五岁左右。这正是人的第二性征发育最快和特征最突出的阶段,在这十多年里花木兰以她的体貌特征和行为表现而被战友认定为“男性”,应该是符合木兰实际上的性别特质的。如果仅仅去翻看一下世界体坛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世界上类似花木兰一样具有杰出表现的“假女人”不乏其人,如波兰田径选手瓦拉谢维奇、南非田径女子名将卡斯特尔·塞门亚、尼日利亚的足球运动员詹姆士·约翰逊等等。[2]
如此,花木兰不仅体貌特征,甚至一举一动都可以自然地呈现自己本质上的男性特点。所以,在战争环境里就不存在刻意掩饰的必要,相反,“女扮男装”反而使得她纠正了以前性别认知的谬误,回归了自己本该应有的角色,从而使她找到“入戏”的感觉,更好的发挥特长,建功立业。故而,这里的问题不是花木兰的伙伴“不知木兰是女郎”,而是花木兰的父母和木兰自己“不知木兰是男郎”。
二、花木兰“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优秀代表,是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先驱”吗?花木兰的形象是否开辟了男女平等的新纪元?
这种定性是缺乏分析的,是非理性的吹捧与误读。
首先,认为花木兰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性,这是完全的主观臆断。
无论浪漫主义让人类的自由精神翱翔至何种境地,社会的发展却总是遵循着现实冷冰冰的逻辑,历史向来是在罪恶和血腥中为自己的前行开辟道路。战争造就英雄,但战争锻造不出美女。在鲜花与掌声之外,与英雄气质相伴的元素往往是疾病、伤痕、扭曲、丑陋、阴暗、乃至于死亡,花木兰也概莫能外。并且,在冷兵器时代能打硬仗的女人必是力壮如牛,浑身肌肉,而绝不会是娇喘滴滴的杨玉环或者弱柳扶风的林妹妹。杨玉环的“凝脂”到了天寒地冻的北国战地是难以继续保持香艳的,林妹妹的葬花锄更是万万做不了砍杀敌人头颅的武器的。战争更成就不了母性,一将成名万古枯。母性意味着滋润、生成、营养、爱抚和呵护,而战功赫赫的花木兰身后是无数个和自己有着同样不幸的孩子的冤魂和累累白骨。
尽管,我们不能去苛求古人,但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把一个嗜血的花木兰与诸如“美丽”、“善良”等等这些女性最正面的品质统一起来。
其次,花木兰的成功仍然代表着男性的成功。
在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虽然都不乏英勇的女战士,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讲,男子更有力量,所以在农业社会里,战争几乎是男人的专利。花木兰进入历史视野是以“女扮男装”和“替父从军”开始的。这里的“男装”不简单的只是一身装束,它是一种符号标示,是一种身份指定。它所表征的花木兰的社会角色内涵是男性的。同时,花木兰是在以“男装”来完成了自己的“性别置换”之后,才得以从军作战。这说明其所从事的战争是完全排斥女性的。所以,花木兰是以“男性的角色”,在“战争”这一男人游戏的舞台上进行了成功的表演。其结果证明的不是自己作为女性的成功,恰恰相反,她所证明的仍然是男性的成功。这种成功千百年来已经被男人们自己反复证明了无数次了,花木兰所做的不过是再次简单的重复。
再次,对花木兰形象的不当解读误导了“男女平等”。
花木兰的“骄人业绩”所示于人们的是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假象。这种所谓的“男女平等”没有鼓励女性去探寻真正适合于自己性别特质的生活和审美方式,却让女性设法将自己的性别掩盖起来,认同以男性的标准来塑造和衡量女性,以类似于“打仗”和“军功”这种行为方式和实践结果的完全同一来宣告:凡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于是,追求男女平等就演变成为了女子不顾差异地向男人看齐。它不仅会破坏社会分工,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和全社会中性化的倾向,更糟糕的是它会误导博弈中的弱势一方——使弱者以为自己不弱,贸然地把自己抛入到一个丛林法则盛行的社会中去,最终被无情地压碎和吞噬掉。
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3]它不但没有被深刻地怀疑和批判,同时,它还充满着诗意和豪情,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总之,花木兰是不足以被视为中国古代女性的优秀代表的,更不能被当成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先驱,遑论她开辟了男女平等的新纪元。
三、“花木兰”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人们加在花木兰身上的光环失之妥帖,那么传统视野中花木兰这一个体特例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当年鲁迅先生曾经感叹:“中国最大的艺术就是男人扮演女人。”在此,我们也可以说:花木兰最大的“艺术”就是女人扮演男人——就在于实现了“女性自然肌体”与“男性社会角色”的成功嫁接与融合。这种成功既可以满足女人的虚荣,又能抚慰男人的软弱。这是一个无论女人还是男人都愿意保守的秘密。并且,由于其成功地披上了“孝悌”①以“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来看,花木兰是“孝悌”两全。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外衣,竟然使得人们千百年来不曾去审视它的粗糙和丑陋。
有关这个秘密的故事一直被继续着。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以花木兰为模板的女英雄形象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如佘太君、穆桂英、孟丽君等等。这些女英雄不单是貌如天仙,爱情信念极其坚定,并且都在家国有难时能扶大厦于将倾,解黎民于倒悬,无一例外地扮演男人世界的拯救者和保护神的角色。耐人寻味的是佘太君、穆桂英、孟丽君,这些花木兰的“升级版本”无一不成型于中华文明日渐走向衰落的明清时期。②佘太君、穆桂英作为女英雄形象最早出现在《杨家将演义》,据考证,该书成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杨家将演义》前言,黎野,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再生缘》,陈端生(1751-约1796),华夏出版社,2001年。这是一个中国男人在美女英雄传说中美得一塌糊涂的时代,也正是历史上中国男人吃败仗最多的时代。尤其晚清,败仗一个跟着一个,内忧外患之甚为三千年所未有。于是,舞台上集中了男人对女性所有美好想象的女英雄故事也日渐繁盛,乃至于风行如潮。
遗憾的是,当一个社会的女人被幻想成万能的神时,这个社会的男人并不能得到庇护和救赎,它只是映衬出男人内心的战栗和恐惧、无奈与迷茫。这种类似于母性崇拜的心灵体验,纠结着无数男人的恋母情结。从中能看到的只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斑驳影像和心理尚未断乳的下跪男人。
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平等可言,更没有一点可以憧憬未来的希望支撑。每想至此,我们仿佛能隐隐约约看见花木兰的魅影,在飨食了众生无数的讴歌与崇拜后,正向着我们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诡异的微笑。
[1]肖磊.巴顿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78.
[2]回顾历史“性别之争”虚凰假凤体坛早有先例[N].东方体育日报,2007-01-10.
[3]郑也夫.代价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5.64;走出女性的“花木兰”困境[N].人民日报,2010-03-08.
【责任编辑:王 妍】
I206
A
1673-7725(2011)02-0067-04
2011-01-12
石海雄(1977-),男,甘肃庆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