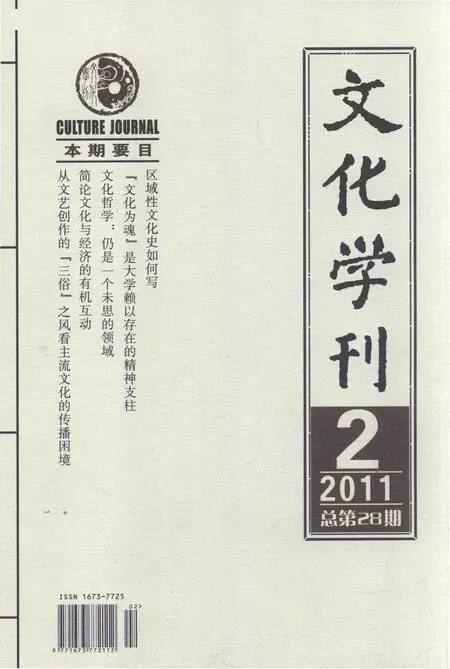地域文化史同样是多元荟萃、绚烂悠长的历史画卷
——读《辽宁文化通史》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地域文化史同样是多元荟萃、绚烂悠长的历史画卷
——读《辽宁文化通史》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在中国众多区域文化之中,辽宁似乎并不是人们眼中的重点。但是,这样的观感即使不是因为“势利”,也是因为评判标准上的偏颇。首先,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也都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其次,华夏中心观或者汉族中心观将以往处于“边缘”的“四夷”过于贬低,他们甚至忘了,北京长期以来也不过是长城脚下的边塞,只是拜了从东北来的民族之所赐,才成为了中国王朝史上的都城。当然,这种现状的造成,也是对这一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所致,而曲彦斌先生作为总主编、集多位专家学者的心血编写而成的九卷本《辽宁文化通史》的问世,则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现状。
地域文化史;辽宁;评判标准
说到辽宁,一般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些什么印象呢?赵本山的二人转和小品?被称为“闯关东”的大移民浪潮?“胡子”、马队或者张大帅?满洲入关前的金戈铁马?甚至还有屈辱的“满洲国”的历史?一个地处边塞以外的冰天雪地的地域,具有怎样的文化发展历程?究竟是哪些方面反映出了辽宁文化的真正品格?
在中国众多区域文化之中,辽宁似乎并不是人们眼中的重点。陕西的关中文化颇受青睐,因为那里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所谓“雄汉盛唐”,其文化成就自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山西的三晋文化也为人称道,因为那里是上古圣王尧、舜、禹的活动之地,华夏文明从那里起源;不用说,江南文化更是重中之重,“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且不说六朝古都,就是明清时期的三鼎甲,也是江南占优;即使是开发比较晚的广东文化,亦由于在近现代史上的特殊位置,特别是近30年来的发展,不由得不让人另眼相看。
但是,这样的观感即使不是因为“势利”,也是因为评判标准上的偏颇。首先,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也都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其次,华夏中心观或者汉族中心观将以往处于“边缘”的“四夷”过于贬低,他们甚至忘了,北京长期以来也不过是长城脚下的边塞,只是拜了从东北来的民族之所赐,才成为了中国王朝史上的都城。当然,这种现状的造成,也是对这一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所致,而由曲彦斌先生作为总主编、集多位专家学者的心血编写而成的九卷本《辽宁文化通史》的问世,则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现状。
一般来说,文化是与人密切相连的。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创造,无论是创造的过程、方式还是结果,就构成了所谓文化。但说到辽宁的文化,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个人类产生之前的古老世界,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影《侏罗纪公园》之类让我把人与地质年代联系起来的缘故。我对自然科学完全没有发言权,但也关注那些科学新发现。当年在辽西地区,曾发现了1.3亿年前的早期被子植物“辽宁古果”,比当时所知的同类植物起源时间提前了1500万年。科学家认为,这种植物的直系祖先有可能是水生的种子蕨类,与以前的认识完全不同。同样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原始热河鸟”,其骨骼特征与奔龙类恐龙类似,为鸟类的起源与恐龙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证据。这一地区的丰富化石遗存揭示了一个生意盎然的远古世界,而这个世界曾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人类长期以来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地用单线进化论的观点来假设这一地区生物的起源与人类史前文化的关系,但辽宁地区的史前文化的确呈现出非常独特的面貌。正如本书第2卷所揭示的,在查海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龙形堆石、陶器上的龙形图案,牛河梁女神庙的泥塑龙和玉雕龙,说明当时存在一个非常清晰和普遍的龙的崇拜。虽然可以确定它与原始宗教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并不知道它与怎样的一个区域文化背景有关联,我们也还不清楚它与中原龙崇拜是否具有或具有怎样的渊源关系。考虑到赵宝沟文化“四灵图”中的凤、鹿、猪的形象,可能与当地的古动物遗存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或许也可以大胆假设,原始先民所能见到的古动物遗存,除了可以与当时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动物直接对应的动物——如鸟类、鹿、熊、猪等以外,还有一些他们无法识别的远古动物,从而构想出龙的形象,并赋予其超出其他动物的神秘意义。
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遗址,体现了辽河文明的早期形态。红山玉文化除了显示权力象征以外,它与牛河梁女神庙显示出的上古祭祀一起,共同展现了早期的礼仪图像。玉可以作为礼器,在各种与祭祀有关的场合使用;而牛河梁的女神庙、圆形祭坛和积石冢则是祭祀的场所。尽管我们未必一定将其与中原传世文献中的上古礼仪相叠合,但这些礼仪器物与场所仍然彰显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重要意义。“戎”的一面或许可以由夏家店文化遗址中分布密度很大的石城堡得到证明。这些城堡包括城墙、城门、城壕、马面等部件,明确体现了防御功能。属于夏家店以及以后时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不仅同样大量作为礼器存在,也有鲜明的北方特征。特别重要的是,本书第2卷告诉我们,在东亚世界,存在一个玉玦文化圈,而辽西可能正是它的起源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是与中原和南方文化类型有异却可等量齐观的另一文明源地。
正如本书第2卷的作者正确地指出的,进入周秦时代,辽宁地区的历史就在以长城东部为景观标志的地理舞台上展开。本书自第3卷到第9卷,即描述了这一丰富的文化发展历程。
在本书第3卷中,作者通过大量考古学成果和历史地理学的考索,揭示了秦汉时期以“汉郡文化”逐渐取代“方国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可以西汉东北四郡之设及其发展为代表。从大量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制度、物质生活与习俗都日益多地受到长城以内文化的影响,日益形成一个“趋同汉制”的走向。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中原政权的制度与文化向边疆地区的延伸是一个逐渐的、甚至多有反复的过程,郡县之设起初只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我们所发现的许多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不过是这几个“孤岛文化”的集中反映,它们还不能代表整个大海的全貌。在这些郡县的城墙之外,甚至在官署的墙外,仍生活着大量语言、风俗等文化各异的人群,他们多数还不是中央政权的编户齐民。恰恰关于这些地区的族群,我们还缺乏更丰富的历史证据。对两汉时期这一地区夫余、高句丽、乌桓、鲜卑的社会文化发展道路,我们还不能只停留在中原王朝文献的只言片语的程度上去把握。
本书第4卷所描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辽宁地区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事实上,我个人并不十分情愿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样一个中原王朝更迭的时段名称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东北或者辽宁,因为虽然这一地区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往来日趋频繁,但并非全部时间和整个地区都是中原政权之下的地方政权,与南朝更没有直接的关系。既然是文化史,我们当然是以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而非政治系统作为原则。相反,以鲜卑为代表的本地族群的强盛,随着他们进入塞内并建立强大的政权,给北方中原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此一时期中原汉人较多地进入辽宁地区,不仅是中原文化向外扩展的结果,也是鲜卑等族进入中原、在长城内外形成统一的族群文化版图的结果。
这一结果导致了一个人们往往回避讨论的历史连续性。在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影响下,传统的历史叙事往往以王朝的更迭为历史的断裂;在汉人中心论的影响下,这一叙事传统又往往以边疆族群入主中原为历史的断裂。但是,假如从边疆族群的角度出发,在鲜卑等族入主中原之后,唐朝的“安史之乱”爆发于东北边塞并不是偶然的,紧接着就是唐末契丹的兴起与南进,直至女真在华北建立统治,这恰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段历史不仅是辽宁的历史,也不仅是东北的历史,而是把东北和华北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而过去,这个整体是被长城障塞隔断的。今天的辽宁,正是这个整体的空间连接点。
本书第5卷是讲契丹文化与女真文化的内容。如前所述,这应该是这幅画卷中最辉煌绚烂的华彩部分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不仅是时段上的相近,在区域文化发展的意义上,也可以与中原王朝史上的唐朝相提并论。但是,辽代文化并不等于契丹文化,金代文化也不等于女真文化。辽代和金代都是时间的概念,它们必须涵盖在这一时段中存在的一切文化,那恐怕就不只是契丹和女真文化的问题了,因为在辽统治区和金统治区内生活的绝不只是契丹人和女真人。当然,这也体现了辽金史研究界这些年来视野上的一些缺失,即将辽金史视为以契丹和女真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这就把这一历史时段的意义大大局限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契丹和女真文化并不仅呈现于今天的辽宁,因此所描述的内容,不能是泛泛的、在整个辽金统治区内的契丹、女真文化,而必须要落脚到今天的辽宁。或者说,我们应在这卷看到的,是在辽金时期,辽宁这个地区的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辽地之得名,与辽之国名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随意忽略的。这些都恰恰说明,辽金时期的辽宁史,以至辽金时期的北中国史,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第6卷将元明两代相连,是注重了元明二者间的连续性,而非以往强调的差异。与以往不同的是,从辽金以降,关外辽东地区与关内属于同一个行政版图,这种状况至元不变。到明代,虽然汉人成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并在这里设立辽东行都司,隶山东都司,而非州县,但毕竟保持着中央的直接控辖。与此后的清相比,虽然盛京地区与关内仍在同一版图内,但因其龙兴之地的特殊地位,反而在近300年里成为不可随意往来的禁地,从而一时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人数有限、变化无常而又颇具悲剧味道的“流人文化”也在第7卷中占有较大篇幅的原因所在。
第6卷的作者在讲述明代辽东文化时,十分注重卫所体制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学校、书院等教育机构,都是在卫所体制下设立或在其支持下创办的。虽然明代在全国各地遍设卫所,使其与州县体制共同构成明帝国的基本管理体系,但在辽东,卫所代行了内地州县的职能,使其成为研究卫所军户制度之行政实践的极好地域。因此,本卷较大篇幅描述的寺庙与信仰,特别是将真武庙与关帝庙及其信仰与卫所的设置及军士的信仰生活联系起来,是非常正确的解释路径。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以往颇为人乐道的广宁寺碑和奴儿干都司之设,虽然不在今天的辽宁,但同样是明初帝国经略东北边陲的产物。为什么永乐时派遣宦官亦失哈巡视奴儿干都司时,修建广宁寺并立碑纪事,正是前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事与祀事相辅相成的例证——寺庙并不仅像今人理解的那样只表现出宗教信仰,而是帝国对某一地区实现有效控制的象征:军事征服只是第一步,但却不能总是“马上治之”;所谓文治武功,寺庙就代表了文治,代表了某种礼仪秩序的确立。今人研究寺庙者,多不及此,故无法理解其中的真谛。
清代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的辽东边镇一变而成盛京,到清末开禁、大量关内人口涌入后则发生更剧烈的社会变革。正如第6卷一样,第7卷所涉及的辽宁文化应该置于内务府体制下的旗人社会这个框架中去理解,主要的篇幅不应给予少数几次皇帝的东巡谒陵和作为流人的汉人士绅,这时的主流是生活在这里的旗人和部分民人。许多档案和族谱没有能够得到利用,不能不说是件憾事。近代辽宁社会至少有三件影响巨大的事,都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冲击,同时也影响到全国、甚至东北亚世界:一是闯关东,二是“满洲国”,三是解放军出关及土改。这三个事件给20世纪以后的辽宁和东北文化带来了重要特征,即移民文化、殖民地文化和老解放区文化,在本书第8卷中,作者对第二、三个特征及其相关文化现象作了较充分的展示,但对第一个特征却几乎付诸阙如。
我本人在当代文化史领域是个门外汉,无法对本书第9卷作出很恰当的评述,而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往往是难度很大的事,因此对作者的勇气表示由衷的钦佩。事实上,人类学者、民俗学者等等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当代文化,他们的文化书写与历史学者的书写会有怎样的不同?我们可以期待。
非常感谢本书的总主编和作者,使我不仅通过阅读全书增长了许多见闻,而且启发我思考了许多以前很少想过的问题,所谓读书使人明智,应该就是包含了这两层含义吧。当然,有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想透,更没有经过实证,因此许多想法都是假设而已。上面的读书体会所提出的问题,就让我和作者、读者们一起继续思考和研究吧!
[责任编辑:董丽娟]
K29
A
1673-7725(2011)02-0007-04
2011-02-20
赵世瑜(1959-),男,四川成都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