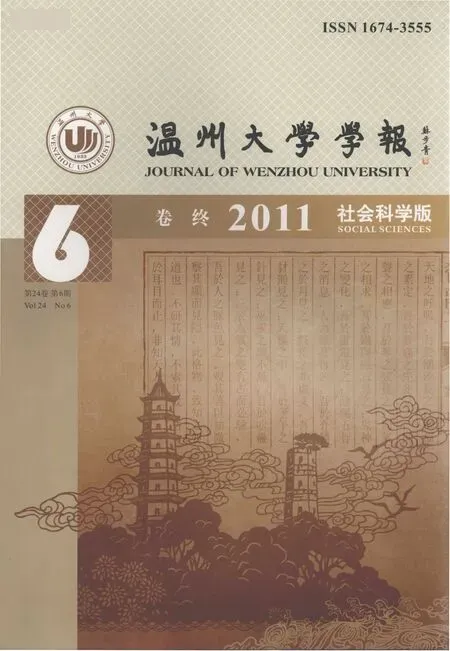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许 晖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许 晖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男性形象可分为弱势男性群体、西方男性群体、特殊时期男性群体以及同性恋群体。这些男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非理想”。从时代环境角度以及女性个体心理角度来分析,产生这一类型人物形象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在性别和异域文化的双重压迫中产生了必须将男性“弱化”的心理需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心理。
严歌苓;小说;男性形象
2009年,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的连续剧《一个女人的史诗》,是由严歌苓这位著名的北美华文女作家的作品改编而成的。严歌苓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很多人的视线中。严歌苓是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坛的当代优秀作家,具有强烈“雌性”色彩的兼宽容、温顺、牺牲和原始情欲于一身的东方女性是她作品中最大的亮点,是目前国内外对她的作品研究的重点所在[1-4];另外从语言和结构角度进行技巧研究,从悲剧和困境角度进行历史研究,也是对她作品的主要研究方向[5-7]。严歌苓作为一位优秀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她笔下众多别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单纯善良的小渔,还是沉默固执的小穗子,又或是柔弱坚强的伊娃,都极富个性,跃然纸上。然而反观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却不是这样。相比女性身上所体现的种种美德,她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是有各种各样缺陷的,是“非理想”的。
一、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一)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弱势群体
《少女小渔》中的江伟,在国内时曾经很有地位,到了国外却沦落得什么也不是,不得不靠小渔“骗婚”来取得国外的居住权①见: 严歌苓. 少女小渔[C] // 严歌苓. 严歌苓自选集.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以下所论小说均出于该选集, 不再一一注出.。尽管江伟的外表和在国内时没什么大变化,依旧健壮,“喉结大幅度升降,全身青蛙肉都鼓起,把旧货店买来的那件西装胀得要绽线”,可是内心却变得十分脆弱,“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恃地饮泣”,“他烫人的抖颐,他冲天的委屈”,对现实他毫无办法,却不断地把气撒在实际上救了自己的小渔身上,换取可怜的尊严。还有那个卑微委顿的老头,在小渔面前,“他半蹲半跪在那里,仰视她,似乎那些钱不是她捡了还他的,而是赐他的”。在他潦倒一生的最后岁月,是少女小渔救赎了他,使得他至少获得了一点尊严,一点自食其力的快乐,一点需要被尊重的知觉。一般人认为本应该更柔弱的女性小渔,竟然成了两个男人的支柱。
在这个群体里,也包括了这样一种人,“这样的一种老单身汉,一辈子没有攒够回乡娶亲的钱而独身一生。他们贫穷而自尊,是旧金山唐人街将要消失的一个社会层次”,《青柠檬色的鸟》里的洼就是这样的老单身汉,他孤独潦倒。香豆死后,他失去了仅有的一个朋友,只能靠在色情小说中想象着她的样子过活。他是那么可怜而卑微,因为“走在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唐人街的街道上,没人想了解他,认识他的人永远叫错他的名字”。
(二)拥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西方男性形象
第二类男性和上文的截然相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西方男性形象。《栗色头发》里的“拜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的律师,以及《花儿与少年》里的瀚夫瑞,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这一类人物在西方社会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谈吐文明,优雅绅士,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在《栗色头发》中,“拜伦”对“我”萌生爱意,不断地为“我”解围。帮“我”的忙,可是到最后,虽然两情相悦,“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拜伦”“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哗”,优越惯了的“拜伦”不可能理解身在异国他乡的“我”对于自己的民族有着更为敏感的情怀,有着更为细腻、生怕受到一点伤害的民族情感。《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的律师,将要娶中国女性伊娃为妻,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现着富有民族熏陶出的优雅,亲和,文明。他慢条斯理地容忍伊娃瞒着他照顾女儿,容忍她撒谎,他永远冷静,有着应该有的怜悯,却给人“他简直拿他的高尚来欺负人了”的感觉,而不是真的爱伊娃,真的爱她先天不足的女儿,他也不理解这种血脉相连的人性。所以最后他这种“施舍式”的仁慈,使得已经随女儿死去一半的伊娃无法再留在他身边。《花儿与少年》里的瀚夫瑞有着强烈的改造欲望,他希望自己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够像自己一样富有教养,优雅而文明。他厌恶一切他认为的“野蛮民族”遗留下来的恶习,他尽全力打造他的中国妻子和女儿。因此他可以把自己“教化”的败笔之作苏送进戒酒协会,他可以优雅地让九华在家里失去立足之地,让晚江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和儿子见面。西方以理性为主导的文化氛围,在社会精英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精英人物无法理解感性的东方女性,无法理解她们坚强柔韧的外表下有颗敏感脆弱的心,无法理解她们对骨肉亲情的重视。
(三)生活在特殊年代的男性
第三类形象是生活在特殊年代的男性。比如文革时代,人性受到扭曲,男性无法保护女性,也无法保护自身。《天浴》里的老金,是个身体不齐全的人,他想要保护下放牧场改造的文秀,可是他自身难保,谈何保护别人?老金眼看着文秀为了回城不停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却无法解救文秀,无法阻止文秀受这种侮辱,直到最后和文秀双双死去。《扮演者》里的钱克,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直到沈编导找他扮演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就迷失在虚幻的一呼百应的高贵和尊严中。钱克就因为外型和领袖的相似获得了尊重,获得了爱情。其实,他没有坚定的人格,他和小蓉的恋情一旦被沈编导发现,就会失去所有的一切。他害怕回到原先的自己,那个被别人看不起的自己。最后他只能选择在虚幻的高贵中死去。《一个人的史诗》里的欧阳萸,成天沉浸在虚无飘渺的风花雪月中,毫无生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只能靠妻子田苏菲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否则他是无法捱过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的。
(四)特殊群体:同性恋者
最后一类是比较特殊一个群体,同性恋者。现在同性恋者在一些国家享有充分的权利,可以有不受打扰的世界。但是,当这样的人进入女性群体,尤其是处于性别和地域双重边缘身份的女性群体中的时候,就充满了无力感。《冤家》里的博士,十几年前在家人的策划下,欺骗了南丝,使得南丝对他恨之入骨,南丝要割除女儿璐与父亲的一切联系。可是博士却无法战胜自己的天性,还是偷偷地和女儿联系,买女儿爱听的CD,忍着被南丝冷嘲热讽、赶出家门的窘迫,去看女儿。尽管如此,女儿还是得依靠南丝来抚养,抚养成为和南丝一样的人,“十四年来的一个瞄准无误地重叠”,“重版了她的青春”。作为父亲,博士是无奈的,他使得女儿人生中“父亲”的概念缺失了。同样的悲剧发生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的亚当身上。亚当家大业大,需要有人继承,可是他的性向却又不允许他有这样的传承。于是他和伊娃达成了协议,给伊娃五万美金,雇伊娃替自己繁衍后代。可是用精确的试管和“非污染”的绝对环保食品精心孕育出来的女儿却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危在旦夕。面对这样的情况,就算是富有高贵的亚当也束手无策,到最后抚养的责任还是必须由伊娃来完成。亚当和博士的身份、性格、命运不同,可是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们同样没有答案,对命运同样无能为力。
由此看来,严歌苓创作的男性形象,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从一个女作家的角度来说是“非理想”的。为什么她没有像赋予女性美好的东方色调一样,多给予男性一些吸引人的个性呢?
二、男性形象“非理想”的原因及作家对男性的谅解
(一)地域因素
通常情况下,华人移民要面对和适应的是与自己的祖国全然不同的环境。作家也是一样,尤其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在海外生活和写作,常常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严歌苓自然也不例外。在迥异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不得不被动地陷入一种“边缘人”的漂泊状态。《花儿与少年》里的晚江,《栗色头发》中的“我”,或者《亚当与夏娃》中的伊娃,都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她们既已经脱离了本族男子的强势范围,不再对本族男子产生幻想(或者可以理解为在国外,本族男子的情况也大多不乐观),而异族男子,却又因社会、种族、地位等等原因而无法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女性身兼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边缘身份,更强烈地感受到强大的西方社会规则的压迫和排挤,从而产生本能的抗拒。而另一方面,她们对男性的幻想破灭了,对异国的幻想也破灭了[8]。日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都要求女性必须迅速独立,适应新的语言、新的环境、新的思维方式。女性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努力从物质到精神增强自己的独立性。
(二)心理因素
当两性中的一种性别独立性增强之后,另一种性别相比较而言就显得弱了。男性的作用在女性心里弱化了。不是因为男性本身不够完美,是女性的个体心理发生了变化,在抗击和独立的双重作用下,她们被动地发现了“自我”,在“自我”的发现过程中,男性贬值了。凯特•肖邦的《一小时故事》中描写过女性这种“自我”意识的发现:患有心脏病的马拉德夫人听说丈夫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消息,感到一阵悲痛过后,意外地发现自己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而正当她为自己重新获得自由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意外地看见远离事故现场的丈夫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使得马拉德夫人心脏病复发,当场倒地死亡。《一小时故事》的情节,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案例。在潜意识里,马拉德夫人希望丈夫死去,因为丈夫的存在压抑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乐极生悲,只有她自己知道是因为丈夫的安然归来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刚到手的“自我”成了泡影[9]。同样,严歌苓小说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有缺陷的男性人物形象,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女性在抗拒心理和独立能力的要求下,产生了一种渴望男性“死亡”的心理,当然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这种渴望被诠释为“缺陷”。从某种意义来说,男性不是事实上有那么多的缺陷,而是女性希望他们有那么多缺陷,在女性的潜意识里,只有男性是有很多缺陷的,是不完美的,女性才有可能完成对“自我”的挖掘和激发[10]。
(三)与男性的“和解”
有趣的是,尽管作者在塑造男性形象的时候,突出了他们的缺陷,似乎男性都是不可靠的。但实际上,对文本深入阅读后我们发现,小说中,男性并没作为女性的对立面被排挤、被丑化,相反,作者尽力为他们营造相对适宜的空间,使他们与女性最终获得“和解”。《少女小渔》里的老头,在小渔的感化和鼓励下,下定决心自食其力,拿起小提琴到街头卖艺,获得了灵魂的救赎。《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欧阳萸,在小菲的百般照料和呵护下,两个人达成了共同的理解,携手共度一生;《扶桑》里的大勇从来没有把扶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而仅仅是一个玩物,但是最后他被送上刑场,扶桑竟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法场与他拜堂成亲。而且,这种“和解”也不单单存在于东方男性和东方女性之间,同样存在于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之间。《栗色头发》里的“拜伦”、《亚当和夏娃》里的亚当、《花儿与少年》里的律师,他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和东方女性有着质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东方女性和他们最终达成谅解。没有哪个男性角色是和女性刀兵相见的,故事的结局都是和解。这样的一种创作倾向,又反映了严歌苓怎样的创作心理呢?
首先,如同上文所说,女性在地域和性别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了必须将男性“弱化”的心理。在心理层面上说,女性认为自己比男性强大,在现实层面上说,女性不可能跟男性决裂。所以反映在作品中就成了:男性尽管不争气,但女性包容他们,原谅他们,两性获得不平等的和解。这一点恐怕是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共同创作心理:她们比谁都明白,在异国他乡,女性不可能过分依赖男性,事实上男性很有可能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而与之决裂,则更是不可能的事,女性还没有这种力量,完全不依赖于男性。其次,这也有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的原因。刘俊将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分成两大类,其中严歌苓被划分为大陆作家群。这个作家群的特点是没有把“北美经验”作为唯一的创作题材,而是更注重自己的“大陆经验”。以一种文化“边缘人”的角度,在创作中流露出对“融入”与否的不太在意[11]。毕竟现代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地强化,我们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创作理念。单就严歌苓而言,在她的作品中,从来不乏传统文学创作的气息。她笔下的东方女性,有着东方传统的美德,坚忍、宽容、大度。就是这样一种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使得她们在对待不够理想的男性时体现出最终的宽容和理解。即使受到忽视,即使被伤害被侮辱,她们也都能够大度地对待这些男性。在面对与自己所熟悉、所依赖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的西方文化氛围时,中国传统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同样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时,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要求的不是改造,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怎样取得在“不同”基础上的和解。女性当然也不例外,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圈子里,保有自己的尊严,同时求得“和而不同”的效果,这是严歌苓笔下众多的女性面对西方强势男性的共同态度。
综上所述,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形象,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她笔下的男性作为一种性别被弱化、被降低了期望值的符号,他们是在海外的特殊地域环境下被创作出来的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男性从理想化,变得不理想;女性从满怀期待,到依靠自身,都是时代左右的结果。走近这些人物形象,去思考他们的内在本质,了解他们存在的背景和意义,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海外华文创作,了解海外华人心理,了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下两性个体变迁的最好的平台之一。
[1] 王列耀. 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 [J]. 名作欣赏, 2004, (5): 91-94.
[2] 付立峰. 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J]. 华文文学, 2007, (3): 84-89.
[3] 刘艳. 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 严歌苓创作品格论[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45-50.
[4] 李仕芬. 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 读严歌苓《倒淌河》[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3, (4): 21-25.
[5] 陈思和. 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 读女作家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C] // 庄园.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30-36.
[6] 陈振华. 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 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 华文文学, 2000, (2): 22-26.
[7] 朱立立. 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 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J].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63-67.
[8] 陶兰. 评严歌苓对中国女人之“最高雌性”的文学书写[J]. 电影评介, 2009, (14): 105-106.
[9] 宋雪. 凯特·肖邦小说《一小时的故事》的女性主义解读[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 110-112.
[10] 胡颖华. 论严歌苓“雌性”书写的矛盾性[J]. 名作欣赏, 2009, (18): 52-55.
[11] 刘俊.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J]. 中国比较文学, 2007, (2): 94-109.
Study on Male Images in Yan Geling’s Novels
XU 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China 541006)
The male images in Yan Geling’s novel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vulnerable male group, group of western men, group of men at a particular stage and group of homosexual male. These male images have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non-ide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me circumstance and female’s individual psychology, the main reason of these phenomenon lies in the female’s psychology of weakening male status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the sexuality and foreign cultures. All these can partly reflect the writing psychology of overseas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their creation process.
Yan Geling; Novel; Male Image
(编辑:刘慧青)
I206.7
A
1674-3555(2011)06-0110-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6.01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1-01-02
许晖(1987- ),女,壮族,广西崇左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特约栏目主持人语·Words from Special Column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