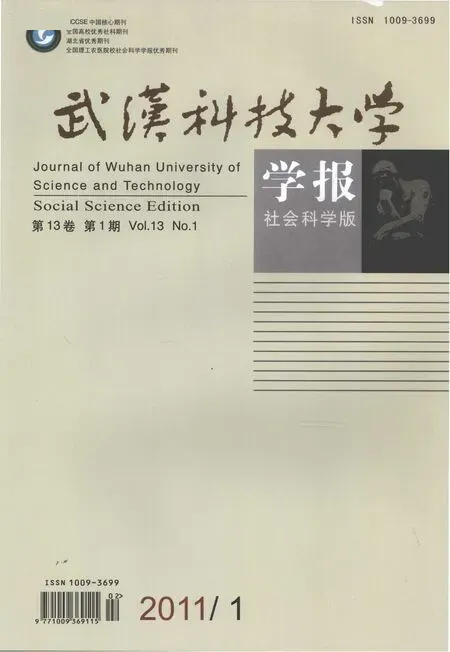墨子对主体间互爱互利关系的建构及当代意义
成 龙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53)
墨子对主体间互爱互利关系的建构及当代意义
成 龙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53)
如何构建主体间互爱互利的关系?这是墨子思想的核心。面对战国时期各主体间互相残害、“交相亏贼”的现实,墨子对主体间的关系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等一系列交往原则。墨子的论述说明:主体间的互爱互利首先是思想情感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现实法制的保障。
墨子;互爱互利;建构
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作为下层劳动者的代表,对如何建构“大国-小国”、“大家-小家”、“强者-弱者”、“贵者-贱者”等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作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等一系列主张。研究墨子关于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建设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墨子建构主体间互爱互利关系的三个原则
墨子对主体间互爱互利关系的思考,本质上是一个实践伦理问题。墨子的主张,贯彻了三个相辅相成的原则:“兼爱”、“交利”、“法仪”。“兼爱”必然体现为“交利”,同时要以“交利”和“法仪”为基础;“交利”要通过“兼爱”和“法仪”来保障;“法仪”不仅作为手段,而且以实现“兼爱”和“交利”为目标。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墨子哲学的逻辑体系,闪现着墨子对主体间相互关系的独特见解。
(一)培植“爱人如己”的思想情感
墨子生活于战国初年,当时诸侯纷争,天下大乱,不同主体视对方为仇敌,互相残杀,出现了“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为人君者不惠”、“臣者不忠”、“父者不慈”、“子者不孝”、“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等不同主体交相为乱的现实。墨子认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
(1)“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究其原因皆起于人们自私自利,彼此不能相爱。做儿子的爱自己不爱自己的父亲,因而总是亏损父亲而寻求自利;做弟弟的爱自己,不爱兄长,因而总是亏损哥哥而有利于自己;做臣子的爱自己不爱自己的国君,因而总是亏损国君而有利于自己。同样,做父亲的也不知爱儿子,做兄长的不知爱弟弟,做君主的不知爱臣子。“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墨子·兼爱中》)不仅如此,人们甚至不能做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完全只顾己身,连丝毫之惠都不能推之于他人。“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不仅一家之中、一国之内情况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墨子·兼爱上》)爱是主体发自内心的思想情感,爱的对象可以是个人、群体、国家。墨子认为,挽救社会首先在于挽救人们的思想情感,懂得爱人。
(2)“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在搞清了天下大乱的原因后,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交往原则。他说:“兼即仁矣、义矣。”(《墨子·兼爱下》)爱人并不是仅仅爱某个人,而是要普遍地爱人。“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墨子·小取》)“爱人若爱己身。”(《墨子·兼爱上》)“视人之室若己室,视人之国若已国。”(《墨子·兼爱上》)“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墨子·大取》)可以看出,墨子倡导的“兼爱”是无差等之爱,其对象不止于一人、一家、一族、一国,而是人所能及的任何人。墨子认为,“体,分于兼也。”(《墨子·经上》)个人是“体”,个人之体是从人类之兼剥离出来的。爱为每个个体所承担,否则,兼爱就成了一句空话。而能承担爱的个体,无职位尊卑、财富多寡的差别,哪怕是奴隶,仍应享有爱。墨子说:“爱臧(男奴隶)之爱人也 ,乃爱获(女奴隶)之爱人也。”(《墨子·大取》)为什么呢?因为“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墨子·小取》)而且 ,“人无长幼贵贱 ,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所以,只要是人,在爱这个问题上就是平等的,就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如果因其出身低微而不能爱之,就“有失周爱”了。
(3)行兼爱,“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墨子认为,只要人们彼此相爱,处处为对方着想,融洽相处,那么,天下的祸乱也就不攻自息了。他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然而,天下之士君子,非言兼爱的言论,却一直不能停止。针对人们对兼爱说的各种非难,墨子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驳。他分别以行“兼相爱”和“别相恶”的士人和君主为例,说明面对生离死别的困境,人们一定会选择行兼爱的士人和君主。有人把行兼爱比喻为举着泰山跨越长江和黄河。墨子指出,这样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墨子·兼爱下》)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治理天下的时候,就做到了“兼爱”。从前越王好勇,士皆敢死;楚王好细腰,一国皆饿死;晋文公好苴服,满朝皆破衣;这说明民风并非不可改变,只要君主带头,行兼爱就像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一样容易。“茍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爱下》)
(二)遍察“皆得其利”的致富之路
墨子认为,爱人不仅是一个思想情感问题,而且是一个利益问题。“义”和“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为了实现天下之“利”,墨子提出了“尚贤”、“节用”、“节葬”、“非命”、“非攻”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主张。
(1)“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认为,只有让那些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天下人才可能各自施展自己的能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任用贤能的人,让不肖之徒出于国君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墨子·尚贤中》)“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墨子·尚贤中》)其结果必然是,“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墨子·尚贤中》)古代的圣王尊崇贤士而任用能人,不偏党父兄,不偏护富贵,不爱宠美色。凡是贤能的人便选拔上来使其处于高位,给他富贵,让他做官任职;凡是不肖之人便免去职位,使之贫贱,让他做奴仆。于是人民相互劝赏而畏罚,争做贤人,所以贤人多而不肖的人少。这样做的结果是“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而昔时三代暴王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任用贤人,让不肖之徒出入于左右。由此,墨子发出呼吁:“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墨子·尚贤下》)
(2)“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战国时代,生产力虽有发展,但还很低下,人们能够创造的财富依然十分有限。针对当时统治者的奢糜生活,墨子发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的呼唤,提出了一系列“节用”的思想。墨子认为,让奢侈的国君去治理邪僻的百姓,要想让国家不乱,这是不可能的。古代的圣人担当处理国家政务的职责,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方面从来不过度花费。圣人治理一国,能够让这个国家的利益加倍增长,这并不是因为他掠夺别国的土地,而是因为他节省了不必要的费用。墨子明确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提出了“节葬”的主张。因为过度花费,天下的财力就会不足,而一旦衣食财力不足,人与人之间为争夺财物而发生争执和抱怨就不可避免,要想让他们保持亲近和相爱就不可能。墨子说:“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墨子·节葬下》)墨子还反对音乐。墨子指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从事音乐活动不仅不能平息战乱,而且使用乐工要荒废百姓的农活,置办乐器得从百姓那里筹措大量的钱财,王公大人们又总要和其他人一起来听音乐,其结果总要耽误别人的事务。“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墨子·非乐上》)所以,从事音乐活动是一种不必要的消费。
(3)“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墨子认为,有命论是非常有害的。有命论者认为,天下之治乱,人口之众寡,生活之贫富,寿命之长短,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即使使出很强的力气,也没有什么用处。这种主张是不仁不义的。同样的社会和人民,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大治,这能说是有命吗?有命论者以百姓之忧为乐,是在毁灭天下。“说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墨子·非命上》)古代的圣王与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利。”(《墨子·非命上》)古代的圣王还颁布宪令,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墨子·非命上》)有命论者认为,赏罚都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相信命定论,那么做君主的就会“不义”,做臣子的就会“不忠”,做父亲的就会“不慈”,做儿子的就会“不孝”,做兄长的就会“不良”,做弟弟的就会“不弟”。墨子认为,有命论实际是在鼓励人们好吃懒做,不从事生产,“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墨子·非命上》)如果一国的百姓,“上不听治,下不从事”,那么,国家的行政就要大乱,财用就会匮乏。“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墨子·非命上》)坚持有命论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4)“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战争在本质上以藐视和消灭对方的主体性为目的。墨子所处的时代,各路诸侯、各个私室大臣等,各以自己的力量逐鹿中原,导致诸侯割据,战争频繁。在这种“大攻小、强执弱”的形势下,墨子主张君主“视人之国,若视其国”,“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兼爱中》),反对不义之战。墨子认为好战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动辄举师数十万,持续数月以至数年,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比如,战争发动以后,“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墨子·耕柱》)。在战争中,军队、装备被消耗,牲畜损伤死亡,“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墨子不仅提倡国与国之间“非攻”,实行和平相处,还广收天下门徒,长期奔走于各诸候国之间,四处游说强国放弃攻打小国。他自己身体力行止楚攻宋;南游到卫国,宣传“蓄土”以备守御;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等。墨子的“非攻”及其实践行动,实际上是他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天下和平、保护弱小国家主体性的集中表现。
(三)树立“度量天下”的法制权威
墨子很早就认识到了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要保障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就必须使交往主体之间有一套交往的法则,他称之为“法仪”。
(1)“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墨子认为治理天下应该有法可循。他反复强调“言必立仪”,意即无论做工务农,还是治理天下,都必须有法度可循,否则将一事无成。他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墨子·法仪》)墨子所说的“法”或“法度”,泛指一切标准、规范或者制度,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但从他这里所强调的“至士为将相者皆有法”,以及“治大国”、“治天下”等方面来看,无疑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和“国家制度”等内容。这里,他将法与圆规、曲尺、绳坠等度量衡相比拟,以突出法律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墨子自我比喻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墨子·法仪》)圆规和矩尺是制轮匠人的工具,它们可以“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这里,“中者”标准就是他的法仪,在政治伦理上就是“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墨子“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的主张对后来韩非、荀况等的法治思想有直接影响。
(2)“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在立法的依据上,墨子主张“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中》)。首先,墨子公开宣称:“子墨子置立天志,以天为法仪”(《墨子·天志下》),并反复强调:“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量天下。”也就是说,墨子以天之意志作为衡量天下士君子言行的“明法”,以“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和衡量言行的最高标准,这表明墨子法治思想是与其“天志”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天志”与法律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治理天下,他选择以天为法的理由是以“父母、学、君”为法都“莫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 ,其明久而不衰 ,故圣王法之。”(《墨子·法仪》)意思是天最公正无私,它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丰厚的恩惠却不要求人对它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君主治国应该效法天来制定法令和政策。所以,墨子认为人类立法应该效法于天。天有三个立法原则:一是立法为公原则,“天之行广而无私”(《墨子·法仪》)。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既然人间之国、人间之人都是天之地、天之人,那就应该平等对待。三是以法治官、以“义政”反对“力政”的原则,“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下》)。墨子推崇“天志”的目的在于强调法律的公正和平等。其次,墨子之法还在于法先王。他把法先王奉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道德行为准则。在判断是非的“三表法”中,第一表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意即他把是否与古代圣王的事迹相符作为判断人们行为的准则。他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贵义》)可见,墨子法先王之法,很是注意到了利益原则。不仅如此,他还把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古代圣王的事迹,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他说:“然胡不考之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下》)墨子强调从法先王的事迹和法先王的路线中找到依据,虽然具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性质,但是他与先秦时代儒家“信而好古”的孔子、“言必称尧舜”的孟子,以及道家主张回归“小国寡民”的老子和描述其“至世之德”的庄子都具有复古倾向有相类同之处,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墨子坚持“以天为法”和“以圣人为法”,表明他也在寻找立法效力的依据。“法天”是墨子构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圣人”是他的立法依据和基础。当然,墨子以“天志”为基础的法矛头重点指向的是统治者,目的是为了将统治者置于天的控制之下,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而是尽可能地为天下人谋福利,以实现他匡救时弊、改造社会的理想。由此可见墨子立法用心之良苦。
(3)“宪、刑、誓”与“法不仁 ,不可以为法”。关于“法”的形式,墨子认为有宪法(宪)、刑法(刑)、军法(誓)。他指出:“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 ,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 ,刑也”、“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墨子·非命上》)。在《墨子》篇中他在引用古代圣王的事例中有多处宪、刑、誓的出现,在此不再赘述。关于立法准则,墨子眼光独到而睿智。他认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子·法仪》),即法不是维护暴政的工具。联系墨子对“仁”的阐述,可见墨子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价值、权利,是为了建立其理想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这种将法赋予道德色彩并以道德作为立法和执法的准则,鲜明地体现出伦理法特色。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墨子之法含有泛指一切依据之意,对于单纯法治思想还具有不明确性甚至带有神秘色彩,但他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为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二、墨子关于主体间互爱互利思想的当代意义
今天,世界和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是时代的重大课题,墨子关于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思想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
(一)互爱互利首先表现为思想情感的融合
一个人只有头脑中视“他人”为主体,具有爱“他人”的意识,行为中才可能为“他人”着想,为“他人”筹划。然而,主体间的思想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从逻辑上讲,可能的情况有四个方面:第一,“我”知道“你”是和“我”一样的主体,但“你”、“我”之间毫无情感可言,我们是竞争对手,甚至是仇敌,我们之间无法尊重和沟通,这大概相当于西方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我”知道“你”是和“我”一样的主体,我们只是这个社会的公民,互不相识,行同陌路,毫无情感可言,只为各自的利益奔忙,“我”不会损害“你”的利益,但也不会做出有利于“你”的事情,这相当于杨朱所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的关系。第三,“我”知道“你”是和“我”一样的主体,“我”愿和“你”平等地讨论,“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会考虑到爱“你”,但“我”不可能如爱“我”一样,或者爱我的家人一样去爱“你”,去爱你的家人,这相当于孔子讲的“仁者爱人”的境界。第四,“我”知道“你”是和“我”一样的主体,因而不但尊重“你”,而且和爱“我”一样爱“你”,爱“你”的家人,时时为“你”着想,这是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境界,相当于墨子“兼爱”的境界。“兼爱”是《墨子》全书的灵魂,“兼爱”的意思就是平等无差别地爱人。
实际上,历史上对“兼爱”的表达并非只墨子一家。墨子稍后诞生的基督教经典《圣经》强调,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生来就是平等的,人们应该互相敬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新约·约翰福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严厉声讨教会的虚伪,鞭挞世俗世界的专制,但基督教“平等互爱”的教义始终未变。稍后,“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尽管资产阶级有虚伪和欺骗人民的一面,但这个口号本身却并没有错误。到19世纪,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人提出的“乌托邦”构想,实际上是实践“兼爱”的另一种试验。马克思正因为看到资本主义下交往关系的异化,才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质上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统治,消灭一切差别,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互爱。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墨子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最初表达者。今天,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而合作的前提是尽可能地为对方着想。在这样的情形下,重新阅读《墨子》,可以引导人们克服自私自利的狭隘心理,培养主体间互爱互利的思想情感。
(二)互爱互利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前提
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贵义》)何为“义”?墨子说:“义,利也。”(《墨子·经上》)“义 ,志以天下为芬 ,而能能利之 ,不必用。”(《墨子·经说上》)在墨子看来,“爱人”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义”和“利”并不矛盾,国家要是没有足够的财物,百姓普遍贫穷,要彼此相爱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正如管仲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有了足够的财物,才可能懂得礼貎,才可能考虑爱人。墨子所讲的“利”与马克思对生产和财富的论述丝毫不矛盾。马克思说过,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就是说,主体间的互敬互爱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离开生产力讲主体间的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墨子不仅提出了“交相利”的主张,而且提出了“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一系列增加社会财富以达到社会互爱互利的具体措施,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文革”期间,我们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强调精神鼓励的作用,以为无产阶级本来就应该是贫穷的,一旦富裕就会变修,这是极其荒谬的。虽然当时阶级斗争的压力在一定范围遏制了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但形势稍有变化,这些东西就沉渣泛起,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发展生产。完全离开物质财富的增长谈爱人,必然要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三)互爱互利还要以现实的法制作保障
为了保障人们之间能够互爱互利,墨子要求立“法仪”,提出了“尚同”、“天志”、“明鬼”等主张 ,要求全国百姓上同于天子,天子要接受鬼神的监督,这可以说是最初的法制建设思想。然而,墨子用鬼神来吓人的做法却是极其幼稚的。由于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对天子的监督就形同虚设。一旦天子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他人的主体性随时都有被抹杀的可能,主体间的互爱互利就失去了保障。
实践证明,主体间的互爱互利需要现实的法制作保障。从历史的视角看,法的阶级性正在日益被淡化,法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从统治和被统治的“主-客”关系向人人身份地位平等的“主-主”关系进化。政党、政府、组织、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趋于明确的划分,法为防止极权和专制做出了各方面的考虑,无论单位、部门和国家,在做出决定时,应更多地采取民主的方法。
在当代中国,在不同主体之间,采取各种手段互相欺骗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官员腐败是对群众的欺骗,企业制假售假是对消费者的欺骗,抄袭他人成果是对作者的欺骗,这说明现有法律有时形同虚设,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人们遭受歹徒袭击,或年迈老人不慎跌到在地需要救助时,路人却往往袖手一旁,不敢救助,原因是担心被救者反诬陷害,而现行法律的确没有相关的保护救助者的规定,说明我们的法律确有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1]任继愈.墨子与墨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蔡尚思.十家论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罗炳良,胡喜云.墨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6]孙怡让.墨子閒诂[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墨翟.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孙中原.墨子及其后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Mutual love and mutual benefit between subjects in Maozi’s thought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Cheng Long
(Institute of Modernization Strategies,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Guangzhou 510053,China)
How to construct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love and mutual benefit between subjects lies at the core of Maozi’s thought.Confronted with the harsh reality of inter-subject infliction,Maozi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inter-subject relationship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rinciples for social contact,including“equal love for others”and“mutual benefit”.The argument of Maozi suggests that mutual love and mutual benefit between subjects should start with emotional involvement,which,however,relies on wealth increment and legal protection.
Maozi;mutual love and mutual benefit;construction
B224
:A
:1009-3699(2011)01-0032-06
[责任编辑 勇 慧]
2010-06-16
成 龙(1964-),男,甘肃通渭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交互主体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