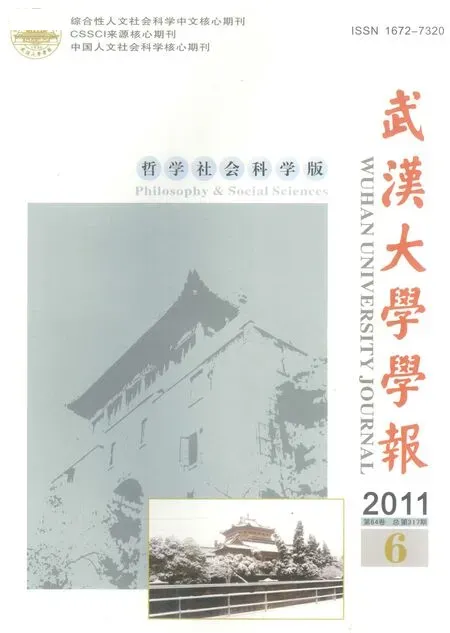论自然遗产保护中的相邻权
马明飞
自然遗产保护与当地原住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是困扰保护行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邻权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自然遗产保护区与原住居民之间的相邻关系,是否属于民法上相邻权的调整范围?我们能否用相邻权制度来解决自然遗产保护与原住居民之间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从目前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当原住民的建设或开采活动对自然遗产保护区构成潜在威胁时,通常有相关的法律、法令对此进行规制。然而,在自然遗产的保护过程中,经常为了保护自然遗产而不得不牺牲当地原住居民的合法利益时,这个时候如何来补偿原住居民的损失,却在立法上无章无循。保护自然遗产固然重要,但原住居民的合法权利同样值得关注和保护。近年来,一些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由原住居民参与管理的社区经营模式得到蓬勃发展,相关的补偿机制也得到确立。处理好自然遗产保护区与原住居民的相邻关系,不仅是自然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面对的命题。
一、自然遗产保护中相邻权的界定
相邻关系源于古罗马法中的地役权,在古罗马时代土地最初为公有,后归家庭私有。为了实现土地的使用价值,所有者需要利用相邻的土地,相邻关系因此而产生。传统意义上的相邻关系指的是相互毗邻的不动产之间的相邻关系,即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相互毗邻不动产使用人或所有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①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相邻关系从权利的角度,又可称为相邻权,即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在处理相邻关系时,相邻各方应本着方便生活、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解决,互谅互让。
然而,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变迁,使得自然遗产保护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与自然遗产相邻的居民或工厂,带来了很多垃圾、噪声、灰尖、工业废物等,这些都对自然遗产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自然遗产的需要,当地政府经常通过颁布法令,对周围的居民房或工厂进行拆迁,虽然这一行为的目的旨在保护自然遗产,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周围的原住居民失去了家园或工作,使得周围的被拆迁的工厂遭受经济损失。对于这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居民或企业进行合理的安置和补偿,既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关系到自然遗产保护的效果。虽然传统意义上的相邻权在自然遗产保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新的经济行为和法律关系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相邻权已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邻权制度也开始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相邻权在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发了变化。首先,相邻范围扩大。在自然遗产保护中,由于地理的整体性、环境的生态性,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与周围的区域息息相关,“相邻”的内涵也得到了扩展。依照德国法学者Herschel的观点,由于不可量物侵入的到达距离延长,如凡其侵入领域均被认为是相邻。随后修改的《德国民法典》也规定不可量物侵害确定是相邻关系上的问题,体现了相邻概念已被加以扩大。其次,调整范围的扩大。传统意义上的相邻权仅调整相邻不动产之间的经济关系,然而在自然遗产保护过程中,除了经济关系以外,还涉及到自然遗产的环保权、原住居民的安宁权、居住居民的舒适权等与环境和人身密切相关的非经济关系。可以说,自然遗产保护中的相邻权是经济关系与人身关系的复合,是法律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双重体现。在环境保护相邻权中,主要考虑的不是怎样利用环境要素才更具有经济效益,而是怎样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①吕忠梅等:《环境资源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再次,权利侵害行为的多样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侵害相邻关系的行为也更加复杂,既可能是直接侵害行为,也可能是间接侵害行为;可能是生产经营活动,也可能是日常生活行为,既可能是一次污染所致,也可能是复合污染所致,这就使得侵害行为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判断。最后,停止妨害请求权内涵更为丰富。传统意义上的停止妨害请求权主要是要求对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而在自然遗产保护相邻权中,请求权的内涵更加丰富,既可以要求侵害行为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也可以要求行为人恢复原状、迁移、赔偿损失或采取补救措施等。传统意义上的妨害请求权以当事人民事权益遭受侵犯为产生的前提,而自然遗产保护相邻权中的请求权,则往往以妨害超过或可能超过忍受限度为前提,而无论其行为是否合法。
可见,在自然遗产保护中,相邻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变化,其扩张是源于环境权的产生和加入,在自然遗产保护相邻权中,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环境保护、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以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二、自然遗产保护中的相邻权冲突
由于自然遗产相邻权除了涉及经济利益外,还涉及到人身利益、环境利益,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自然遗产的保护要求保持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因此任何影响自然遗产生存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而自然遗产相邻的原住居民为了生存,需要利用自然遗产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例如需要打井取水、伐木生火、开采矿石、狩猎动物等,和对于有些原住居民,特别是土著居民,可能打猎和采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具体而言,自然遗产保护相邻权的冲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住居民资源利用与自然遗产保护区的冲突
许多自然遗产保护区建立在当地原住居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之上,他们在这里垦山种茶、采伐开矿、采药捕猎、挖沙取土,这些经济活动已成为原住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为了自然遗产,管理机构颁布了许多禁止性规定,例如《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禁止采伐、损毁保护区内的林木植被。”第十七条规定:“在保护区内,禁止开山、采石、采矿、挖沙、烧砖瓦、烧石灰,禁止围堵填塞河流、溪流、湖泊、山泉、瀑布,禁止采集化石、抽取地下水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地质地貌的行为。”为了保护自然遗产,这些禁止行为固然重要,但生活在武陵源地区的居民世世代代都是过着靠山吃山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这一保护自然遗产的法规是以牺牲原住居民的一定利益为代价的。原住居民的这些生活方式,在自然遗产保护规定颁布之前是合法的,而出于保护自然遗产的需要,这些行为却被法律所禁止,因此就这造成了双方的现实冲突。
保护自然遗产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是不是为了保护自然遗产就一定要禁止所有相邻原住民的相关经济活动呢?考察国外相关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些立法无一例外的禁止上述经济活动,但这些禁止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些立法都规定了例外的情形,即根据动植物的生长或生产周期,允许原住居民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特定的动植物物种进行采伐或捕猎。这一举措既保护了自然遗产,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原住居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就特定时间而言,以《美国阿肯色州自然保护区2009-2010狩猎规定》为例,该规定对捕猎的时间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在日出30分钟前,日落30分钟后,禁止任何打猎行为”,“禁止在4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利用猎犬进行打猎”,“禁止在3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对鱼类进行捕捉”。这些日期上的规定,都是根据动物的作息规律和生长周期来制定的,具有科学性,在立法上更具有指导性。就特定地点而言,该规定“禁止在距离城市或乡村边界150英尺内进行狩猎活动”,“禁止在距离住宅50码内进行狩猎”。同时该规定还制定了许可制度,即狩猎者必须拥有颁发的许可证,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将会被扣以相应的点数,例以在禁止期内使用猎犬将被扣除9点,捕捉濒临灭绝的物种将被扣除30点,而任何人如果累积扣除30点时,将被吊销许可证,并且3年之内不许重新申请。可以说这些规定,既保护了自然遗产,又满足了居民生活的需要,达到了双赢的目的。
(二)原住居民与自然遗产保护区经营权的冲突
由于自然遗产的权属大多归为国有,在经营方式上多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模式,虽然各国普遍采用承包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由私人来进行经营,但这些私营者往往并不是当地的原住居民,而来外来的投资者,甚至可能是国外的投资者。这些外来投资者的加入使当地的原住居民的利益受到了挑战,许多当地居民经营的旅馆、餐厅等经济实体面临着竞争,甚至排挤,当地居民非但没有从中获利,反而利益蒙受损失。以加拿大国家公园为例,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周边地区的旅游服务设施大多为外地商人投资修建,一些大型饭店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聘请外地人而非当地人,许多消费品一般也直接从外地采购。因此,当地原住居民不一定能从经营活动中获得期待的经济收益,国家公园周边旅游服务的经济收益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入到外地人而非当地人的手里①王连勇:《加拿大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以武陵源自然遗产保护区为例,1992年武陵源区主要街道武陵大道的40平方米左右的商业铺面租金不过3000元/月,随着外来投资的不断涌入,商业铺面的租金也随之越炒越高,1995年升至5000元/月,1998年升至6000元/月,而2003年刚升至8000元/月,许多当地居民对此价格望而生畏。
构成保护区与原住居民经营权上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同时拥有管理权与经营权,尽管管理机构经常采用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模式来进行经营,但势必会维护其所选定的经营者。保护区的管理机构与经营者实际上是处于同一个利益集团,与原住居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管理机构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其所选定的经营机构在经济实力上又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结果。相同的经营项目,保护区选定的经营者有很多的优惠,而原住居民则处于弱势,经营权的不公平,是自然遗产保护区与原住居民相邻关系冲突的一个焦点。
(三)原住居民与自然遗产保护区因搬迁而产生的冲突
在自然遗产被认定前,许多居民祖祖辈辈已经在此生活了百年,甚至几个世纪,而一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自然遗产,为了保护的需要,许多原住居民不得不面临着需要搬迁的境遇。这一情况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更为明显,许多自然遗产或备选的自然遗产都已经有人居住的历史,如何有效的解决原住居民的搬迁问题,是主管部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例如在泰国的Ranong红树林保护区②Ranong红树林保护区拥有一个面积达30000公顷的沿海红树林区和海洋生态系统,该区与两个国家公园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包括从山区生态系统到沿海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栖息地保护区。该区于1999年被列入生物圈保护区计划,它拥有75740公顷重要的红树林保护区,包括淡水和海水种类。,有3万多人口居住在该保护区周围,并环绕着保护区形成了农业区、渔业区和其他生产区,为了保护红树林保护区,政府下令要求部分居民进行搬迁。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越南Can Gio红树林保护区,居住在Can Gio保护区的人口估计有58000人,他们主要以农业、渔业、水产业和盐业为生,这些居民也同样需要搬迁。原住居民因搬迁问题而与当地政府产生利益冲突,使自然遗产管理部门无力招架。
更为重要的是,搬迁问题还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1.被迫搬迁的居民如何安置;2.被要求搬迁的居民的损失如何进行补偿;3.搬迁后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因为大部分居民都是以保护区作为生存基础,过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如果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或强制措施,非但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因此,搬迁问题应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通过有效的补偿机制来弥补原住民的损失,同时对于搬迁后的生活区建设应进行合理规划,对于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应进行帮助或有效引导,否则将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以北京潭柘——戒台风景名胜区为例,该保护区为了保护自然景观的需要,对部分居民实施了搬迁,在搬迁过程中进行了小城镇建设为主的安置措施,实现了城镇建设与自然遗产资源相协调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实行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先行,在改变农村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强调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对搬迁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引导,改变了原住民原有的生活方式。
(四)原住居民与自然遗产保护区因土地权属而产生的冲突
原住居民与自然遗产保护区的土地纠纷主要表现为权属不清。虽然大部分国家法律规定,自然遗产保护区归国家所有,但也有部分自然遗产保护区归集体或私人所有。例如美国的国家公园大多数属于国家所有,也有部分的自然保护地和历史纪念地为私人所有。在成立自然遗产保护区时,许多土地的使用权拥有者全部或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将这部分权利交给国家或地方政府,由自然遗产保护区管理主体代表国家或地方政府来行使管理权。由于土地权属的不清,在自然遗产保护区内又含有集体所有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又是由自然遗产的管理机构来行使的,这就导至了土地权属的纠纷。例如,广西贺州市滑水冲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与实验区山林权属为居民组所有,社区居民在区内进行种植、开矿、砍伐等活动,与保护区管理目标背道而驰,但在目前情况下保护区又无力制止。锡林郭勒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同样因为没有土地使用权证,以至于无法建立足够面积的核心区,保护区实际管理面积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7%。
而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野牛跳”自然遗产保护过程中,因土地权属产生的冲突却因为双方达成共识而化解。阿尔塔省的“野牛跳”遗址于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自然遗产的称号,该遗址的所有权归卡尔德伍兹和德尔斯奇斯两大家族所有。两大家族的族长认为,保护这些自然遗产是他们的神圣使命,因此他们不愿意开发这些考古资源。然而“野牛跳”对于研究土著人几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却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许多科学家对此很感兴趣。后来卡尔加里大学的考古研究机构向阿尔伯塔省政府提出建议,希望政府利用其宪法权力对该遗址进行保护。最后省政府同意了这一主张,并和两大家族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了共识,并颁布了相应的法案。该法案对两大家族的所有权进行了限制,使得“野牛跳”遗址在最大保护的前提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
三、自然遗产保护中相邻权冲突的法律救济
自然遗产保护中相邻权的冲突严重影响了自然遗产保护与当地原住居民的和谐发展,给自然遗产保护带来了很多的隐忧。自然遗产保护立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保护区与社区居民协调发展的问题①王曦、曲云鹏:《简析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之不足与完善对策》,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9期,第50页。。在国外的立法中,已有一些成文的法律制度可以用来解决自然遗产保护过程中的相邻权冲突。
(一)美国的妨害制度
在美国环境法领域中,妨害行为是最常见的侵权行为。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里的解释,妨害是是由于相邻人无根据地、不合理或不合法地使用其不动产或动产,而导致其他人的权利或公共利益受到妨碍,或因此而产生损害而带来实质上的不便、烦扰或伤害的侵权行为的集合。在种类上,妨害可分为公共妨害和私人妨害。两者区别的依据是所影响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当自然遗产保护区侵犯到当地原住居民的合法利益时,原住居民可以请求法院发布永久性禁止令或中间性禁止令来停止侵害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决定是否发布禁止令时,法院会将双方的利益进行比较来裁量。由于原住民受到的损失要比排除自然遗产保护区所造成的社会效用的损失要小,因此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原住居民要求发布禁令的请求,但在有些情况下法院仍会发布禁令。美国的一条基本理念是:如果认定存在妨害请求,一方当事人证明造成了重大损失,法院就应该批准禁止令①约翰.E.克里贝特等:《财产法:案例与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6页。。当原住居民的利益因为自然遗产保护区的建设蒙受损失时,如果要自然遗产保护区停止建设,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时如果颁布禁止令,显然在利益上无法平衡。因此在美国的妨害制度中,法院通常倾向于采用“代替性赔偿”或“部分排除侵害”等具有调解性质的新型责任制度,而允许继续经营,但前提是在不涉及重大生态环境利益和受害人生命健康的情况下,目的是为了尽量保护产业的发展,同时又不失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当相邻者为企业而并非个人时,可能双方的利益都是巨大的,牺牲任何一方都可能使其遭受巨大损失,在此情况下,保护自然遗产的公共利益显然要重于私人利益。例如,1978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根据《濒危物种法》的规定,最高法院为了保护濒危的蜗牛鱼而最终停止了已经耗费数百万美元巨资的特立特水坝工程。
(二)补偿机制的建立
无论是自然遗产保护区因经营权与原住居民产生的冲突,还是因搬迁权与原住居民产生的冲突,原住居民的利益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严重的损失。随着整个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遗产地的土地所有者和土地占用获利者之间因占地补偿的经济纠纷便不断产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②张晓等:《自然文化遗产对当地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载《旅游学刊》2006年第2期,第17页。。因此,应当在立法中,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来平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在美国的国家公园法律体系中,就建立了明确的补偿机制。在《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保护法》中规定:“当非联邦土地已经确定需要获取,管理局将通过各种努力与土地所有者在购买价格上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管理局将按照权威机构和国会对该单位的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但不论怎样,这种情况时应对土地所有者采取补偿措施。”同样,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相应补偿机制的建立,由于一些矿业开发公司在玉山国家公园瓦拉米地区进行爆破、修路等活动,影响了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持,破坏了生态平衡。为了实现保护国家公园的目标,确保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与矿区主管机构和矿主协调,依法将瓦米拉地区的矿区划定为禁采区,并对矿主进行适当补偿。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补偿机制,可以有效的弥补原住居民利益上的损失,化冲突为和谐、和解与合作,实现自然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力救济
当自然遗产保护区与当地原住居民因相邻关系产生纠纷时,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既省时又节约经济成本。然而,相对于自然遗产管理机构,原住居民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地位上都属于弱势群体,为了更好地保护其利益应赋予其公力救济的权利。
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的相关法律体系中,就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为美国公民维护其权利提供了一条公力救济的途径。该诉讼制度规定如果任何美国公民或机构,根据国家公园体系的相关法律,认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某项管理行动是错误的并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在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未采取行动,他们都可以对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提起诉讼。例如在保护红杉树国家公园(Red-wood National Park)的行动中,相关的利益团体认为该国家公园所做出的规定超出了其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权限,其禁止狩猎、捕鱼的措施违反了法律规定,牺牲了该团体的利益,于是该利益团体提起了诉讼。
四、解决自然遗产保护中相邻关系的新模式——社区参与管理
法律救济虽然可以补偿利益受损害者的损失,但都是事后救济,而且法律救济会消耗双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可能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僵化。因此,法律救济虽然可以亡羊补牢,但却不能防患于未然。近年来,欧美国家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自然遗产管理模式——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来对自然遗产进行经营和管理。社区参与管理是以社区的资源、需求和决策为基础的一种管理模式,是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所谓社区管理,即社区居民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到自然遗产的管理当中,形成政府、自然遗产管理机构和社区居民三方共同管理、互相监督的管理模式。而这一模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社区居民与政府、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社区参与管理试图实现三方利益的均衡,相互制约,避免矛盾和冲突的产生。
学者们也对这一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最多的是美国,其次英国和德国。在2007年召开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会上,也将社区管理作为一个主题进行专门讨论。社区管理模式试图在政府与经营者之间,寻求第三方利益主体的介入,从而约束政府与经营者的过度开发、忽视当地居民的行为。于是欧美学者开始构建了自然遗产保护区所在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经营模式,Martin Cihar and Jinriska Stankova将社区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 ,与政府、经营者等其它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害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社区居民是介于政府与经营者之者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①Martin Cihar,Jinriska Stankova.“Attitudes of Stakeholders Towards the Podyji/ThayaRiver Basin National Park in the Czech Republic”,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6,p.273~285.。Jeffery M·Sanders分析了纪念碑谷部落公园(Monument Valley Tribal Park)与钦利——绮丽峡谷国家遗迹(Cany de Chelly National Monument)在规划和管理上的不同。前者面向社区居民积极推行特许经营权,注重社区居民的需要,将社区居民纳入到员工的名册之中,而后者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②Jeffery M Sander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Monument Valley Tribal Park and Canyon de Chelly National Monument,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6,p.171~182.。Ryan L·Marone认为,社区居民接受管理措施的前提是必须让他们获得实际利益。William M·Adams and Mark Infiel讨论不同利益主体对自然遗产旅游项目收入的争夺,提倡将自然遗产旅游收入的一小部分分给当地的社区民众,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需求,弥补他们因国家公园创建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社区参与管理模式的产生使得自然遗产的管理在决策的制定、利益的分配、责任的承担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模式也对增加就业,解决原住居民与自然遗产保护区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冲突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