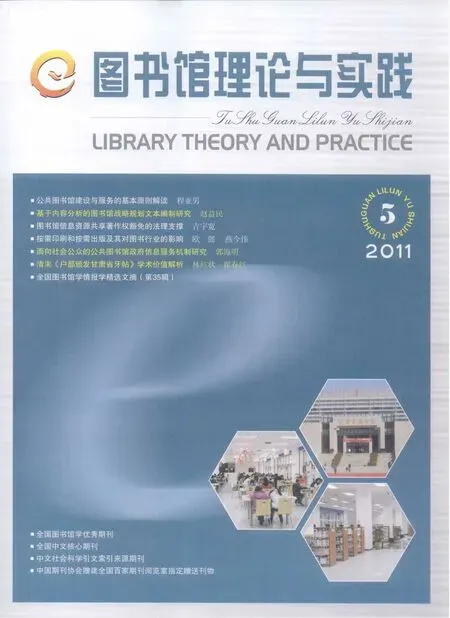浅论阮孝绪《七录·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影响
●傅荣贤(黑龙江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阮孝绪(479—536),字士宗,南朝梁人,生于“有遗财百余万”的世族家庭,以清高隐逸见称,淡于进取,悉心治学,遍通五经。阮氏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撰成《七录》十二卷,惜乎不传。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保存了《七录》的《序》,[1]从中可揭橥阮氏目录学思想之大概。
1 首次将目录作为研究对象
“依刘向故事”的我国古代书目往往都是某个具体“图书馆”的藏书目录,甚至是列入校雠对象的文献目录。例如,《七略》所收“六百三家”文献都是在刘向“每一书己,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的基础上,刘歆“总群书”而形成的分类目录。所以,虽然刘氏父子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十分崇高,但他们的书目只是以当时“中秘”实际所藏、且手自校勘的603种文献为著录对象,未能做到“范围方策而不过”“著录古今而无遗”,因而长期为学者所病诟,并形成了从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降历代延绵不绝的“补阙”之风。先校雠后编目的基本程序,使得我国目录学长期被认为只是校雠学的一部分,言目录必称校雠。而阮孝绪是我国历史上首位对目录本身展开研究的学者。《七录·序》云:“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他的《七录》是在对“名簿”和“官目”等其他书目对比和补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而不是以具体经手校雠的文献为对象或以某一“图书馆”的实际所藏为范围。因此,阮孝绪特别重视对书目本身的研究。
这首先表现在他十分重视对目录学史的梳理上。在《七录·序》中,阮孝绪论述了我国目录工作的源起和发展,从孔子整理六经述及刘氏父子校书编目、班固“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直到四部书目的产生和演化。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讨论了历史上各种主要书目之间的传承关系并分析各书目的特点及其得失醇驳。例如,《七录·序》曰:“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时之论者,谓(《中经》) 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为十有余卷而以四部别之……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因此,《七录·序》可视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目录学史著述。嗣后,《隋志·簿录序》等承绪其事,降及近现代的目录学史著作则日臻完善了目录学学科史的体例。
通过阮氏的《七录·序》,我们才得以对他之前的历代重要书目窥斑见豹、得其崖略。例如,《七录·序》指出:“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他认为刘向校书时为每一本书所写的叙录,当时是“皆载在本书”的;《别录》是将这些“皆载在本书”的一篇篇叙录另外辑出,汇集而成;《辑略》是《七略》中纲领性的总论。众所周知,《别录》《七略》皆亡佚于唐末五代,阮孝绪得以亲见其书,故其有关论述都具有根柢,值得采信。事实上,上述关于《别录》《七略》的基本观点,堪称定论久孚,迄今仍然是刘氏目录学思想研究中带有前提性的结论。又如,他认为《汉志》以降,“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并说王俭《七志》“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佛经、道经各为一录”;他还在《七录·序》的“古今书最”中指出:“《后汉·艺文志》书若干卷,八十七家亡。”说明袁山松的《后汉书》(今佚。现传《后汉书》为范晔所作)曾经仿拟班固《汉志》作有《艺文志》,这无疑是史志目录学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宝贵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古今书最”不是书目之名,而是指古今图书的总会,即图书总财产账。《说文》:“最,犯而取也。”小徐本:“犯取也,一曰会。”王筠《说文句读》曰:“此与聚同义。”《公羊传隐公元年》:“会犹最也。”总之,“最”意为“会聚”。因此,《目录学教程》[2]38等不少目录学著述误将“古今书最”视为书目之名是不对的。
其次,阮孝绪还首次将书目类文献列入《七录》的著录范围。他在《七录·纪传录》中首列“簿录”类,著录包括《七略》在内的各种“名簿”和“官目”计36种。这是我国“书目之书目”的最早见存,并成为《隋书·经籍志》在史部设立“簿录”类的先响。于兹而还,书目本身被著录于书目,成为我国书目的常式。同时,为阮氏所著录的36种书目,基本都是他“凡在所遇、若见若闻”的忠实记录,藉此,我们得以清晰勾稽我国前此书目编撰的大致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目录学史料价值。
再次,阮氏还首提“流略”之学。《七录·序》说:“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后人之称传统目录学为“流略”之学,即源于此。
2 阮氏目录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具体而言,阮孝绪目录学的思想主要聚焦于著录和分类两大方面。
2.1 著录思想
首先,目录应该通记天下有无图书。
我国书目大多是针对当时实存文献(甚至实藏文献)而形成的藏书目录,但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通记古今、不遗亡佚、全面记有,个性十分鲜明。现代学者一般都以“通记天下有无图书”为郑氏目录学思想的一大特色。[2]87-96然而,《七录》 才是我国历史上已然确知的首部立意“通记天下有无图书”的书目著作。据《七录·序》,阮氏通过自己多年“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的努力,其《七录》以“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和“不足编于前录而载于此”为职志,在文献著录的数量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七录》一书实际著录之书凡55部(子目)6288种,“自有目录以来,要以阮氏此书,最为繁钜”。[3]可以肯定,阮氏不仅在观念上、同时也在实践上努力践行“通记天下有无图书”,无疑是郑樵“通记”思想的先响。
其次,最早产生“国家书目”乃至“书目控制”的思想。
阮氏疏淡于对一本本具体文献的校勘,但特别重视对当时“全国”文献总财产的勾沉,这集中反映在《七录·序》所条列的“古今书最”中。“古今书最”共罗列从“《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到他自己的“《七录》内外篇图书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共11种书目的图书总数及其存亡情况。然后,再具体罗列其《七录》所分七大类五十五小类的类目名称及各类文献的种数、帙数、卷数及图画数量。应该说,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国家书目”乃至“书目控制”思想的最早源头。
再次,最早著录图书存亡。
阮氏在总计文献总财产的同时,还注意著录存亡,如上所引《七略》“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即是其例。就目前史料来看,《七录》也是我国已然确知的最早著录图书存亡的书目。这其实是要在统计文献总财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曾有”财产和“现有”或“实有”财产,对《隋书·经籍志》等后世书目著录图书存亡、统计文献“曾有”和“现有”或“实有”之举不无影响。
最后,重视对图书聚散的讨论。
正是基于对图书实际存佚情况的重视,导致他在《七录·序》中着墨于对历代图书聚散的讨论。可以认为,隋人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正是在阮氏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五厄论”的。事实上,阮氏《七录·序》所谓“蠃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存一”等文辞,也直接为牛弘所袭取。
2.2 分类思想
《七录》的最大特色反映在它的类目上,“所析子目,为后世目录所遵循”。[4]不仅如此,《七录·序》从“斟酌”此前的一些重要目录(尤其是《七略》和《七志》)的类别入手,展开对书目类名、类别等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成为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研究分类的理论文篇。
首先,责实定名,用当时最为科学的方法讨论了类名的确立原则。
虽然阮氏基于当时的学术规范,尚不能从纯粹逻辑的角度给书目中的每一个类名以确切的定义,也不能自觉遵守逻辑学上“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上位类名和下位类名之间必须是严格的种属关系”等科条,但他却是第一个真正讨论分类类名的内涵及其使用合理性问题的目录学家。他说:“今所撰《七录》,斟酌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阮氏这段文字,本旨在解释其《七录》分类类别及类名之所由,但他“斟酌刘王”,成为现存最早研究《七略》和《七志》分类类名的文献。总体而言,他讨论的最终目的是要“于名尤显”,并认为书目类名“名”与“实”之不符,既包括类名与文献“客观”事实的不符,也包括因类名所附带的价值判断而造成的“主观”不符。换言之,类名除了字面含义,还引起人们主观心理的不同反应。相应地,“不正确”的类名既有认知判断问题也有价值判断问题,既有语言自身的问题也有语用实践的问题。在不断校正与调节类名“能指”和文献“所指”的统一性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到文献的“真实性”和社会伦理的“正当性”。
与责实定名相类似,阮孝绪还倡导根据文献的现实地位和社会影响来确立其类别位置。例如,《七录·序》说:“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伎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这里,与王俭《七志》相比的两点变化是:第一,《七志》之“七”不包括佛道二目而《七录》之“七”是包括佛道二目的;第二,《七志》先道后佛而《七录》先佛后道。这是由佛道类文献的当下地位及其现实合理性决定的。
其次,最早提出类似今天“文献保障原则”的分类思想。
《七录·序》指出:“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阮氏认为,《汉志》以史书附于春秋家盖因史籍奇少;诗赋略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等等,无疑是今人以“酌篇卷之多寡”[5]作为《汉志》分类原则的最早思想源头。总体上,目录系统是为整理文献进而整序文化服务的,目录系统的基本面貌应该取决于文献发展的具体状况。用姚名达的话说,就是目录分类法“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在乎能适应当时的著作界”。[6]当然,从“古今书最”所列《七录·传纪》等类目来看,其“酌篇卷之多寡”的分类原则未能充类至尽。例如,墨家仅4种文献、阴阳家和农家都仅有1种文献、纵横家仅2种文献,但阮氏仍列有墨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等类名。
再次,其“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的观点是郑樵重视图谱思想的先导。今天的文献分类和目录编制大多包括图谱,阮氏认为“图谱宜从所部”,即将图谱文献直接和相关文献一起随部入类,其识见要比郑樵《通志·图谱略》将图谱单独立出为高。
3 结语
阮孝绪的《七录》我们今天只能在《广弘明集》中见到其简略的序文和它的分类目录框架,但它却开启了我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研究之先河。其序言的研究内容,诸如分类和文献发展的关系、类名的选择和分类系统的原则等,一直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主体内容。郑樵“类例论”、章学诚“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观,都可导源于此。同时,阮氏的理论思考立足于对前人(如刘氏父子、王俭)目录学思想的评论,在此基础上有所批评折衷,并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这种基于评论的入说方式,成为自此以降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启发后人良多。当然,《七录·序》对书目的提要和序言几乎没有任何讨论,这使得他在我国目录学研究史上虽有荜路蓝缕之功,却有未臻完备之憾。
[1](南朝·梁) 阮孝绪.七录·序 [C]//(唐)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M].四部丛刊本.
[2]彭斐章.目录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胡楚生.中国目录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66.
[4]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132.
[5]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9.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41.
——以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课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