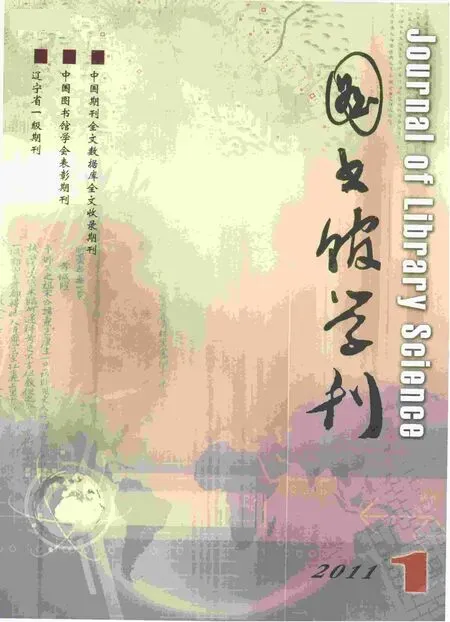毛泽东与图书馆之缘——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马晴云
(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1 少年励志,利用图书馆奋发读书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读过几年私塾,精明能干,克勤克俭,善于经营,但是性情暴躁,教子苛严。母亲文七妹,慈爱善良,为人慷慨厚道,常接济别人,毛泽东十分敬重母亲的品德。
当时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统治到了末年,又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这个一度辉煌的古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国弱国,内忧外患交加,社会危机四伏。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强,寻求独立自由民主的道路,前仆后继,奋斗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但是人们所作的努力都失败了,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长大的。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山川秀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先秦时期这里是荆楚之地,唐宋后得以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逐渐繁荣起来。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特别是宋以后,兴教崇文,形成了以变革、重才、图强为核心的湖湘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或影响的人物,如魏源、王夫之、谭嗣同、黄兴、蔡锷、左崇棠、曾国藩等。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对毛泽东早年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2年春,毛泽东8岁开蒙读书,到13岁在韶山先后就读过6所私塾。读了《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四书五经,他是一个聪颖好学和机智顽皮的孩子,给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自述里说过:“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系完全不识字……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我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又说:“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的父亲很生气,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机器——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想恢复学业的愿望。”
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恢复了学业,在私塾里他选读了《史记》、《汉书》、《纲鉴类纂》等古籍,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终于说服了父亲,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从此,他离开了韶山,走向了外面广阔的世界。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母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小学堂之一,毛泽东是慕名而来。他的入学作文《言志》因为志向远大、文句优美而得到了校长李元甫的赞扬,他高兴地说:“我们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李元甫是一位新式知识分子,在他的主持下,学校革新了课程,除教经书外,还增设了自然科学、中外历史、地理、英文、音乐等课程,并新设一个藏书楼。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个图书馆——东山高等小学堂藏书楼。这使毛泽东大开眼界,每天都来这里,除读中国古代史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尤其是《新民丛报》。这份杂志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主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他读了又读,并作了很多批注,其中有些文章都能背下来。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书,因为他年龄较大,学习成绩又好,校长、老师鼓励他去长沙考中学继续深造。1911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东山小学堂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
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长沙城革命气氛极其浓烈,一位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讲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毛泽东异常兴奋,决定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一名列兵。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毛泽东以为革命成功,便退出新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后来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里,由于他爱好文学,作文《商鞅徒木立信论》受到国文老师的高度赞赏,批示“传观”,还说:“历观生作练成一绝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所至。”他读完从老师那里借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之后,激起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他觉得在学校学习课程有限,校规陈旧,不如自学。1912年秋便退学,寄居在长沙湘乡会馆。每天步行3里多路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青年毛泽东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基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等。为了争取时间多看书,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天开馆他总是第一个进去,晚上闭馆他最后一个出来。毛泽东在自述中讲的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时说:“就像牛闯进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一样。”他提出“改造中国”的口号,决心要为中国痛苦、世界痛苦人服务。
由于父亲拒绝继续供给费用,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继续学习。1914年2月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八班。第一师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就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荟萃着一批思想先进而又学识渊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等,也是湖南先进青年向往的学府。图书馆藏书丰富,订购了当时流行的20多种杂志。毛泽东非常珍惜时间,再次把重点放在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自学上。1915年《新青年》创刊,在杨昌济老师的推荐和影响下,毛泽东成了它的热心读者,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学习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时,他在课本上写了12000多字的批注,阐述对原著的见解和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用他的话说:“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深得杨昌济的喜爱。在这里,毛泽东读了4年书,直至1918年6月毕业,这时的毛泽东已经25岁了。
2 刻苦读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接到杨昌济教授从北京的来信,叫他去北京大学学习,并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召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像磁石般吸引了很多立志报国的青年人,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年8月,他和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应该说,从韶山到长沙,是毛泽东人生中迈出的一小步,而从长沙到北京,则是人生中的一大步。
北京大学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又是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这里荟萃着一大批知识精英,在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各种思想争奇斗艳。校长蔡元培倡导学术思想“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方针。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的生活十分困苦。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去找杨昌济帮忙。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这样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获得一份期刊阅览室的工作,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清理书架,打扫卫生,登记阅读者的姓名。这不仅解决了他的必须生活费用,还能阅读各种新学说的书刊,广泛地接触名流学者。他结识了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以后他还见到了当时心中的“楷模”,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毛泽东后来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他带着许多新思想、新经验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5月4日,北京爆发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席卷全国,形成了强大的反帝爱国风潮。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毛泽东和湖南学生代表坚决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新的湖南学生会,发动学生罢课,积极响应五四运动,主编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在创刊宣言里,他兴奋地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澎湃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他在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中,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呼吁中国来一个“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经过五四大潮的洗礼,毛泽东成长为湖南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3 建立图书馆,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社会上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写道:“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经营百余种图书、40余种期刊和进步报纸等。
同年8月,毛泽东利用原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设10多个专业,主要学习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及马克思主义文献。提倡一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方面从事劳动和工农运动,为建立湖南中共组织培训干部。自修大学先后培养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夏明翰是其中之一。这为建党从组织上、思想上创造了条件。同时整顿了原船山学社图书馆,改为大学附设图书馆。添购了大批书刊,订立《借阅书籍规则》、《书报阅览室规则》。编印馆藏书目,藏书1004册,421种;另有私人寄存图书近200种,600册。其中数量颇丰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政治书籍,如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以及《新青年》、《新潮》、《觉悟》、《共产党》等,供学员自修阅读。当时的科学家、教育家蔡元培看到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在上海《新教育》期刊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赞扬自修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论相合”。
1922年,毛泽东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馆藏图书有介绍西方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西洋伦理学》、《资本论入门》等重要书籍以及进步报刊《新青年》、《劳动界》、《新教育》、《晨报》、《时事新报》等。成为进步青年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1931年,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巩固并扩大了中央根据地,当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主席。会后,毛泽东找到当时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经两人协商,在叶坪村找到两间房办起了图书馆,由徐特立负责筹办。这就是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并带头号召机关、团体和个人向图书馆赠送书报。苏维埃第一次大会以前,每次打下一个城市,他都要去图书馆收集资料,书报收集的越来越多,他让警卫员分类打包背着,大包则让马驮着,这是战士们流传的马背图书馆。苏区中央图书馆成立后,毛泽东除留下自己需要的书刊资料,其余的全由图书馆收藏。
1932年以后,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排斥,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专做政府领导工作。曾志在回忆时说:“我已于1930年调白区工作,当时奉命从厦门来到漳州。我们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住处下面的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所漳州龙溪中学。那时学校停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回家了。一天主席对我说:‘曾志,走,我们到那所中学去看看。’这所中学是漳州有名的中学,校舍很宽敞,尤其是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装着满满两个房间的图书。毛主席到了图书馆,喜形于色,他一本一本地翻书,越翻阅越兴致勃勃,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说:‘曾志,帮个忙,去找几个箩筐来,我要找些书籍带回江西去’。我和勤务员找来了三四个箩筐,毛主席仔细挑选,我们就把挑出来的书往箩筐里放。毛主席在学校的图书室整整翻阅了一个上午,找人挑了两担箩筐的书借回住处。据说他后来还去过该学校两趟,回江西时带回了许多书。
身在逆境中的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增长知识,积累实践。在1957年他同曾志回忆这段艰难的经历时感慨地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过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的就找同志们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读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的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1937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后,生活条件相对稳定了。在瑞金苏区建立的图书馆,如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在长征中,大部分文献资料都失散了,正属于恢复时期。为了满足领导机关和干部读书的需求,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致电中央,建议成立流动图书馆。1936年9月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失散。(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这是毛泽东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极珍贵的一份历史文献。当时在每个连队和每个团都有列宁室,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收藏的图书是中国红军教科书和讲义,俄国革命史,各种从白区偷运进来的杂志以及中国苏维埃出版物,如《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等。陕甘宁边区几个图书馆成立时,由于缺少经费,购书来源也很紧张,毛泽东将每月50元生活费节省下来,4次赞助鲁迅图书馆的扩建、中山图书馆的新建、延安女子大学图书馆成立和边区医院成立,并为扩建后的中山图书馆题写馆名,将自己珍藏的书多次捐借给图书馆。
毛泽东不管在逆境中,还是在戎马倥偬、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从不放松读书学习和理论研究,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地结合,那就是“实事求是”。每天他要批阅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并作出批示与部署,然后在窑洞里昏暗的灯光下读书或写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许多具有丰富革命实践和理论的著作和文章,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理论,指导了中国革命。他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4 北京图书馆一号借书证
建国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还是挤出时间读书学习。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吃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二日不读。”据逢先知介绍:“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难以实现,后来实际也没做到。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他的藏书已达到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自己需要的藏书室。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部分)、《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就个人藏书不算少了,但仍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还经常向一些图书馆借书,如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图书证,给他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出于对他的敬重,把借书证编号为一号,并配专职人员值班,24小时为毛泽东办公室和中办办理借阅事宜。据不完全统计,仅1974年在北京图书馆和其他馆借阅书刊共计1100余册。”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还是博学多才的诗人、书法家和学者。他一生读得最多的还是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在他读过的书籍上,留下了许多精辟独到的批语。到了晚年,患了眼疾,视力减退,这对一刻也离不开书的人是件多么痛苦的事。他用稿费把书印成大字体,配上放大镜阅读。为了让毛泽东侧卧时看书不感到不便,工作人员给他定做了两副单腿眼镜,右侧看书时,就戴上没有右腿的眼镜。他一生嗜书,无论在艰难的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到外地工作视察以及在深居简出的晚年岁月,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书,始终是他最亲密的伴侣,就是在重病卧床期间,仍坚持阅读文件和书报。实在不能看时,叫别人读给他听。书,陪伴他一生,直到生命的尽头。
[1]张素华,许雪.毛泽东画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3]周德辉.湖南省志·文化篇.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