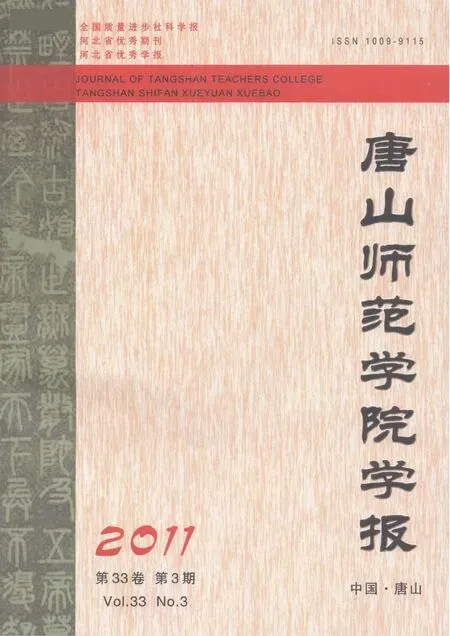张悦然论
喻晓薇
(武汉工业学院 人文系,湖北 武汉 430023)
张悦然论
喻晓薇
(武汉工业学院 人文系,湖北 武汉 430023)
本着对一个有潜力的文学新人负责的态度,细读其文本,将其置于文学史座标系中来考察,会发现张悦然的小说属于主观型创作,诗化小说;其小说存在明显的唯美主义追求,且充满魔幻与灵异色彩;从女性文学角度来看,其作品是典型的女性文本,具有女性的阴柔极致之美。
张悦然;诗化小说;唯美主义
一直以来,张悦然作为创作者的意义只被视为归属于“80后”、青春文学这样群体性存在的意义中。而在许多持文学是“成人的事业”[1]的研究者看来,“80后”、“青春文学”只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①,其创作就文学价值本身而论相当小儿科,不值一提。于是,张悦然作为创作个体的个性和价值在人们对“80后”、“青春文学”不以为意的态度中被忽略。
且勿论这样的文学观是否合理,单就将一个有个性有潜力的创作个体贴上“80后”、青春文学的标签,淹没于群体中的做法本身而言就是相当随意和不负责任的。持这样观点者恰恰鲜有对张悦然的小说进行认真研读,大多先入为主,凭借从一些渠道获得的印象、观念,对其文本进行有选择有针对性的阅读,由此对张悦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加挞伐。如声讨其创作小资情调倾向,将其命名为小小资文学[2]。再如声讨其创作“经验匮乏”、“病态冷漠”、“无历史担当,无现实意义,无理想追求”[3]。
勿庸置疑,张悦然是属于“80后”这个代群,其创作题材也多是取自于自身的青春经验,因而其作品也有一些属于这两个不同标准划分的群落的特征。但作为“80后”迄今为止最为优秀和最有前途的代表②,张悦然作为一个创作个体的价值已逸出“80后”写手的群体性意义层面。如果仅止于从“80后”和“青春文学”的层面来泛泛而论其创作,这样的研究只能算是相当浅表层次的。
据此,在进入张悦然的文本前,本文将禀承对一个有潜力的文学新人负责的态度,悬置已有的对张悦然创作的种种结论和看法,以还原现象的学理态度,对其全部创作文本进行细致研读,力图深度开掘张悦然的小说世界。
一、主观型创作——诗化小说
一般而言,文学史上有两类气质的小说家和与之相对应的创作:一类作家主体自我无限“缩小”,眼光外扩,热衷于观察、描述外部客观世界,讲述别人的故事,我们称之为外向型创作或客观型创作,比如以社会剖析小说闻名的茅盾就是典型的外向型作家;一类创作主体自我意识强烈,眼光向内,关注自身心灵世界,即使是讲述故事,描写外在于主体的环境氛围都习惯于将其浸透在主体的情绪、心理中,我们称之为内省型创作或主观型创作。这一类作家的代表有创作出了系列“自叙传抒情”小说的郁达夫,以对故乡童年往事抒情而著称的沈从文、废名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悦然作为创作主体的气质类型显然属于后一种,其小说是典型的主观型小说。翻阅张悦然的作品,从“新概念”时期的《陶之陨》,到留学新加坡时期的《葵花走失在一八九Ο》、《十爱》、《红鞋》、《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及至近期的《誓鸟》,我们发现,作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反反复复、从不同角度讲述一个少女的情绪体验和经历(尤其是前者——情绪体验,而后者——经历或故事性的成分常常是融化在这种情绪体验中的)。这个少女在文本中常常是以“我”或“她”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化身为“他”或“它”③,不变的是青春期的女性情绪、心理特质——感性、细腻、敏感,对某些形式细节的酷爱乃至于沉迷,耽于想像,富于梦幻和艺术气息。不必说《陶之陨》、《黑猫不睡》、《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这样的故事中有与创作主体身份年龄气质相仿的少女主人公的小说,即便是在她为数不多的欲突破少女视角的试验性小说中,我们也能够找到这种少女心理特质的印痕。短篇小说《船》故事的主体部分是一个中年男性“我”对宝宝讲述20年前杀妻然后趋车去海边毁尸灭迹的经历。在“我”对自己把尸体运到海边,载入白木船并推向大海深处的男性视角叙述中,穿插跳跃在情节间并推动情节行进的是对卡车、公路、悬崖和海边等环境氛围的相当篇幅的描述,而这种描述浸透了诗性眼光,散发着女性气质:
杂草在这片热带地区异常茂盛,它们从根部就紧紧地纠缠住花朵,像是在求欢[4,p72-74]。
海在一个黄昏的雨水里辗转反侧。这是一片很少被打扰的海,她在多数时候可以随时进入梦乡。她进入梦乡的时候,海潮看来并不强大,可是迂回曲折,零星的梦魇星罗棋布。她非常喜欢在下雨的时候睡过去,她让她的波浪任由凶悍的狂风雨水摆布,她喜欢她自己看起来更加具有母性的温情。[4,p101-102]
李子红色的裙子在海水里像一块粘稠的血迹一样氤氲开来。驶向海中央的时候,船忽然像获得飞行的鸽子一样快乐。其实礁石有最柔软的怀抱,你们谁也不知道。[4,p103]
我们有理由将这看作是作者欲突破主观型叙述视角所做的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张悦然是那样迷恋这种梦呓似的女性化叙述情调,以至于不惜一次次从男性视角下逃逸,滑向她所热衷也是最擅长的诗意化的少女视角。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张悦然无法走出她主观个我的情绪心理世界。
这诚然是一种局限,但从积极面来看,对于一个青年作家而言能把自己内心世界演绎到极致何尝不是一种风格。沈从文在创作中始终纠结着湘西情结,郁达夫执着于书写“于质夫”们的世界,在文学史上都独树一帜。
与主观型创作相伴生的是小说的诗化特质。张悦然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亦不以人物取胜,位居小说中心的是梦幻气息十足的情绪、情感或虚化的意念。有时这种独白式或倾诉式的抒情纵贯了整个小说,而故事情节则被打散成碎片点缀于其中,并且这些碎片情节也被氤氲在情绪、情感的雾气中,变得极淡。譬如《领衔的疯子》、《心爱》、《赤道划破城市的脸》、《痣爱》、《这些那些》这些纪实性较强的小说根本没有一个人物或完整的事件贯穿始终,全篇弥漫的皆是对过往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缅怀与眷念,从某种角度看就是抒情散文或诗。而在那些有完整情节和纵贯始终的人物的小说中,我们也发现梦呓似的情绪情感或意念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并成为推动情节进展的重要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篇小说《誓鸟》。小说构筑在遥远而庞大的历史时空背景上——明代大航海时代,从中国大陆跨越南太平洋的几大岛屿。作者采用倒叙、插叙、多视角手法来讲述,力图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磅礴大气的厚重感。其实细读文本,情节很单纯:中国少女春迟远嫁南洋,遇海啸丧失记忆。为了找回记忆和爱情,她走上了搜集贝壳,从中寻找藏有自己记忆的那枚贝壳的艰辛旅程。单凭着找回记忆这个意念,她经历了身体残缺、生育以及牢狱之苦,最终成为了一个拥有无数记忆的“最富有的人”。小说情节的根本渊薮来自于一个神话传说——丢失的记忆可以从贝壳中找回:“在南洋一些土著部落里,人的记忆被视为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它们可以脱离肉身存在。更有一些传说,认为贝壳里藏着记忆。”[5]春迟对记忆的执着追寻成为小说主要情节前进的根本动力,主宰着小说的是对一种超离于世俗生活之上的虚化的精神追求。小说骨子里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属诗的。
二、唯美主义文学——魔幻与灵异因子
他们看到一个稚气未脱的美貌少女的身边堆满了肢解的动物,拧断脖子的鸡,掏干净五脏的麻雀。还有鸡血写下的字,插满骨头的雪堆。她手上还拿着巨大的铲子,铲子上有慢慢凝结的动物血液。因为有些冷,她的脸蛋冻红了,宛如一簇愈加旺盛的小火焰[4,p207]。
这段文字是张悦然作品中引用频率较高并且得到质疑较多的。质疑焦点集中在以下两点:其一,这种冷酷血腥的描写具有非道德化倾向;其二,小说并未揭示少女病态行为的形成根由,仿佛天生如此,所以这种描写是封闭性的,没有现实指向性。
暂且悬置对这种描写倾向的褒贬,笔者认为这种非道德化和没有现实指向性的封闭性特征正是唯美主义的表征。唯美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风行于西方的一股文学思潮,其重要代表是英国作家王尔德。他信奉艺术至上的纯艺术理论,声称自然和生活是丑陋的,唯一美只在于艺术,艺术是高于一切的美,并且主张艺术是非功利、超道德且纯形式的。《红鞋》中的女孩的特征是冷和热的截然对立:一方面对世间一切的冷漠甚至于冷血,冷血到对杀害自己母亲又养育自己成人的杀手养父无动于衷,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另一方面,热衷于美的形式,乐此不疲地制造新奇刺激的行为艺术,诸如将一只白猫拔光牙齿,五花大绑,再刷上花汁,将它变成紫红色;一次次从养父身边逃走,制造被人绑架的假相,然后再等养父筹足钱找到她,将悠然沉醉于新的美的场景制造中的她一次次地“赎回”……。这简直就是托身在中国当代的“莎乐美”。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新文学中是极其罕见的。
再细读张悦然的小说,我们发现唯美主义倾向的确非常普遍地存在于张悦然的作品中。几乎她所有小说都活跃着一些艺术家或具有艺术气质的人物:他们执着地追求艺术或某种美的理想,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自毁或毁掉他人;但是,他们的追求和由此生产的自由精神与世俗生活又是格格不入的:在世人眼里,他们行为怪异,是疯子。譬如,《水仙已乘鲤鱼去》中天才作家丛薇狂热追求艺术,向往自由生活,但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受挫,失恋、酗酒、吸毒、早产,以至疯癫,最后纵身大火。《葵花走失在一八九〇》中的文森特是油画《向日葵》的作者——19世纪的荷兰画家梵·高的化身——那个毕生献身艺术患有精神病的艺术家。《谁杀死了五月》中少年成名的少女作家为追求“文学深处的桃花源”离家出走,在一个江南小镇邂逅摄影师三卓,两颗追求艺术的心灵交汇,碰撞出火花,他们迅速相爱并发生关系,然而为了维护各自艺术追求的完整性,女孩再次出走离开男人……张悦然通过这些艺术家或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物的追求构筑了一个绝少人间烟火气息的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不指向现实,而指向艺术和美。
对美的追求与伦理道德追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当在追逐美的道路上走入极端深处时,就往往会置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于不顾,产生非道德化倾向。所以唯美主义与去道德化倾向往往唇齿相依。这也正是人们不明白张悦然小说中何以存在“虐酷”倾向的根源所在。
唯美主义是五四时代随西方众多思潮一起涌入中国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方国情不同,唯美主义传入中国后产生很大变异,与原盛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有很大区别。学者王光东在《美的诱惑与变异——中国新文学中的唯美主义》一文中指出:“……他们(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解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换句话说,在王尔德那里他所要求的是要生活模仿艺术,而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所要求的则是以艺术来改造和美化社会,同时反抗社会对自我的压抑。”[6,p105]这就使其作品中的唯美追求具有极明显的现实指向性。而中国现代作家“对现实时代精神的重视,又使他们以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亦即善的力量,净化了唯美主义作品中所谓‘非道德’的肉体享乐的内容,表现出他们在美的追求过程中对于‘善’的重视。这种转化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中国浓重的实践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却也在无意中淡化了自己的个性强力意志。”[6,p106]事实上,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和中国人文传统中的强大实践理性精神影响,从建国以后一直到80年代,在中国都没有产生纯粹的唯美主义创作。
与前辈作家相比,许多“80后”作家们的成长环境倒是更接近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产生的土壤。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物质条件的优裕,更容易导致他们精神追求的纯粹性;而全球化的成长背景使他们更易于与西方思想接轨。张悦然毫无疑问就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所以有理由相信,张悦然小说中唯美主义追求是相对比较纯粹的,是更接近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这样的唯美主义文学也使中国文学的唯美主义追求更多地具有了文学自觉的价值。
唯美主义者既然主张最高的美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虚拟的艺术中,当然就会用一切非现实主义的手法,如想象夸张变形等虚构手法来构筑这个超凡脱俗的世界,这就是王尔德所谓的“说谎”的艺术。我们看到,有着超凡想像力的张悦然把这“说谎”的艺术操练得那样的飞扬灵动。在她笔下,幽灵飘忽游荡,自由来去,去人间寻找他们生前的恋人(《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二进制》);鬼魂的头可以从身体上分离,飞行于夜空中,象鸟一样栖息在树枝上(《宿水城的鬼事》);记忆吸附在贝壳里,被灵敏的手触摸阅读(《誓鸟》);一小女孩心口疼痛,另一小女孩也同时感知(《樱桃之远》);一株葵花爱上了画家,变成一个女子追随心爱的人直到死(《葵花消失在一八九〇》);小白骨精一根根抽出身上的雪白骨头奉献给乐师丈夫创造世界上最伟大的竖琴(《竖琴,白骨精》)……或从经典童话中吸取养分,或从中国民间神话和鬼怪故事中寻找资源,或从灵异电影中激发灵感,加以自己非凡的想像力,整合、创造,所以呈现在张悦然小说中的世界是唯美的,又富于魔幻与灵异色彩的。
三、女性文本——阴柔极致之美
说到当代的女性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在写作中作家性别意识淡薄,以无性别化的中性姿态存身于文本中,这种女性写作姿态普遍存在于1990年代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出现在文坛前,比如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等都是以中性化写作著称的作家;还有一种是在写作中,作家惯于从女性独有的区别于男性的心理特质出发,以女性的眼光描写女性独特的经验、心理,因而其文本呈现为突出的女性化特质,典型代表是林白、陈染。
在一篇访谈中,张悦然曾坦言对林白作品的共鸣:“另外一类作家或许作品并不完美,或许从未被那么多的读者关注,却格外地打动我,因为她的作品中有我特别关注或感同身受的成分,比如林白,我对她的作品相当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作品中有许多梦幻般的超现实场景,她的这种‘女性写作’说出了好多女性感受。”[7]或许是受林白的启发,或许是两人写作气质不谋而合,总之林白的“女性写作”对张悦然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比起林白等女性前辈们躲在帐中、关在房中的女性言说方式,张悦然显然更多了几分坦然,她在小说中毫无避讳地挥洒着她身为女性写作者的优势:长于直觉感悟,善于体察细节,关注内心情感远超过外部世界,富于梦幻性的倾诉直白式的言说方式,叙述结构上的诗化散文化特征,语言的形象性和画面感。当然这样极端女性化的写作姿态也造成另一面的缺失,譬如论者经常诟病的对驾驭宏大场面的力不从心,小说结构零散化,缺乏逻辑性,视角单一。这也正是女性文本的一体两面了。
这样的笔致下绘就的世界,一如张悦然在一篇小说中所写到的:“我承认我一直生活得很高贵。我在空中建筑我的玫瑰雕花的城堡,生活悬空。我需要一个王子,他的掌心会开出我心爱的细节,那些浪漫的花朵。他喜欢蜡烛胜于灯,他喜欢绘画胜于篮球,他喜欢咖啡店胜于游戏机房,他喜欢文艺片胜于武打片,他喜欢悲剧胜于喜剧,他喜欢村上春树胜于王朔。”[8]在这个执拗地将篮球、游戏机房、武打片、喜剧和王朔等坚硬的男性化事物拒之门外的“玫瑰雕花的城堡”中,张悦然精心地构造着她温柔绵软潮湿感性的少女世界。这是一个纯粹女性化的世界,唯一准入的男子——她心爱的王子,是水草般的阴柔,睫毛上粘着蔷薇花粉,干净得没有影子(见张悦然小说《毁》,她写道:影子是人间的尘垢结成的痂)。这也是一个圣洁的灵的世界,少女和她的天使王子因为对艺术对美的共同追求而相爱,她们的爱情是清洁的精神之爱,肉身之欲是令人却步的。
这个阴柔的世界又具有一种极端偏执的特质。这主要源自于女性主人公身上的一种执着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往往是爱情。她的许多小说,比如《霓路》、《竖琴,小白骨精》、《葵花消失在一八九〇》……都隐含着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的故事内核:女孩为了心爱的王子,心甘情愿地追随之,无私付予,甚至可以付出生命。而且这种付出不带任何勉强,正如珍妮对皮诺曹所说:“皮诺曹,我现在终于懂得爱情的真谛是什么了。是甘愿。人一旦甘愿地去爱一个人,就会万分投入地去为他做所有的事情,并且感到幸福,永远也不会后悔。你不觉得这样的情感很美好吗?”[8]深入地看,与其说是少女们为她心爱的王子而付予,勿宁说她们为自己的爱而付予。她们享受自己的这种情感,无关乎男性是否同样施予爱;她们享受为自己的情感无私付出的过程,无关乎结果如何。而她们的生命意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彰显。所以一旦她们认定她们生命中的男人时,便义无返顾地奔过去,奔过去,没有丝毫犹疑……正如一部女性电影所传达的思想:“我爱你,与你无关。”这样的主题在张悦然的近作《誓鸟》中得到了更充分地展现。女主人公春迟丧失记忆后,遇到她的王子——骆驼。骆驼只以一个小小的藉口便轻易抛弃了她:“因为你把从前的事都忘了。我待你的好,我们有过的好时光,你都不记得了。这在我看来是不能原谅的事。”于是为了骆驼给出的那个虚无飘渺的承诺——寻找到记忆再来找他,春迟踏上了漫长的追寻记忆之路。她刺瞎了双眼,钳掉了指甲盖,走遍南洋搜寻贝壳寻找记忆,什么也阻挡不了她的脚步。实际上骆驼的爱情、骆驼的承诺只是一个契机,在春迟追寻记忆的过程中,它淡化到几乎没有,而弥补缺失的记忆,寻找完整的生命,最终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才是春迟所有极端行为的内在根源。
[注释]
① 2006年,在《誓鸟》首发会上,张悦然曾宣称:“希望媒体不要再把我归类于‘80后’,我的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学的樊篱,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这部作品正是我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
② 2005年,张悦然获得由人民文学社主办的“春天文学奖”。2006年,她的长篇小说《誓鸟》并被评为“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最佳长篇小说”,标志着她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一名“80后”写手向主流纯文学作家的转型。2007年5月,张悦然签约北京作协,正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撇开文学以外的因素不计,张悦然已成为“80后”这个群体中走出的成就最斐然、最有潜力的一位。
③ 前者如《船》,后者如《残食》中的鱼妻、《宿水城的鬼事》中的无头女鬼、《坚琴,白骨精》中的小白骨精。
[1] 张柠.青春小说及其市场背景[J].南方文坛,2004,(6)∶20.
[2] 王长国,叶祝弟.小小资文学的青春地图[J].名作欣赏, 2006,(6)∶58.
[3] 赵静.冷眼阅读张悦然[J].山东文学,2006,(2) ∶72-74.
[4] 张悦然.张悦然文集∶昼若夜房间[M].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
[5] 张悦然.誓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4.
[6] 王光东.东岳论丛[J].1997,( 6).
[7] 张悦然.写作只为稀释寂寞[N].中华读书报2004,(8).
[8] 张悦然.张悦然文集∶霓露[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On Zhang Yue-ran
YU Xiao-we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China)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 potential new hand, perusing Zhang’s texts, and studying them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literary history, we will find that Zhang’s novels are subjective writings, poetic novels; there is evident aestheticism pursuing in her novels, and full of magic and super natural colors; from feminist literature, her novels are typical female texts, full of the beauty of extreme of feminine.
ZHANG Yue-ran; poetic novel; aestheticism
2010-12-09
喻晓薇(1974-),女,湖北武汉人,硕士,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批评。
I210.6
A
1009-9115(2011)03-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