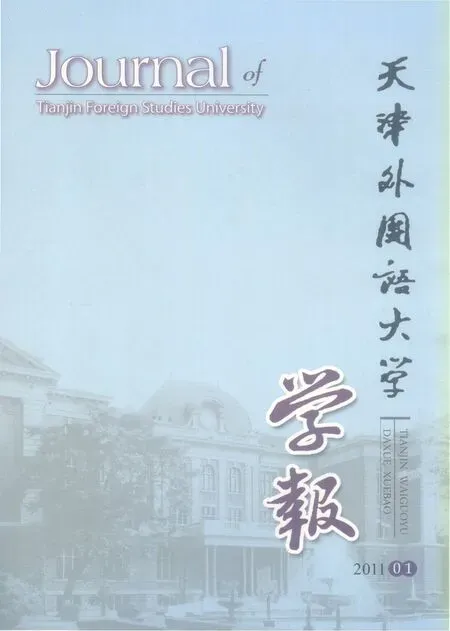认知视角下转喻的修辞功能再考
王 军,唐 毅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东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620)
认知视角下转喻的修辞功能再考
王 军,唐 毅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东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620)
转喻目前已被看作是比隐喻更为基础的一种认知方式。转喻的修辞功能始终都在语言使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知科学在转喻研究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发现对转喻的修辞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从认知到修辞的再次转向,或者说是基于认知的修辞探索,必然会使传统的转喻修辞研究焕发新的生机,也会对其他辞格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认知;修辞;转喻;隐喻
一、引言
人们对转喻的关注长期以来一直与对隐喻的关注紧密结合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转喻是隐喻的一个组成部分(Panther &Radden, 1999:1)。Lakoff和Johnson (1980)也在经典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中专门辟出一章对转喻进行阐述。随着对两种比喻现象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发现转喻和隐喻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典型的转喻和隐喻似乎处在一条轴线的两端,中间地带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Barcelona, 2000:10)。隐喻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转喻的发展过程。
Lakoff和Johnson (1980)著作的发表标志着(广义的)隐喻研究开始从传统的修辞学转向认知语言学,而现代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隐喻研究广泛而深入的开展,这使得有些人甚至产生认知语言学就等同于隐喻研究的错误印象(Taylor,2007:173)。隐喻的认知研究可谓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也成为当前语言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认知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人们对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进行探寻的一种手段,隐喻的认知研究更多地是在揭示隐喻的思维本质。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的作用并没有消失,也不应该被遗忘,隐喻认知研究的成果应该用来加深人们对隐喻修辞功能的认识。
由于转喻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视作比隐喻更为基础的一种认知方式(Panther &Radden, 1999:1; Taylor, 1995; Barcelona, 2000),本文就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转喻上。转喻的种类比较多,本文仅限定在名词性转喻这个类别。希望通过这一探索启发人们以认知的视角或借用认知研究的成果去探讨转喻、隐喻以及其他辞格的功能作用,让古老的修辞话题重新焕发生机。
二、传统修辞学中的转喻
在修辞学中,转喻的替代观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从词源学上讲,“转喻”一词最初来自古希腊,意为意义的改变。无论是古希腊修辞学家还是阿拉伯修辞学家,通常都是把转喻作为一种替换过程来处理(陈香兰, 2005:56-57)。能够反映转喻替代观巨大影响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就是各类工具书对转喻概念的界定。例如,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的定义是“a figure of speech that consists in using the name of one thing for that of something else with which it is associated(一种使用一种事物的名称表示另一种与其相关的事物的修辞格)”,Literary Dictionary的定义是 “a figure of speech that replaces the name of one thing with the name of something els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t(一种使用一种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种与其密切相关的事物的修辞格)”,Columbia Encyclopedia的定义是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n attribute of a thing or something closely related to it is substituted for the thing itself(一种修辞格,其中一种事物或与这种事物密切相关的某种东西的属性被用来代替这一事物本身)”。虽然这些工具书的类别不同,但在对转喻的界定上有两点是完全相同的,一是均把转喻视作一种事物或有事物属性参与的替代关系,二是把转喻视作一种修辞格,这与当代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看法存在明显的不同。
传统的转喻研究虽然以替代观为基本特征,但在某些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概念因素,如在划分替代关系时就会出现诸如原因代结果(CAUSE FOR EFFECT)、容器代内容(CONTAINER FOR CONTENTS)等概念关系,这些都属于一些比较概括的概念思想(general conceptual notions)(Radden & Kövecses,1999:17),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操作具有很大的不同。传统修辞学中的转喻大都停留在名词性转喻的层面,与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研究视野相去甚远。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对诗学以及诗性语言很感兴趣,对比喻(trope)的研究正是看中了它不同于一般语言表达的特点。比喻性语言被看作是背离语言规则而产生的非常规(deviant)现象,能够增加文体的魅力与特色,这一思想也为20世纪的修辞学家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家所接受(刘正光,2007:1-2)。转喻的修辞功能主要体现在言辞简洁、表达生动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语言形式,后者主要是指内容。转喻能够“表达比思想更多的内容”(李鑫华, 2000:89)。例如:
(1)O, for a beaker fu ll of the warm South. (John Keats,Ode to a Nightingale)
啊,满饮一口南方的美酒。
在本例中,the warm South或指英伦岛的南部或欧洲的南部,那里的气候温和,盛产葡萄,也因而盛产葡萄酒(李鑫华, 2000:89-90)。但如果把上述全部信息都表达出来,这句话必然就会显得啰唆、累赘。
Dirven和Pörings (2002:120-123)认为,名词性的指称转喻事实上隐含着一个修饰语+中心词的短语结构(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例如,在The shoes were neatly tied.(鞋系得很利索)中,the shoes的隐含结构为the laces of the shoes(鞋带),转喻使用的结构性优势显而易见。Leech (1983:152)也曾说过:“转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省略,它在诗歌中明显的优势在于表达上的简洁。”
转喻的另一个重要的修辞作用是表达的形象生动性。黄任(1996:78)认为,转喻是“利用两个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来唤起别人的联想,从而避免生硬直说”。在新闻报道中记者们经常会使用转喻来称呼各类人或物,给人以简洁有力而又幽默巧妙的印象,如用Uncle Sam(山姆大叔)转指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用 the Pentagon(五角大楼)转指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美国国防部)。汉语中经常使用的“大腕”(有名气、有实力的人)、“大款”(很有钱的人)、“丹青”(绘画)等词也具有很强的对人或物进行生动刻画的美学功能(李国南, 2001:164)。
三、转喻的认知解读
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转喻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是人的基本认知思维方式的反映。转喻以事物的邻近(contiguity)关系为基础,在同一理想认知模型里通过一个概念(源域)提供的心理通道来通达另一个概念(目标域)(Peirsman & Geeraerts, 2006:270)。转喻的认知研究成果表现在很多方面,下面仅对能够对转喻的修辞功能产生直接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当代认知科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为人类是在对外部世界种种现象的感知体验过程中才逐步形成概念、范畴和思维,抽象出认知模型,建立起认知结构并获得意义。人类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自身和空间的理解,沿着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的道路逐渐发展起来的(王寅, 2006:287-288)。Dirven和Verspoor(1998:2)曾说过,人们在描述事件时总是把人放在优先的地位。这表现在转喻思维方面就是倾向于以有生命的、具体的、与人有互动联系的、具有使用功能的事或物去理解无生命的、抽象的、与人无互动联系的、没有使用功能的事或物。作为转喻的认知理据,与人类经验并行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感知的显著性。这表现为我们的感知器官倾向于也易于感知那些直接(观)的、现实(在)的、大的、有完型结构的、边界清晰的、特定的、能引起注意的事或物(文旭、叶狂, 2006:7)。转喻的体验观对于我们创造转喻和进行转喻理解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转喻的替代观有着根深蒂固的修辞学传统,这种思想对当代认知视角下的转喻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Panther和Thornburg(2004:107)认为,在原型转喻(prototypical metonymy)中,对目标域的凸显能够实现最大化,源域义被目标域义完全取代,转喻替代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更多认知视角下的研究发现转喻并非是一种替代关系。Warren(2004:106-107)明确指出,在转喻关系中,“隐含成分并不能取代显性成分,相反,两者是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指称整体”。Panther和Radden(1999:9)认为,转喻替代观存在“严重的缺陷”(serious draw-backs),应该把源域和目标域看作是处于同一认知框架(conceptual frame)内,其中源域作为一个参照点在视解中被背景化(backgrounded),而目标域则被前 景 化(foregrounded)。Radden和 Kövecses(1999:19)也认为,源域和目标域作为两个概念实体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新的、复杂的意义整体。持类似观点的还有Dirven(1993:14),Langacker(1993:30)等。
吕叔湘 (1998:65)曾说:“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像打仗,占据一片,控制一片。”占据的一片显然不必大,但一定要是要害之处,否则就难以做到控制一片。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普遍地把转喻中的源域视作某一理想认知模型(ICM)中的一个概念参照点(Lakoff,1987; Panther & Radden, 1999; Langacker,2000; Barcelona, 2000; Dirven & Pörings,2002)。通过对这一概念参照点的激活,继而连通激活目标域概念,并最终实现对包括源域与目标域概念在内的整个认知框架的认知解读。既然源域被视作参照点,它必须具有足够的显著性和可区别性,否则经由源域到达目标域的心理通道就无法被适时打通,或者只是打通了经由源域到达非理想中的目标域的通道。例如,英语中的hand, head, mouth等身体器官均可以用来转指人,使用上述任何一个词均可以激活目标域人。而我们在实际的话语篇章中使用某一种身体器官转指人的时候往往不是转指一个泛泛的人,而是转指具有某种特别属性的人,而这种特别属性正是由源域所体现的。hand是人体最为显著的用于劳动的器官,所转指的人应该具有劳动的属性,当我们说we need a lot of hands(我们需要很多人手)时,并非仅仅表示需要人,而是需要一些能够干活的人。mouth的主要功能是进食,它基本上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属性,如果用于转指干活的人则缺乏应有的显著性和可区别性。由此可见,转喻中目标域的成功激活必须有赖于选择一个恰当的源域作为参照点。
徐盛桓(2005:11-12)认为:“常规关系是事物自身的关系,包括客观世界自主的规则和人世间自为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喻就是常规关系的体现。首先,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心理连通的基础是某种一般的常规关系。利用容器来转指内容就属于一种一般的常规关系,因为容器这一概念总是相对于能够容纳某种物质而存在的。基于这种一般的常规关系,我们既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诸如“壶开了”这样的普通转喻,也可以创造和理解一些所谓的新奇转喻,如“暖壶开了”(使用热得快时)。其次,特定转喻内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心理连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不断强化,形成自动化很高的激活连通关系。例如,英语常用grey hair转指老人(The grey hair should be respected.), 而 汉 语 则 使用“花白胡子”来指称长者(前面来了个花白胡子),尽管英汉语的源域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能分别与目标域老人构成常规关联。第三种常规关联与回指(anaphora)有关。Panther和Thornburg (2004)把转喻粗略地分成两种,一种主要凸显目标域,称之为原型转喻(prototypical metonymy),并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典型的转喻。例如,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impatiently.(火腿三明治等得不耐烦了)中的主要对象显然是人(目标域)而非火腿三明治(源域),在后续话语中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继续以人作为话题,如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impatiently, and he wants to leave.另一种转喻所凸显的对象是源域,如在“衣服晒干了”中,衣服被用来转指水,但在该句中水的概念认知地位远不及衣服,因为在更大的语境中我们似乎只会进一步谈论衣服(如“衣服晒干了,该收起Ø来了”),而不太可能去谈论水。事实上,还有一种情况是介于单纯的源域凸显和目标域凸显之间,如前面提到的“壶开了”的源域壶和目标域水的显著性难分伯仲,因为我们既可以说“壶开了,可以拿Ø来沏茶了”(零代词Ø指水),也可以说“壶开了,快拿Ø下来”(零代词Ø指壶),甚至还可以说“壶开了,先拿Øi下来,凉一凉Øii沏茶Øii才好喝”(第一个零代词指壶,后两个零代词指水)。因此,所谓的第三种常规关系,是指转喻的源域或/和目标域与潜在回指语之间在语用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较稳定的心理连通关系。
四、从当代认知研究成果反观转喻的修辞功能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深刻揭示了转喻形象生动特点的根本动因,即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基于身体体验,基于直接感知。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才能逐步扩展到身体之外,进入更加抽象的甚至虚无的世界。这是一个由形象到抽象,由直接到间接,由简单到复杂,由生动到深刻的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人的思维发展过程既然如此,在正常情况下语言的表达和理解就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转喻的生成和理解正是符合了人的这种基本认知规律。我们用壶转指里面的水,而不用里面的水转指壶,因为壶比水能更直接被感知。而我们能用菜名转指食客,或用乐器名转指演奏者,因为菜名或乐器名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显著性和可区别性,最容易被感知和定位。正如当代认知语言学把转喻视作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和普遍的认知方式一样,我们是否也应该把修辞学中转喻的诗性功能或美学功能淡化一些,或许更有利于对转喻的理解、创造和使用。
Dirven和Pörings (2002:120-123)把转喻的本质结构视作修饰语+中心词的关系,这是一种句法关系。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只有修饰语得到凸显,转喻的简洁性才能一目了然。更多的认知语言学家虽然并不一定认同转喻深层语义中存在的这种句法结构,但却普遍认为转喻打通了由源域到目标域的心理通道,使源域和目标域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主体,源域表达式以一己之力激活了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结合体。
转喻的简洁性不仅表现在一种类似于量的多寡关系上。参照点理论认为,在经由参照点激活某一概念实体的过程中,参照点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和可区别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目标域激活的准确性。参照点作为一个点具有形式上的简洁性,而作为一个认知触发语还携带有延伸激活的关键语义信息。只有在充分考虑到后一因素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对转喻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这无论是对转喻的理解和欣赏还是对转喻的创造,均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
画龙点睛是通过点睛之笔激活整条龙,这一方面体现了睛之关键,更重要地是描绘出了一条活灵活现的龙。点睛之笔固然重要,但点睛之后我们往往只关注整体效果,即所谓的完形认知。在完形认知中,整体感知是第一位的,对部分的感知位居其次,甚至得不到感知。画龙点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修辞学对转喻的认识。而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转喻表达获得的往往是一种一箭双雕的效果,假借转喻表达语的使用,使源域与目标域同时被感知,前面提到的“壶开了”这一转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一箭双雕也并非意味着源域与目标域总能获得基本相同的认知凸显地位,有时源域的认知地位会高于甚至远高于目标域的认知地位,或者相反。这种变化能带给我们诸多启示。首先,传统的转喻替代论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一箭双雕的阐释更具说服力;其次,不同类型的转喻具有不同的表达或修辞效果,它们或更多地凸显源域,或更多地凸显目标域,或两者并重;再次,在转喻的创造和使用过程中,常规关系始终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得某一特定转喻的语用修辞功能逐渐发生某些变化;最后,转喻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之一,是思想表达非常自然的一种方式,因此,转喻表达并非总是具有显而易见的修辞功效。
Panther和 Thornburg(2004)的研究表明,最能让我们体会到转喻修辞效力的形式是那种能够凸显目标域而非源域的转喻,即他们所说的原型转喻或好转喻。因为这种情况下形式(特指源域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特指目标域)的冲突最显著,而冲突比和谐在修辞上往往更具表现力,更能引人注目。即便是在那些已经规约化了的(conventionalized)凸显目标域的转喻(如使用hand转指干活的人,而不是直接使用person一类的直接指称词语)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转喻的修辞效力。当然,凸显源域的转喻也并非总是不具有修辞效力。以认知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转喻为例:
(2)Nixon bombed Hanoi and he killed countless civilians. (Ruiz de Mendoza &Hernandez, 2003:36)
尼克松轰炸了河内,杀害了无数的居民。
尽管上例中Nixon被用来转指美国飞行员,但由于实际凸显的对象是源域(Nixon),后续话语中只能使用he来回指Nixon,而不能使用they一类的词语回指目标域(美国飞行员)。就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来看,该例中形式(Nixon)与内容(美国飞行员)的冲突并不强烈。然而,当把语言语境因素(Nixon bombed Hanoi)考虑进去的时候,这种冲突还是存在的,毕竟实际轰炸河内的人并非Nixon本人而是美国飞行员。该例中语境的冲突并未改变源域在该话语片断中的主题地位,源域的主题性大大削弱了目标域的认知显著性,并使得转喻的修辞效力受到一定抑制。
当我们无论通过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还是通过语言语境的效果,都难以获知转喻的形式与内容的冲突的时候,原有的修辞力就基本消退殆尽了,几乎感受不到“衣服晒干了”中还有多少修辞效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结语
跨学科研究不一定只是一种横向的沟通与交流,还应该包含纵向的回顾与展望。转喻作为沟通修辞与语言认知研究的一座桥梁,一方面在共时层面上应为两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双方能够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从认知研究的角度出发,不应只是把传统修辞学中的转喻视作认知研究的垫脚石,可以把转喻修辞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利用最新的认知研究理论和发现作为研究工具或研究基础,更加深入地挖掘转喻的修辞功能,让认知回归解释性本质,让修辞重新成为语言研究的聚焦主体之一。本文的研究即为这方面的一点尝试。
[1] Barcelona, A.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C]. Berlin: Moutonde Gruyter, 2000.
[2] Dirven, R. Metonymy and Metaphor: Different Mental Strategies of Conceptualization [J].Leuvense Bijdragen,1993, (2): 1-25.
[3] Dirven, R. & M. Verspoor.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4] Dirven, R. & R. Pörings.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2.
[5] Lakoff, G. & M.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6] Lakoff, G.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 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7] Langacker, R. W.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4): 1-38.
[8] Langacker, R. W.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9] Leech, G. N.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London: Longman Group , 1983.
[10] Panther, K.-U. & G. Radden. Introduction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14.
[11] Panther, K.-U. & L. L. Thornburg.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J].Metaphorik,2004,(6).
[12] Peirsman, Y. & D. Geeraerts.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J].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17(3): 269-316.
[13] Radden, G. & Z. Kö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U. Panther & G.Radden (eds.)Metonymy in Languageand Thought[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7-59.
[14] Ruiz de Mendoza, F. & P. Hernandez. Cognitive Operations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 [A]. In K.-U. Panther & L. Thornburg (eds.)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23-49.
[15] Taylor, J. R.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6] Taylor, J. R.Ten Lectures on Appl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John Taylo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7] Warren, B. Anaphoric Pronouns of Metonymic Expressions[J].Metaphorik,2004,(7).
[18] 陈香兰. 转喻:从“辞格”到认知的研究回顾[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8).
[19] 黄任. 英语修辞与写作[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20] 李国南. 辞格与词汇[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1] 李鑫华. 英语修辞格详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2] 刘正光. 隐喻的认知研究—理论与实践[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23] 吕叔湘. 语文常谈[M].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4]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25] 文旭,叶狂. 转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理据[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6).
[26] 徐盛桓. 语用推理的认知研究[J]. 中国外语, 2005,(5).
Metonymy has now been acknow ledged as a more fundamental cognitive pattern than metaphor.As a figure of speech, metonym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Some important theories on metonymy in cognitive science shed much light on the rhetorical exploration on metonymy.A shift from cognition to rhetoric, or more exactly a cognition-based rhetorical exploration, will definitely bring about much enlightenment to the traditional rhetorical study on metonymy and benefi t the study of other figures of speech.
cognition; rhetoric; metonymy; metaphor
H 31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665X(2011)01-0022-06
2010-05-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语篇间接回指对比研究”(07BYY008)
王军(1966-),男,教授,博导,研究方向:英汉对比、认知语言学、语用学
唐毅 (1967-),女,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