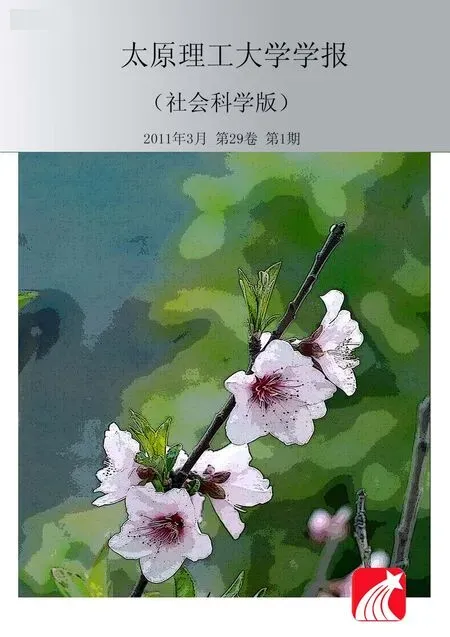构建人类历史科学的四大前提*
李润珍,武 杰
(太原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系,山西 太原 030024)
人类社会系统是由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和人的思维三个子系统有机组成的,相应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那么,研究这三个子系统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揭示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人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科学。深入分析社会系统,探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运动特征是构建整个人类历史科学的中心环节。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构建人类历史科学的基本前提进行探讨,因为它是揭开人类历史迷团首先需要分析的问题。
一、人的生存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人的躯体,另一部分就是人的精神或意识。他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在这里马克思选择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肉体组织来表达人的躯体。不过,在马克思眼中的“肉体组织”不像礅板上的“猪肉”、“牛肉”、“羊肉”或“死尸”,而是与动物的活体组织一样,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用“肉体组织”不仅生动地指出了他的历史学、经济学是以具有“动物”特性的欲望和要求的个人存在作为他人类历史科学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也指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具有意识——高于动物的一种特殊思维。很显然,马克思的“分解”就像我们今天把信息和信息载体(如音乐和乐器)区分开来一样,完全是一种科学的处理方法。
80多年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任何一个存在者都有其存在,人们也可追问任何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但是一般的存在者对其存在并无所关注和察觉,他们是不会提出关于存在的问题的。存在论的出发点不能是任何一种存在物,而必须是这样的存在物,它的存在是其他存在物的存在的基础,因此,对于它的分析能够导致对一般存在的把握。人就是这样的存在物,因为只有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才能提出和追问存在问题,才能揭示存在者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人的存在,其他事物才能得以显示自己。人的存在是其他事物存在的先决条件。为了区别人的存在,海德格尔以“生存”(existence)表示人的存在。只有人是生存着,其他存在物都不能生存,它们的存在(Being of beings)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只能通过对于原本意义上的存在,即人的生存才能被理解。尽管人只是存在物中的一个或一类,但却体现了原本意义的存在物,因而和其他一切存在物相比具有优先地位。
随后,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专指现象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即先于主客、心物二分的,没有规定性的原始状态下的人的存在,以此和日常生活、传统哲学及科学中的人和主体概念区分开来。“此在”就是“存在于此”的意思。这样,人们对Dasein就既不可能有具体的、确定的感觉,又不可能有一般的、抽象的概念,而只能有关于人存在于此的原始和混沌的意识,即对人的存在显现的直接领悟。正是由于人对自己的存在有这种领悟,才使得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和其他一切存在者区分开来。所以,海德格尔称此在的存在为“生存”。
因此,我们认为,在人类历史科学中,透过承传下来的东西,透过这些东西的表现方式及传统而直趋社会现实本身的倾向日益强烈的今天,“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2]
二、人的自然前提
我们知道,思维系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思维系统的存在,人类社会就会退化如达尔文(C.R.Darwin)的生物进化论所说;如果再把生物系统也去掉(即把它当做一般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这样的进化论就是整个宇宙的进化理论了。因此,宇宙的演化发展是有层次的。人类作为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的产物,处于生命金字塔的顶层,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人类作为世界上最高级的生命存在,他的行为自然要以自己为中心,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3]因此,“人靠自然界生活”。在这里,自然界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一样,是人类历史科学的第二个前提条件。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述。然而,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过去的思辨哲学也仅仅从普遍概念出发,无法提供一个准确的、有效的分析方法。因而,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天人合一也好,人是精灵也好;分开也好,合起来也好——都是根据一些“专家”、“权威”的个人思维体系而得出的一些既无定量分析,也无逻辑分析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当我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科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人类历史科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就像生物与自然之间的作用过程一样,无论是个人、组织、民族、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意识发展都是人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从这里,我们既找到了人与社会的物质基础、生存基础,也找到了人与社会的结构基础和情感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符合情感法则,也符合经济法则、政治法则和意识法则。整个人类历史构造就是自然构造和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像生物那样的纯粹自然构造的结果。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没有看到的东西。
人类利用社会群体的力量,通过各种生产实践,从自然界那里获得了自身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问题的自觉而分散的探索,产生了各种自然科学,并促使各种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改变了自然的本来面貌。人类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使智慧人类猛醒:人——社会——自然这个巨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至大方面(如整个地球的生态)与至小方面(如每个人的行为与观念)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的耦合关系。这就促使人类追求新的平衡,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人的思维前提
思维依附于人的存在而存在,没有人就没有思维,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没有思维的躯体,人就等同于动物;没有躯体的思维就是幽灵。那么,在我们的系统划分中,为什么还要把思维和“人”区分开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科学方法的视角来解释。达尔文根据他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不仅把人的思维与“肉体组织”进行了分离,而且干脆把思维从“肉体组织”中抽掉而不予考虑。即他并不研究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特殊性,而是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对于达尔文的这种划分方法,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内是完全可行的,但对于人类历史科学来说,这样的处理就是原则性的错误了![4]
达尔文把人的思维抽掉,人们认为它是科学。马克思把思维找回来,并重新还原给“肉体组织”——但他仅仅是从观念中把思维找了回来,却没有把思维和“肉体组织”放在一起,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历史“参数”来进行考察。在这里,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把思维从肉体组织中分离出来,并不予以考虑;而后者也把两者分离开来——但把它放在了“另一个篮子里”——这不是本质上的分离,而是科学方法上的分离。当然,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与达尔文并没有谁秉承谁的思想的问题,而仅仅是在方法论上的不谋而合。[4]然而,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与达尔文分道扬镳了。
那么,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认为,人是会制造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事实上,动物也会劳动,甚至会生产产品,而且很多产品是人无法比拟的,所以,现在有一门学科叫仿生学,就是专门模仿动物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来改进工程技术系统。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5]。这说明,人类劳动,即人类创造历史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受自己思维的支配。人具有思维,这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人具有思维,动物也具有思维,并且像海豚、猩猩这样的动物的思维还达到了较高的层次。据考证,海豚的思维达到了3~5岁小孩的水平。但是,人可以把环境的信息通过思维与其劳动关联起来,动物却不具有这种本领。因此,从本质上讲,人的这种学习机制最终实现了由“刺激—反应”向“学习—适应—稳定”模型的转化。这也就是说,人的思维与动物思维的根本区别,不仅仅是在水平的高低上,而且因为人的思维可以有效地利用环境,形成了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即人的思维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正如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创始人约翰·H.霍兰(John H.Holland)所说的“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在这里,“我们把系统中的成员称为具有适应性的主体(adaptive agent),简称为主体。所谓具有适应性,就是指它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主体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6]。所以,人的思维能在几千年内发生无法想象的变化,而动物的思维却在几亿年内还几乎停留在原始的本能阶段。因此,人具有特定的人类思维是人类历史科学的第三个前提条件。在人类历史科学中,广义的物质系统和广义的思维系统相交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也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之一。
那么,为什么我们仅仅把思维的一部分纳入人类历史科学呢?难道我们只让一部分人进入历史吗?当然我们不是只考察一部分人的历史,也不是让一部分思维进入历史,而是因为从目前的观念来说,还有许多人认为,除了在普通人的头脑中存在的思维之外,还有所谓超越现实世界的“绝对精神”。 那么是否存在着绝对精神呢?在我们以往的教科书上对它似乎看得十分重要,甚至把它看成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对立事件。其实,科学是非常宽容的。现代自然科学不是仍然在寻找“反物质”、“暗物质”和“虚拟空间”吗?牛顿不是也曾证明上帝的存在吗?因此,认为绝对精神的存在并不是人类历史科学的障碍,甚至完全可以像寻求“反物质”那样去寻找绝对精神。就连我们许多普通人也在思考绝对精神,比如,相信鬼神,探求可能世界。但是,科学有一个严格的“自律标准”,那就是科学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意味着科学所承认的思维仅仅是那些真实存在于人脑中的、可以检验的思维,而不是虚拟的、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的、或像史蒂芬·霍金(S.W.Hawking)所认为的存在于“黑洞”之中的那种思维。[4]
四、社会结构前提
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的肉体组织、无机的自然界和人类思维的简单叠加吗?这也是人类历史科学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社会不是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将无机世界、生命世界和思维世界像揉面团一样杂乱糅合起来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建造”起来的社会有机体。人类社会是有组织的结构——这是马克思人类历史科学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理论的根本所在。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有机体的“细胞”,人群共同体好比是社会有机体的“器官”或“组织”。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大厦的基础,它好比是社会有机体的“骨骼”,支撑着社会有机体,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社会中的一切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关系,则好比是社会有机体的“血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有机体是包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总体性范畴,指人类社会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要素相互制约、有机联系所构成的整体。其中的各种要素是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彼此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表现出一定的秩序,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人们在研究社会时,不应“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这表明,社会历史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一定社会结构,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完成的有机统一。“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3]所以,人类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指人类社会结构的运动。由此不难看到,人类历史科学的第四个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结构的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对马克思人类历史科学的体系也可以按照“公理”+“假设”+“逻辑”+“检验”的方式表示出来。它们是:[4]
公理一:人类社会是由人与自然组成的;
公理二:人的生存需要吃、穿、住、行等生存条件;
公理三:人与动物相比具有独特的思维存在;
公理四:人类社会中的人是按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关系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
假设一:人类社会每个历史阶段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
假设二: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可以看做是平衡态结构来处理。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体系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运动最科学、最深刻的概括和描述。这四条公理和两个假设(这两个假设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是存在的,所以,赖泽民先生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历史科学体系是一个静力学体系)已基本清楚地反映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但是从当代系统科学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它仍然是一个平衡态的理论构架,只有把开放性真正引入人类社会系统,才能找到社会运动的主要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变化的、有机联系的人类历史科学体系。
因此,我们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科学的基本构架就是由马克思提到的四条公理再加上开放性这一外部条件而构成的一个科学体系。当然,这个体系的逻辑演绎将借助于科学进化理论的研究成果,从而阐述其运动形态和演化规律,最后的实践检验环节将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实践来予以证明。所以,科学是一种方法,一般地可以被规定为通过诸真命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体。尽管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感受到,科学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复写”,而是涉及各种巧妙的、合理的分解与组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把笼统的自然界区分为无机的自然界、生命的自然界和思维的自然界,同时把这三个部分都纳入人类社会的考察之中,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科学的基础和基本构架。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再加上开放性这一外部条件,从而构成一个更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上述讨论也可能预演着人们以后展示内容的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09.
[2]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3.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95,121-122.
[4] 赖泽民.人类历史科学原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3,53,54,47.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2.
[6] 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