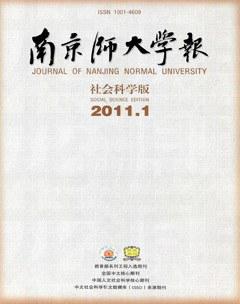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
摘要: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
关键词:何其芳;延安文学;忏悔仪式;话语机制;创作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135—07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407)
作者简介:李遇春,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430079
一、认同后的冲突
抗战后的延安,作为红色的革命圣地,在无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实际上被想象成了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正是这股神圣的激情和诗意的冲动催迫着他们毅然西行,奔赴那片红星闪耀的地方。那情形,宛如虔诚的教徒朝圣,“虽九死其犹未悔”;又如孤胆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便是那一大批以自己的身心去拥抱革命却又无奈地为政治所裹挟的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
何其芳正是这样一个染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群体中的一员。1938年8月,当诗人行进在通往心中“圣城”的川陕公路上时,他竟然“狂妄”地想起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此时的何其芳还是一个满怀“摇醒成都”般激情的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一个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这实际上是知识精英积极干预社会现实、谋求改良人生境遇的启蒙主义姿态。它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旋律。对于何其芳而言,从北平时期“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跃进到成都时期“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勇于对社会人生“叽叽喳喳发议论”(《云》),这种转变的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它标志着诗人开始洗尽铅华、告别感伤,逐步超越早期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藩篱,摆脱“刻意”“画梦”创作定式的拘囿,从而预示着诗人又一个“艺术的春天”的来临。然而,历史就像那浩瀚无垠的大海,其间翻滚腾跃着无数神秘的时代的浪潮。古往今来,除极少数时代的弄潮儿能够驾驭那神奇的伟力并藉此升腾至生命的峰巅外,无数生命的孤舟只能无奈地被时代的巨涛所挟裹,身不由己地漂流,至多只能做象征性的反抗,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历史所吞噬的宿命。何其芳自然也未能例外。当诗人向理想的“圣地”进发时,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误把“延安”当“成都”,他仍然天真地以醒世型的启蒙者自居,像飞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珍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作为一个预言型的诗人,何其芳并没能参透老黑格尔所谓“历史的诡计”。这一次顺应时代潮流的漫长“旅行”并不像诗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狡黠的历史就像一柄双刃剑,当诗人响应它的召唤去接受革命的洗礼时,同时他也就不经意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就主体与权威政治话语的关系而言,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大体上历经了三个阶段:认同、冲突、沉默或失语。最初的延安让诗人“充满了印象”和“感动”,尤其那“自由、宽大、快活的空气”更是让诗人心折,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写下了著名的时文《我歌唱延安》。诗人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诗作是《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叙述了一个农民如何阶级意识觉醒,参加八路军英勇抗日,最终凛然面对日寇的火刑慷慨就义,成为了一个“新的殉道者”和“新的圣徒”的革命传奇经历。这首叙事诗其实是对当时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化演绎。它表明诗人的心灵开始为权威意识形态所笼罩,同时也意味着一个自由的主体开始被主流权力话语所重新塑造和建构。但诗人对政治话语的直接认同很快便遭遇了危机,他过去业已形成的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仍然想顽强地表达自己。巨大的心理冲突遂由此滋生并蔓延开来,1945年初版的诗集《夜歌》中的大部分诗章便是诗人这一阶段心灵挣扎、灵魂搏斗的真实写照。作为主体应对政治权威话语的典型心态的传达,何其芳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是本文后面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
1942年春天以后,何其芳基本上中断了诗歌写作。诗人陷入了痛苦的沉默,那是一种旁人无法深味的孤寂。“诗人”与“热心的事务工作者”(《叫喊》)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一个“合理化”的借口,我们必须寻找诗人患上“失语症”的真正原由。那年的春天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紧接着毛泽东又在5月专门为文化人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旨在为文艺创作“立法”。随后在翌年夏,整风运动又被康生变本加厉地导向了一场恶劣的“抢救运动”,弄得不少从“亭子间”来的文化人“惶惶不可终日”。可以想见,这场铺天盖地的思想整改运动在何其芳的心灵中投下了深重的暗影。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他还能运用“合法化”的话语策略来“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③的话,那么在《讲话》业已确立了一套革命文艺规范,制定了一个从内容(“写什么”)到形式(“怎么写”)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生产范型的历史语境下,诗人除了热情地充当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外,便只能三缄其口了。何其芳早年的唯美主义倾向残留,使得他从心灵深处鄙视前者,沉默或失语于是成了他不可移易的宿命。于是我们看到,从1943年至1953年,何其芳只留下了《新中国的梦想》(1946)、《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49)等寥寥几首“颂诗”,直到1954年发表的《回答》才含蓄地泄露了诗人多年“失语”的隐秘心曲。诗人起始自比为一叶孤舟,被“猛烈”而“奇异的风”所“鼓动”,既“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终篇又自喻为一只倦鸟,虽“努力飞腾上天空”,却“只能在地上行走”。从中我们不难体味诗人灵魂里深深的苦闷与寂寞。由于建国后主流政治话语的无边渗透,今天我们已无法深味诗人那长埋心底的浓郁诗情:“像密封在地下的陈年的酒,什么时候你强烈的香气,像冲向决口的水一样奔流?”(《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1965年)
二、一种双重性的话语策略
何其芳延安时期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占据了诗集《夜歌》中的绝大部分篇章。它为我们今天分析那个红色年代的知识分子作家采取何种话语策略,超越意识形态权力运作提供了一批绝好的文本“样板”。诗人来延安后不久,便体察到了那种泛政治文化规范的限制和压抑。他意识到只有“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才符合自己一贯的创作个性,而“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于自己只能是勉为其难。诗人于是“动摇了”、“打折扣了”、“退让了”、“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的倾
向抬头了”,这才留下了一批传递自身“新旧矛盾情感”的诗篇。在创作中,诗人一边“唱旧世界的挽歌”,“我将埋葬我自己”;一边“赞颂新世界的诞生”,“快乐地去经历我的再一次痛苦的投生”(《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之二)。诗人在情感上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以至于在当时的革命文艺规范尚未定型的语境下最大限度地宣泄自己,顽强地表达自己,与此同时,诗人在理智上又是“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夜歌》之二),他无法拒绝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召唤,只能被迫否定自己、审判自己,藉此向其时已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秩序表示认同和皈依。
不难看出,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革命文艺规范的拘囿,何其芳或显或隐地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话语策略来进行自我抵御和防卫。对此,诗人曾有过明确的说明:“这些诗发泄了旧的知识分子的伤感、脆弱与空想的情感,而又带有一种否定这些情感并要求再进一步的倾向(虽说这种否定是无力的,这种要求是空洞的)。”这种意味深长的话语策略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了何其芳延安时期的大多数诗文本之中。借用米歇尔,福柯的说法,本文称之为忏悔仪式。福柯指出:“忏悔是一种话语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说话的主体同时又是陈述主体;它同时又是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仪式,因为不当着合作者的面,谁也不会去坦白忏悔。这位合作者不光是一个对话者,而且是一个权威,他需要你坦白,规定你要坦白,并对你的坦白予以评价,不断介入以进行裁判、惩罚、宽恕、安慰与调解;在这一仪式中,真要想得到确认,就得克服在系统阐述时必然会出现的障碍和阻力。”作为一种话语仪式,忏悔内在地具有某种权力结构。在说话者和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后者对前者具有支配性和统治力量,说话者并不是支配者,因为这种说话是身不由己或曰言不由衷的,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话语构成规则,说话的内容和形式早已预先被规定,因此说话者表面上是主动者而实际上却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言说机器。反之,对话者(准确地说应是听者,因为在整个仪式中它始终是一言不发的权威)才是主动的支配者,他不仅是从说话者身上“压榨”和“挤出”坦白话语的人,而且是对这些话语进行最终裁决和处置的权力载体。正如福柯所言:“知道内情并给予回答的并不是支配者,而本应什么都不知道的提问者才是支配者。”如此,忏悔作为话语仪式内含着某种苦涩的反讽意味。以上是就忏悔仪式的本质而言,至于其功能则具有更强烈的悖论色彩。在福柯那里,陈述主体一般来说并不等于说话主体,确切而言,应称其为“位置”。在忏悔仪式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忏悔者和裁判者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的“位置”,前者可以由罪犯、教徒、学生、病人等一切可能的越轨者来置换,后者则可以由法官、牧师、教师、医生等一切现实的立法者来替代。当越轨者坦陈自己的犯禁行为时,一方面他通过否定自己以求立法者来拯救自己,另一方面他又凭借话语的力量再次宣泄并肯定了自己,而且对于包括一切立法者和追随者在内的听话者来说都具有某种隐在的心理补偿功能。显然,后者对于越轨者和立法者而言是始料未及的,或者不如说正是他们潜意识中所召唤的。
作为忏悔仪式的诗歌话语,诗集《夜歌》中的大部分篇章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成的:那时的何其芳在白天“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叫喊》),只有到了晚上或凌晨他才是一个诗人。在《夜歌》(二)中诗人引用了《雅歌》中的话作题记:“我的身体睡着,我的心却醒着。”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即白天/夜晚、革命/文艺、躯体/心灵、沉睡/清醒,它们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是权威话语与自由人格之间的对立。实际上,这种外在的对立与诗人提供的诗文本的内在结构是同一的。我们看到,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文本大多包含了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红色话语系统,能够集中凸显其特征的关键词有:工农兵、革命、阶级、集体主义、乐观精神、大众化、民族形式等;一套是“灰色”话语系统,与之相应的关键词则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人性、自我、个人主义、悲观情调、“化大众”、西化倾向等。曾几何时,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被贴上了“灰色”的标签,以彰显其自私、冷漠、动摇、妥协等负面特征。这使得他们在大公无私、彻底革命的“红色”工农兵群体面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实际上,何其芳延安诗歌中的两套话语系统本质上表现为红色和“灰色”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然而,这种对立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双峰对峙,而是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不是双方之间平等的互动式对话,而是一方折服并认同于另一方的话语权力。从诗人提供的诗文本来看,红色话语系统在文本中所占的篇幅,也就是它们得到的表现机会并不多。相反,“灰色”话语系统在文本中占据了大多数篇幅,有时甚至呈现为自言自语的独白状态。但是这种表面的话语强弱对比并不能说明真实的情形。要想深入探讨何其芳延安时期诗歌话语中内在的权力结构,我们必须考察两种话语系统各自的地位和功能。首先,红色话语系统在整个话语仪式中充当的是支配者、统治者、裁判者的角色,本质上它是所谓听话者,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不时地插话,更多的时候它还是不怒而威、“无声胜有声”的权威者。相反,“灰色”话语系统由于缺乏政治权力的支撑,面对高踞“上位”的权威听者,只得匍匐于地、屈居“下位”,除了遵照主流话语规范进行坦诚忏悔之外,似乎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在整个话语仪式中,它才是所谓的说话者,然而正如福柯所言“说话者并不是支配者”,因为这些被“压榨”和“挤出”的坦白话语并不能真正地,或者说不完全地代表“说话主体”的心声,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被动的“陈述主体”。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当“灰色”话语系统在整个话语仪式中忏悔即“陈述”时,虽然其间渗透和辐射着主流话语规范,但这并不能完全排斥和封锁住在那些忏悔式“陈述”中或隐或显地传达出的“灰色主体”的真实情感和思想。
不妨以爱情话语为例稍事分析。在红色话语规范的视野中,爱情无疑是“灰色”的,属于“小布尔乔亚情调”之类。而对于多情的诗人来说,“在这十年(指1932-1942——引者注)中缠绕得我灵魂最苦的/是爱情”,“谈论得最响亮的是恋爱”。(《给T.L同志》)但诗人深知作为“灰色”话语的爱情无法直接和正面地走进诗文本之中,因为权威政治话语已经统摄了诗人的灵魂。就在刚引用的同一首诗中,诗人采用了自我否定的方式直接喊出了“打倒爱情”的口号,就“像可怜的洋车夫喊‘打倒电车”一样,以此表达对红色话语规范的认同,同时也达到了“热烈地谈论”爱情话语的潜在目的。与这种“否定”的言说策略不同,诗人在《夜歌》(五)中运用了“消解”策略,即以红色的“同志爱”置换“灰色”的爱情,以此达到话语稀释和净化的目的。设若稍加体味,便可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曲
折地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在奔赴延安途中邂逅的一位女子的爱慕、相思与怅惘。然而诗人并不承认这是一首“情诗”,又说,“我想即使是,/恐怕也很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无论是在它的兴盛期或者没落期”。这种诚惶诚恐的表白显然是为了赢得红色话语规范的同情并逃避其惩罚。还有一首诗叫《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它同样运用了消解式话语策略,虽说是为了祭奠“最早的爱情”和忆念“最早的爱人”,但又不得不罩上“纯洁”透明的面纱,小心翼翼地向权威政治话语争取着“谈说”“灰色”爱情的机会。
以上不过是对何其芳延安诗歌中的忏悔仪式与爱情话语进行了权力分析,其实类似的“灰色”话语还有不少,譬如对阶级血统的反思、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沉吟等。历史有时候真是既残酷又狡黠,在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中真正为他在当时和以后赢得大量“爱好者和同感者”的主要并不是主流话语系统,而是知识分子的那些“不健康和有害的”,总之是“灰色”的思想情感。
三、被权力制造的主体
作为一种话语仪式,忏悔是权力的产物。忏悔实际上是作为应对权力“技术”的某种策略而出现的。因此,从对忏悔话语的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话语主体对外在异己的权力话语的屈从和反抗,而且还能够窥测出权力重新塑造和建构话语主体的运作机制来。随着外在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任何主体都可能面临着“再主体化”的命运。在当代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眼中,主体不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说,主体实际上是不同话语权力实践和争斗的场所。
在何其芳延安时期作为忏悔仪式的诗歌话语中,我们在上文便已发现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争斗的痕迹。阿尔都塞曾宣称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实践,他的学生马歇雷进一步指出,“文学通过使用意识形态而向意识形态挑战”。前一个意识形态是指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而后一个则是指一定时代的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于话语主体来说,前者是真实的,然而处于潜在状态,后者是“虚伪”的,虽是“异化了的思想”,却往往公开在场。在何其芳的忏悔话语中显然存在着马歇雷所说的文本一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即红色和“灰色”意识形态的“貌合神离”,后者对前者在理智上虽表示皈依,在情感上却依然故我。然而,问题在于,在诗人的忏悔话语仪式中,作为权威话语,红色意识形态用来驯化和改造业已存在的“灰色”主体的运作机制究竟有什么特征?与此同时,“灰色”主体的忏悔策略对自身的重构又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学在1930、40年代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话语转型,即从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灰色”启蒙话语向以工农兵为本位的红色革命话语转换。何其芳便处在这种话语变革的转捩点上,形成了所谓“何其芳现象”,这使得他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在文学史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话语转型本质上是话语内部深层构成规则的变迁。后者被福柯命名为“知识型”,意指“一套在任何既定时刻决定能够思想什么和不能够思想什么、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的先验规则”。这种知识的自主性和支配性使得话语主体沦落为被动的陈述主体。在此意义上,福柯宣称知识即权力,两者实际上二位一体。不难看出,在何其芳延安时期诗文本中两种不同色调的话语系统内部,其实都隐秘地运作着各自的深层话语构成规则即“知识型”。只不过受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红色的革命知识型由于有“制度化权力”的支持,成了一种强势的“规范化权力”,而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粗具形态的启蒙知识型则由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中的“漂泊”身份,一直处于某种孤立无援的状态,直至红色话语勃兴,它也就无奈地退居边缘,孤独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响。何其芳的忏悔话语就诞生在这两种知识型转换衔接的交叉地带,作为某种历史“中间物”,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兴的红色文化规范是如何逐步改造和重塑诗人那业已成型的“灰色”的启蒙主体的。
首先,革命知识型通过“排除程序”(proce-dures of exclusion)来对诗人的话语进行控制,具体地说,即借助“禁止”、“区分”、“拒绝”等战略而发挥功能。所谓“禁止”是指对处于对立面的话语实行强制否定,而“区分”和“拒绝”则是对处于中间状态的话语的歧视和贬低。这两者实际上又统摄于某种对“真理意志”的鼓吹和张扬之中。在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中,由于诗人运用了双重性的忏悔策略来应对政治权威话语的调控,故而无论是与红色话语处于对立状态还是中间状态,诗人启蒙主体的许多“灰色”话语仍然在“规范化权力”所许可的最大限度内得到了表达。“禁止”和“区分”的权力战略在这里已经合流,难分彼此。譬如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在当时并未构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后者只不过被“区分”对待,处于遭受冷落和歧视的中间状态。然而,正是这种尴尬的地位和身份使得诗人作为话语主体,不得不站在否定的立场上将知识分子处理为工农兵的对立面,从而运用忏悔仪式这种话语策略来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将知识分子的那些遭到红色话语规范“禁止”和“区分”的“灰色”话语以某种否定的形态加以言说。再譬如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对于身处“写光明”的阵营——“鲁艺”之中的何其芳来说,择前者而从之理所当然。然而对这种对立话语的处理,诗人却采取了双重策略,即在忏悔仪式中站在“光明”的立场上来“暴露”和否定自己内心中“黑暗”,“虽说这种否定是无力的,这种要求是空洞的”。诗人正是以忏悔的话语策略来较为有效地抵御和超越了主流话语规范的“禁止”战略。此外,诸如阶级论和人性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乐观精神和感伤情调等对立话语中的后者,诗人都让其在否定的形态中作为“他者”得到了间接的表达。当然,上述外在的文化规范战略与主体内在的心理防御策略之间的对抗最终还是规约为对红色“真理意志”的追求,一个红色的“真理王国”开始在话语主体的内部将一切“虚假”的、“非理性”的、“反常态”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潜意识当作“另类”话语驱逐或排挤到了边缘,以致最终消失或者说压抑进了无意识域。
如果说所谓“排除程序”是指红色话语构成规则系统对诗人忏悔话语的内容从外部所施加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控制战略,那么“提纯程序”(procedures of rarefaction)则是前者对后者的形式、准确的说是广义上的语言,从内部实施的垂直方向上的控制战略”。众所周知,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两分为能指(声音)和所指(概念或思想)。虽然他曾指出能指和所指最初的结合是“任意”的,但仍然认为二者的关系通常犹如一张纸的正反面,不可随意分离和拆解。显然,这种语言符号观采用了由上至下、由表及里的深度思维模式。它意味着符号内在地具有某种垂直结构,即每一个能指都有隐藏在下面的约定的所指。拉康对索
绪尔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均衡对称状态提出质疑,他使用“S/s”这一公式(即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来表明,虽然能指对所指具有至上权力,但是所指也能抗拒能指对它的限制和规范”。用福柯的话说,即“词与物”,词语秩序与事物秩序之间既可以互相规范,亦可以互相颠覆。与这种理想的状态相反,福柯所谓的“提纯程序”是指规范化权力对主体话语的“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之间丰富的原生关系实行的“稀释”、“净化”或“阉割”战略。不难发现,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文本基本上是一种转喻型的文本,这与他早期典型的隐喻型文本(《预言》和《画梦录》)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词与物的关系看,隐喻植根于“相似性”的选择和替换,在垂直方向上为语言开拓了巨大的话语空间。而转喻建基于“邻近性”的横向组合,在水平方向上为话语的有效传递构筑了通道。当年延安的革命知识型采用了“民族形式”作为“陈述方式”,正是它在深层次上规定了诗人选择“纯净透明”的转喻而不是意蕴丰饶的隐喻进行话语实践,从而排斥了“灰色”主体反规范的另类话语,剥夺了词与物之间“自由降落”的权利,构筑了语言的“确定性”或“恰当性”的神话。凡此种种,使得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艺术和早期相比逊色不少,同时也可以表明:话语内在的“提纯程序”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比外在的“排斥程序”更为严苛,因为后者犹可以运用忏悔仪式之类的话语策略来加以拆解或超越,而前者只会使主体深陷权力话语之网,无处遁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想见,当年的何其芳为了谋求被延安文学秩序所接纳经历过艰难的心理困境,付出过沉重的精神代价。经历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艰难蜕变。如果说所谓“旧我”指向启蒙知识分子的“灰色”话语,那么“新我”则是以工农兵为代表的革命话语的人格化身。显然。作为话语主体,诗人的心灵已经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争斗的战场。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对主体和现实具有“再生产”的功能。从当时延安的红色话语来看,正是它用一种“真理”化的“想象性关系”规定了诗人作为话语主体所置身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并使其接受和认同。这种认同实际上是某种“误认”,然而这种误认对于抚慰诗人心灵上的创伤和人格分裂的痛楚来说又是必需的。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于一个话语主体而言仅仅停留在表层的意识层面上,而不是积淀至无意识深层,那么它就还未能完成对话语主体的重塑和“再生产”。对于何其芳来说,真正的误认便是他对红色意识形态及其文艺规范的完全接受,使其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本质”,即“无意识”(杰姆逊语)。诗人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并最终“消失在它们里面”。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何其芳写于1942年的诗句:“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鸟雀未飞时收敛着翅膀/你呵,你为什么这样沉郁?/有些什么难于管束的东西/在你的胸中激荡?”诗人接下来这样回答了自己的发问:“我在给我自己筑着堤岸,/让我以后的日子平静地流着/一直到它流完,/再也不要有什么泛滥。”(《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