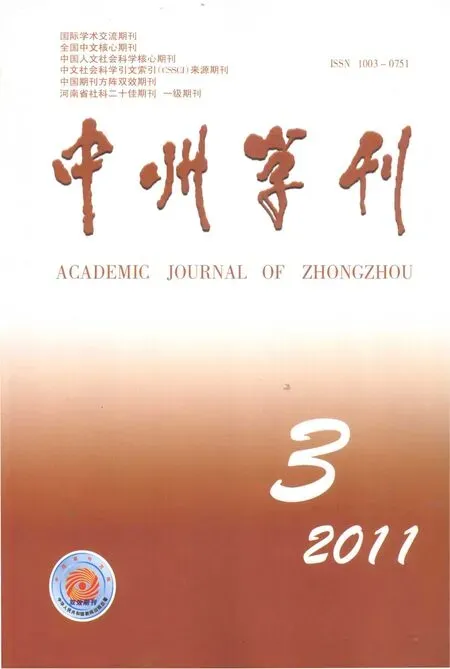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黄丹纳
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黄丹纳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因为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复杂,工业文明发展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内涵”。新声诗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并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呈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现代性;中国内涵;新声诗;历史演变
“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近20年来新诗研究和批评的一大热点。以现代性作为新诗研究的新视角和贯通线,对百年来新诗发展的历史道路、成败得失进行整体审视,对建构中国现代诗歌学,特别是建构中国现代诗歌史学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综观近20年来新诗现代性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局限于所谓新诗的“内部研究”,二是所谓“新诗”依然等同于“欧体欧风”、“译体译风”的“自由诗”,而占有“新诗”或“中国现代诗”半壁江山的“新声诗”或称“歌诗”,依然无人问津。
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的说法,本来是有为而发的。它意在纠正过去的文学史“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的现象。但它同时承认“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的研究法“在作品释义上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只是不能以此代替“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①而已。区分文学“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家,其本意不是让人只搞文学的“内部研究”,特别是关于“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更是“内部研究”所难以完全承载的沉重话题,只能将所谓“内部”与“外部”作为一个整体中既彼此有别,而又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作既分别又综合的研究。
至于“新声诗”迄今仍被排除在“新诗”或“中国现代诗”研究的主流之外,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诗歌变革和诗论变革的历史悲剧。关于“新声诗”在中国历代诗歌史,特别是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思想价值、美学价值,笔者已有专文作了初步论述②。而揭示“新声诗”的现代性,则是事关恢复“新声诗”在“新诗”或“中国现代诗”中“合法地位”的另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而要论证“新声诗的现代性”,还必须从“现代性”谈起。
一、现代性的“中国内涵”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理论问题,中外学者对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作出了各种不同的阐释,这里无须一一列举。其中也不乏能对现代性问题作整体把握者,最有代表性的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具体说来,包括“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复杂的经济制度”和“一系列政治制度”等。他还特别指出:现代性“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另外,当代法国一些掀起“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对现代性体现的一整套“共识法则”所作的概括,也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例如,让·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三大“原则”,或者说三大历史特性:“一是坚信客观真理和绝对正义,抱着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二是跟随启蒙精神及其理性主义,让‘工具理性’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准则,结果是从宗教迷信走向了科学迷信;三是奉行普遍功利主义和社会福利原则,市场逻辑和享乐主义并行,让现代人受制于‘物化’的现实。”③还有一些中外学者持所谓“多重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对现代性的性质及不同文明国家的现代性的解释上”主要有三种说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所要论述的是世界的同质化;而与此相反,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则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针对这两种观点,艾森塔德提出第三种论断,将当今的世界看作是属于一种多元现代性的世界。”④但不管人们从什么立场出发,取什么视角,作出怎样的理论表述,总之,所谓“现代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人类工业文明阶段的社会历史特性。它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或现代社会,也不能局限于观念层面的、精神性的、人性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久已定型的僵死的公式,而是一个从过去走来的、至今还并未终结的、开放的、人类工业文明阶段的社会历史特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工业文明阶段产生的“现代性”,既有其历时的自身发展、流变的阶段性,又具有共时的国度、民族的差异性、多样性。正如艾森塔德所指出的,当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之初,人们曾有过人类文化将由此走向以西方现代文化为范型的“同质化”的预期,但是人类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展开,却深刻地表明“多元现代性或对现代性的多元解释获得了不断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趋势,切断了现代性与其‘西方’模式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权。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欧洲或西方的现代性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它实际上只是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形式”⑤。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已经走过的和现在正在走着的工业文明的历史道路为依据,具体揭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对“中国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之类的概念作出界定。
从世界各国建设工业文明的历史道路来看,既有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发展阶段有别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历史共性,也有国家、民族、地区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及所采用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就前者而言,世界上凡是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的国家、民族、地区的现代社会的历史特性,都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就后者而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现代性,又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内涵。甚至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其现代性的具体内涵也会有所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迄今为止的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昭示我们:“现代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原发型的、以欧洲各大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性”和后发型的、以亚、非、拉美的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性”。其中,后者又包括两个子类型: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种特点不同的“现代性”。据此,我们也可以将“现代性”概括为三个类型,即“原发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后发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发型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探求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特殊复杂的中国国情和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曲折道路。探求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只能以中国工业文明从萌芽到展开再到转轨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西方原发型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为参照,不能以西方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为依据、为标准,更不能以个别带着“西方中心论”有色眼镜的西方学者的个别论断为绝对真理。
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曲折、坎坷,命运多舛。从明代后期直至今天,可以粗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体上是从明代后期到鸦片战争前后。这是内生性、自主性的,其特点又不同于西方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早期的“原始工业化”的、中国工业文明的发轫阶段或中国特有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二阶段大体上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殖民者以暴力打断了中国内生性、自主性“原始工业化”进程,将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行程强行推入一个特别复杂艰辛的阶段,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先后选择了三种不同的工业文明方向;三者间波澜壮阔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这一阶段现代性“中国内涵”的历史奇观。第三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今天。这是曲折艰辛的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模式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之路的探索、实践到自觉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上,每一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解决的矛盾、所完成的任务,既是先后贯通的,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地、发展着的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既有历史的连贯性,又有阶段的差异性。
显然,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既不同于任何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不同于其他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其他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我们探求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固然不能忽视一切类型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共性,更不能漠视中国道路的民族个性。甚至可以说,后者才是我们探求的重点。只有抓住这个重点,才能真正求得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才能使我们有一个评价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正确标准,才能让新声诗的现代性落到实处。
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在“原始工业化”阶段上所具有的原发性、内生性的基本特征从明代后期开始,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层面上展开了,它与西方原发型工业文明不同的民族特性,也已经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从整体上看,二者的基本差别就是内生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表现在内生性工业文明的早期,其基本的历史特性分属于和平型、暴力型两种不同的类型。在明代后期,中国当时的“白银资本”已相当强大,白银的大量流入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质量、规模。当时的中国虽不免有天朝、上国的自我期许,但对世界各国基本上是以礼相待、和平交往、友好通商,没有强占海外寸土以为殖民地,甚至还受到倭寇及荷兰殖民者的伤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复杂、多元的民族构成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干扰或阻滞了内生性“原始工业化”的自然进程。明清易代,中国和平型的工业文明之路被严重阻滞。与此同时,西方暴力型的原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却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在“原始工业化”阶段,本来同西方大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但我们今天却不能因此抹煞中国本已萌生的早期工业文明的历史事实及其呈现出来的民族特性。
在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其基本的历史特性表现为各种不同社会力量选择的三种不同的工业文明方向、道路的斗争、博弈。西方列强和继起的日本,力图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世界体系的附属品;如果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着眼,这也可以归入广义的“现代性”范畴。与此同时,中国先进的爱国志士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力图建成自主的、健全的、后发型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爱国志士们在运用各种方式反抗殖民化的同时,在列强间诸多矛盾的缝隙中,先后尝试着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逐步推进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但是,无情的现实向中国人宣告:此路不通。中国先进的志士、精英不得不总结失败的教训,而另觅救亡之道、强国之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人们逐步发现了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崭新道路。于是,这便有了第三条道路。
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世界体系强加给中国的殖民地型工业文明道路,既使中国产生、发展了工业文明的某些普世要素,同时又构成了中国发展后发型健全、自主的工业文明的最大障碍;其社会历史特性,就前者而言,具有一定“现代性”;就后者而言,则有着“反中国现代性”的特质。所谓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或“中国现代性”应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进行的独立自主的、健全的后发型工业文明变革时代的社会历史特性。在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内部又存在着两条道路三种方式的博弈、互动和互补。所谓“两条道路”是指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道路和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道路。所谓“三种方式”,简要地说就是“革命”、“西化”、“本土化”。杨春时先生把它们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现代性思潮”,并分别命名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中虽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方向,但都主张首先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打碎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为实现独立自主的、健全的后发型工业文明扫清道路,进而独立自主地逐步展开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自己的工业文明;“自由主义”则主张按照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实行“全盘西化”;而“保守主义”却主张主要靠开发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创建中国本土的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中国变革的历史事实来看,“激进主义”是“主流”,主导着这一时期工业文明变革的历史方向,但自由派和保守派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作为中国现代性思潮的两个方面军,对“主流”不仅始终保持着干预和制衡,甚至在许多方面被主流派吸纳并实践。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本身就是以激进派为主导的“革命”、“西化”、“本土化”三大“现代性思潮”的辩证发展、辩证综合。不过,在这一历史阶段上,无论走哪条道路、用哪种方式创建后发型工业文明,都必须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前提。因此,反殖民主义是现代性“中国内涵”的逻辑起点,也是本时期现代性“中国内涵”的基本内容。我们评价本时期“新声诗”的现代性只能以此为主要依据。
中国工业文明之路的第三阶段,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内地)、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台湾)、殖民地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香港、澳门),从分立、并存到共生与逐步整合。在这一历史时期三个分属于不同类型工业文明的地区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社会特性,共同构成了本时期现代性“中国内涵”的多重复合的整体。如此特殊的国情,如此复杂的多重复合的现代性内涵,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过祖国大陆毕竟是中华民族推进后发型工业文明的主体部分,其社会变革的历史道路、成败得失及其呈现出的历史特性代表着现代性“中国内涵”或“中国现代性”乃至“中国新现代性”的主流或基本内容。祖国大陆推行的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变革,极其鲜明、强烈地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一切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个性特征。自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益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推动下,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思潮的兴起和中华民族内部不同类型工业文明的并存、整合,更使中国的工业文明呈现出新的、独一无二的现代性特征,所以有人将其命名为“中国新现代性”。虽然人们对中国工业文明的新特性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说它“新”与“独一无二”则是无可置疑的。
二、新声诗现代性的历史演变
不管人们如何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所谓“内部研究”的重要性,文学变革总是同人和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的;虽然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所以,我们考察新声诗的现代性,就只能将所谓“内部”与“外部”看做有别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新声诗的现代性,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恰恰是更鲜明、更强烈、更具体地表现出同所谓“外部”即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特性间的激发与互动。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它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体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呈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就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一)新声诗的第一次浪潮
新声诗的最初形态是明代中后期的“市井艳词”。它是伴随着明代中后期“原始工业化”的推进,表达民众反抗传统礼教、追求人性解放的历史诉求而到处歌唱的新韵文。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精英,很早就发现了它的不朽价值,如李开先、冯梦龙等人,与民间艺人一道,从事“市井艳词”的搜集、整理、刊印、传播工作。李开先在他所编的《市井艳词》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些“艳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初学言者,亦知歌之。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⑥。这种依托民间音乐,表达新的历史诉求的新民歌,发展到清代,不仅创作、整理盛况有加,而且演变出品类繁多的民间说唱和地方戏曲。这种表达民众新的历史诉求的新型声诗,进一步丰富、提高,更加普及,可谓初步具有了早期文艺现代性的“大众性”品格。
新声诗是在中国工业文明推进的第二阶段逐步成熟的。新声诗正式诞生的历史性标志是“学堂乐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启迪和殖民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的先进精英们,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把创建自主性、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大幕正式拉开。现代教育制度、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性文艺变革运动中“诗界革命”和“音乐改良”的展开,使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它代表着中国的先进精英向西方寻求真理、唤起民众、挽救危亡、变法图强的精神取向,其本身就是中国后发型自主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变革的一部分,所以它诞生伊始就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创作者是中国最早一批接受了西方音乐系统训练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等。早期的学堂乐歌多采用现成的外国歌曲和我国的民间曲调填上新词。1902年,李叔同创作的《祖国歌》就采用了民间乐曲《老六板》的旋律;同年,沈心工创作的《男儿第一志气高》则选用了一首日本的学校歌曲的曲调。歌词是语言通俗、形象鲜明的白话诗,这比通常作为“新诗”诞生的历史标志——胡适“尝试”的白话诗,至少早了十多年。李叔同擅长抒写个性化的情感体验,所选曲调多为欧美清新优美、婉转流畅的通俗名曲,所填歌词则优雅清丽、意象生动、韵味十足,其意境之美同先有的曲调融合得天衣无缝。
学堂乐歌后期的新声诗创作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不仅选曲填词转向自创词曲,而且艺术性较强的独唱、合唱、诗剧和形式新颖、童趣盎然的儿童歌舞曲也登上了舞台。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是后期的代表作家。赵元任对新声诗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语言学家和作曲家,他将现代汉语的声韵规律同音乐曲调完美结合,对新声诗曲调的民族化作了深入而广泛的探求。他与多位诗人合作,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使学堂乐歌走出学校,走向了社会。著名作品如大型艺术性合唱《海韵》表现了一代青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卖布谣》、《织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呜呼三月一十八》则是对反动军阀政府的愤怒抗争。
黎锦晖开创了儿童歌舞剧这种声诗新形式。1920年,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同时在“卷头语”中提出了以“美育”改造国民性等主张。他按照儿童特点和兴趣选择题材,运用浅显、生动、形象、亲切的儿童语言编写歌词,音乐创作也合乎童心、童趣,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在儿童声诗创作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27年所写的组诗,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均属上乘。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农夫歌》、《儿童工歌》、《手脑相长歌》、《自立立人歌》等,都曾唱遍全国。其中赵元任为之谱曲的就有五首以上。
作为新声诗第一浪潮的“学堂乐歌”,其“声”是以西洋音乐理论、西洋音乐规范、西洋艺术方法为主导,融合民族、民间音乐要素而创作出来的具有鲜明现代品格的“新声”;其“诗”的语言形式,大多采用白话或接近语体的浅近文言,具有与西乐规范相合而又自由、自然的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节调、韵律。这与传统的以文字型文学语言写成的、格律精严的各体古典诗歌相比,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自不待言。至于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创造的境界,则更是集中表现出当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爱国反帝、改造国民精神品质,独立自主地走工业文明之路的历史诉求。至于它对教育制度近代化,特别是审美教育、音乐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更是直接属于建设工业文明之制度层面的变革。总之,时代性、开放性、自主性、民族性的自觉追求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性的“中国内涵”。
(二)新声诗的第二次浪潮
随着中国殖民地化危机的日益加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先后进行了两次全国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实质是三个不同的中国工业文明道路的决胜、拼杀。抗日战争是“救亡”,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的工业文明之路而对日本军国主义殖民者的拼死抗争。解放战争则是中华民族内部对两条不同的工业文明之路——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之路的抉择。战争的结果是国民党退居台湾依然坚持前者,共产党领导祖国大陆选择了后者。两条道路虽然不同,但中华民族则共同战胜了殖民主义,取得了发展自主性工业文明的决定性胜利。战胜殖民主义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发展自主性工业文明的历史前提,也是本时期现代性最突出的内涵。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新声诗创作是围绕着抗日救亡而展开的,一大批活跃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新声诗的创作。这不仅使新声诗表现的思想内容极大地丰富起来,成功地塑造出了革命战争年代各阶层人物,特别是抗日英雄的生动形象,而且从整体上把新声诗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推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声诗传播的新方式——亿万民众参与的第一次群众性歌咏浪潮,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的文艺家,首推田汉,还有光未然、公木、麦新、安娥、塞克、孙师毅、桂涛声等;而为新声诗谱写了众多动人乐章的音乐家,则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吕骥、张曙、张寒晖、刘雪庵、江定仙、夏之秋、孙慎、郑律成、李焕之、孟波、马可等。
本时期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堪称是新声诗的历史丰碑。此外,既有慷慨激昂的呼号、呐喊,如《毕业歌》、《大刀进行曲》;也有对侵略者滔天罪行的血泪控诉,如《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更有对英雄人物、英雄行为、英雄精神的热情赞颂,如《歌八百壮士》、《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延安颂》。这些作品不仅全方位地描写了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的宏伟图景,而且在新声诗创作,或者整个新诗创作所遇到的历史性难题方面,较成功地解决了文学语言口语化与艺术性的矛盾、表现时代的宏大主题与反映广阔社会生活、满足不同阶层的多种精神需求的矛盾。如《松花江上》以口语常言,直击亿万民众的心灵深处,几乎把口语化文学语言写情述事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毕业歌》将雅言同口语融合得天衣无缝。在反映生活的丰富性和体裁、风格的多样性,多侧面地表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心理状态,力图满足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方面,也同样创作出了许多不朽名作,如《玫瑰三愿》、《渔光曲》、《夜半歌声》、《铁蹄下的歌女》、《秋水伊人》、《四季歌》、《天涯歌女》、《读书郎》、《茶馆小调》、《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何日君再来》等。在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以及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区则产生了许多歌颂新生活的佳作,如《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
总之,对表达现代性的“中国内涵”而言,无论时代特征的鲜明性或生活内容的丰富性,形式、风格、趣味的多样性以及与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结合、互渗的广泛性,特别是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无不参与的空前未有的群众性,这一时期的新声诗与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文艺样式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或有过之。而这恰恰是现代性“中国内涵”最突出的民族特征。
(三)新声诗的第三次浪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两条工业文明之路并存的时期。新声诗创作都以鲜活的生命力长足发展,但因两条工业文明之路的不同,其现代性的具体内涵也根本不同。台湾、香港、澳门大体属于同一类型,走的是自由化、商业化、感官化、通俗化甚至是低俗化的消费型大众文艺之路;内地走的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的政治化、普及化的宣传型社会主义的大众文艺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后,两条道路从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就祖国大陆部分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新声诗创作、传播,以“文革”为界,又有前17年和后13年的分别。
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十七年”时期,这是新声诗史上群众歌咏的第二次高潮。但人们所唱的不再是呐喊、呼号的战歌、悲歌,而是各类题材的昂扬颂歌。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刚刚开始进行探索,人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和民族的豪情,歌唱新时代,歌唱新生活,歌唱新国家的主人。虽然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情势下,精神环境并不宽松,人们却依然热情地歌颂革命历史、建设成就、英雄情怀,也不时地以抒情之笔赞美青春、吟咏爱情。
堪称新中国第一颂歌的是王莘的《歌唱祖国》,至今仍流传于亿万民众中。另一首歌唱祖国的名作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爱你,中国》。颂歌题材、风格也是多样的,数量最多的是歌唱工、农、兵和少数民族生活的声诗,被广泛传唱的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克拉玛依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马儿啊,你慢些走》、《人说山西好风光》、《新疆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牧歌》、《逛新城》、《翻身农奴把歌唱》、《乌苏里船歌》、《阿瓦人民唱新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此类作品,语言大多是口语化、通俗化的;而乐曲则多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民族特色,在新声诗中别具一格。歌颂人民军队的《我是一个兵》家喻户晓;《打靶归来》也早已唱遍全国。《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三杯美酒敬亲人》、《洗衣歌》等,赞美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少儿歌曲是歌颂新中国声诗中的一朵奇葩。《快乐的节日》、《我们的原野》、《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一大批久唱不衰的名作,无论是生活内容、童心童趣,还是曲调之美、诗句之佳,都远远超越了前人。
革命历史题材的颂歌也可谓成绩辉煌。多乐章大合唱、歌剧都属于大型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单是其重要唱段已广为普及的名作就有《洪湖赤卫队》、《长征组歌》、《江姐》、《红珊瑚》等。
歌咏爱情的声诗,虽然处境艰难,但也成就不凡,如《清粼粼的水来蓝蓝的天》、《三十里铺》、《山对山来崖对崖》、《九九艳阳天》、《婚誓》、《敖包相会》、《蝴蝶泉边》、《草原之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被称为“中国式小夜曲”的《草原之夜》,其宏阔悠远的诗境,绵邈无尽的思念,忠贞不渝的互信,含蓄、深沉、柔婉的格调,将那个时代特有的爱情范式典型化了。
本时期的第二阶段是“文革”10年及其余波。“文革”10年是新声诗创作最为暗淡的时期。横行无忌的“造反歌”、“战斗歌”“假大空”、“高硬响”,与声诗无缘。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产生了《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湖美》、《太阳岛上》等,像暖雨轻风,抚慰了人们长期紧绷的心弦,也宣告中国新声诗创作一个时代的结束。
(四)新声诗的第四次浪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具有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特质的大众文艺从碰撞逐步走向融合。中国内地的新声诗创作便正式跨进了大变革、大繁荣的新时代。一是个体本位的主体意识的跃升,人们更多地把新声诗的创作、鉴赏、传播看做个人的生存方式、自我实现的需要、个体生命的状态和个人情感的宣泄、精神的满足。二是新声诗的创作、演唱、接受被纳入由城市引领的大众文化的潮流。除了专业文艺家、当红歌星之外,形形色色的唱片、音像制作人和具有先锋意识的城市青年往往左右着商业卖点和创作潮流;而演唱和接受则是视“歌星”为导向的、以城镇青年为主的平民大众了。三是演唱方式的个人化,传播方式的光电化、商业化、消费化。四是对港台和世界先锋性艺术新资源日益深广的利用、开发。这一切,特别凸现了新时期新声诗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或中国“新现代性”。
在这个时期,新声诗创作潮起潮落,冲走了泥沙,留下了珍品。一方面,情调健康、艺术性强的港、台流行歌曲大量传入内地,使内地乐坛乃至年轻一代的心灵风云激荡。在所谓“抒情歌潮”中出现的《军港之夜》、《美丽的心灵》、《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嘀哩嘀哩》、《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银梭》、《请到天涯海角来》、《大海啊,故乡》、《那就是我》、《小草》、《难忘今宵》等,大大拓展了表现情感的领域,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民族情、故乡情、师生情,以及对自然风光的赞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青春时光的珍惜,对军旅生涯的热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等等,都表现得自由而富有个性。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有的豪迈,有的柔婉,有的清新,有的淳朴,有的灵动,有的典雅。至于作为歌曲之本的诗,不少作品语言之新,想象之奇,单凭“眼看”,已属佳作,“嘴唱”出来更是分外动人了。如儿童诗《嘀哩嘀哩》,乡情诗《那就是我》,想象新奇,诗境如画,“真”到了极致,“活”到了极致。
以《让世界充满爱》为标志,中国内地流行歌坛开始自立。这部作品立意深刻,情怀博大,充满现代气息。崔健喊出的《一无所有》,既唤起了中国流行歌坛的“西北风”潮,又把世界流行的摇滚音乐同中国新声诗创作正式连在了一起。从此,中国内地的新声诗创作进入了一个以大众文化为主潮,依托通俗、美声、民族三大声乐流派的多元并存、辩证发展的新阶段。“西北风”之外,也出现了很多佳作,如《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爱的奉献》、《七色光之歌》、《今天是你的生日》、《好大一棵树》、《唱脸谱》、《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弯弯的月亮》等,成就远远高于“西北风”。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声诗创作进入一个以通俗化、多样化、个性化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突出的特点是自由抒写广大民众的情感百态,对传统民俗的依恋,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对现代人心灵世界的解剖以及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迷惘与探求……笔触探及现实生活、民众心灵的一切角落。而歌唱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新变革为基本内容的“主旋律”声诗作品,更唱出了鲜活的内容、生动的形象、浓浓的情味,名篇如《亚洲雄风》、《爱我中华》、《同唱一首歌》、《青藏高原》、《走进新时代》等。这时歌坛上涌现了众多的优秀音乐人,如乔羽、阎肃、张藜、晓光、凯传、蒋开儒、张千一、崔健、陈哲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总之,百年以来的新声诗,连接古今,沟通中外,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作了极为全面而有益的探索,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展示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
注释
①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65页。②黄丹纳:《新声诗初探》,《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③欧阳谦:《当代法国哲学与“新启蒙运动”》,《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2期。④陈嘉明:《现代性对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光明日报》2008年3月25日。⑤转引自李翔海:《论“以中释中”》,《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⑥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1]陈支平.晚明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J].河北学刊,2008,(1).
[2][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3]毛佩琦.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J].河北学刊,2008,(1).
[4]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5]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J].文艺争鸣,2008,(2).
[6]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J].河北学刊,2008,(1).
I207.25
A
1003—0751(2011)03—0243—06
2011—03—15
黄丹纳,女,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讲师(北京 100083)。
责任编辑:一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