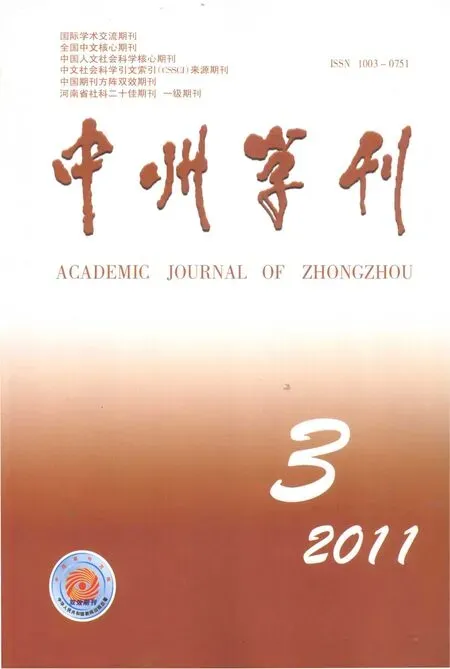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王建生
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王建生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南宋初;最爱元祐;文化重建;统绪
一、“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
“最爱元祐”,是南宋高宗的金口玉言。绍兴四年(1134)八月,宋高宗与范冲君臣二人进行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对话,内容涉及政体、史事、史籍、人物评价等等。关于此次君臣对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详细记载,现征引于下:
范冲入见。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笔者注:指《神宗实录》、《哲宗实录》)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读毕,上顾冲云:“如何?”对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①
上引宋高宗君臣对话,是南宋初年围绕政治文化建设纲领而进行的集中讨论,也是要对外宣示新政权的“所本”与“所因”。这一纲领,是对包含元祐之治在内的元祐资源的认同。就政事而言,宋高宗君臣舍熙宁、元丰而取元祐,延续了北宋后期以来褒此贬彼的路线。废新法、复旧政、贬逐新党,或是绍述新法、贬逐旧党,数度反复。直至宋钦宗即位,为了清算蔡京、王黼等人的罪行,“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②。虽然伴随着北宋的覆亡,宋钦宗复归元祐的作为没来得及施展,但这种路线却被新建立的赵构政权所承继。宋高宗君臣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评判,表明了南宋朝廷“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这实际上附带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与王安石变法的熙、丰政事相比。
这种附带与比照的背后,隐含了高宗为君父开脱罪责的历史动机。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及以蔡京为首的绍述党,成为变法及绍述的完全责任人,背负起尽变祖宗法度、误主亡国的罪责。在靖康围城的大变局下,士大夫将北宋亡国的责任,多追溯于宋神宗变更祖宗法度所致。而王安石则被指认为祸胎之源。所谓“安石之不利赵氏,其实迹可见”③,也就是上引范冲奏对时所说“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南渡后,有关王安石变乱法度、败人心术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词。王安石新法开启蔡京集团乱政之源的看法,逐渐占据主流。宋高宗君臣对王安石新学极度反感的背后,竭力构筑的是北宋神宗以来帝王圣明的形象,证明赵宋王室并未失德;之所以造成二帝北狩,原因在于用人不当。这样,在赵宋王室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皇位的承继便合法、合情。
在“最爱元祐”的基调下,南宋朝廷政治措置也有意向所谓的“元祐之治”方向努力。在用人策略上,褒录元祐子弟。据史载:“(赵)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去赃吏,进正人。”④这既可以看作是赵鼎对“最爱元祐”说的回应,也可以说明执政者对元祐资源的认同与尊崇。在经历十余年的措置后,至绍兴六年(1136),南宋朝廷初具规模,甚至有“小元祐”⑤之说。元祐作为治世典范,成为当时政治评论的参照系,反映了南渡士人对元祐之治的集体性膜拜。
二、推崇元祐学术的文化政策
宋哲宗绍圣以来,元祐学术受到排斥。党禁的危害,不仅仅在缙绅阶层,还蔓延到学术、思想等领域,“绍圣间党论一兴,至崇、观而大炽,其贻祸不独缙绅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叹恨也”⑥。崇宁以来,元祐学术又长时间内受到禁锢。以文学而言,诗赋成为朝廷法令禁止的主要对象,甚至有“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⑦之令,诗歌的创作主体受到干扰与冲击,“畏谨者至不敢作诗”⑧。这促使了某些本来信奉元祐学术的士人改变了自己的学术取向,如王安中初从晁说之学,其后密结梁师成,“与晁氏兄弟绝矣。既长风宪,位丞辖,讳从晁学”⑨。同样,理学的处境也很艰难,崇宁二年(1103)四月,“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察觉”⑩,也就限制了程氏学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程颐迁居洛阳龙门之南,阻止四方学者来问学。司马光、范祖禹等人的史籍,同样面临被禁的命运,司马光文集、范祖禹《唐鉴》均被毁板⑪。直到靖康元年(1126)二月,朝廷才解除元祐学术之禁。南渡以后,朝廷在文化政策方面推崇元祐学术,对此前禁锢元祐学术的政策及时进行了调整。
首先,删除禁止传习诗赋的政令,矫正科举罢诗赋的弊端。建炎二年(1128)五月,重新恢复了“科场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词赋者近四十年。(王)綯在后省,尝为上言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上以为然,至是申明行下”⑫。十月,大理少卿吴环言:“国家科举兼用诗赋,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诗赋私相传习之禁,尚未删去,望令刑部删削。”⑬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朝廷颁布的科场取士法,恢复了元祐之制,也就意味着官方对王安石及绍述新党专以经义取士的否定,为元祐学术尤其是诗赋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对于那些不曾参加北宋经义科考的士人,南宋政府有选择地给予了出身资历。先后获赐进士出身者,有韩璜、徐俯、王蘋、周孚先、朱敦儒、吕本中、陈渊,等等。此外,任申先不由科举而被任命为词臣,亦属破例。以上所举赐进士出身者,或以文学名家,或以思想见长,但大多数是元祐之学的传人。不参加北宋科举而在南宋能获取官方颁布的出身资历,说明了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禁元祐学术对士人的影响,南宋政府的作为也算是对既往科举之失的弥补与矫正。
“元祐之学鸣绍兴”⑭,与元祐政事的回归互为表里,也即“最爱元祐”的纲领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具体落实。在南宋政局尚未完全稳定之时,官方推崇元祐的文化政策,其初衷无外乎服务朝廷政事、收揽人心、维系民望。胡寅曾列举了宋高宗在这一时期的部分举措:“笃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废之《春秋》,又于讲筵进读神祖所序、司马光所纂之《通鉴》,下杨时家取《三经义辩》,置之馆阁。选从程氏学士大夫渐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孙之有闻者,仍追复其父祖爵秩。将以刬削蛊蠧,作成人物,朝冀贤才之赖,国培安固之基。”⑮朝廷推崇元祐学术的意图,正如胡寅指出的,要“作成人物”,为朝廷网罗安邦定国的贤才。
元祐学术的复苏,得益于官方的文化政策,而主要的途径则是通过朝廷的用人政策来实现。自建炎南渡以来,朝廷改变了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对其子弟及后学也推恩录用。绍兴六年前后,朝廷对于元祐子弟及后学的任用因赵鼎执政而达到空前的高度。元祐党人的子孙及元祐学术的传习者大量地参与南宋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如晁补之之子晁公为、范纯仁之子范正舆、陈瓘之子陈正由、范祖禹之子范冲、黄庭坚外甥徐俯、吕希哲之孙吕本中、常安民之子常同,等等。同样在绍兴初年,陈与义、朱敦儒等以文学名家者相继进入朝廷权力中心。这标志着元祐学术真正意义上突破党禁束缚,步入正常轨道。官方的褒崇,为元祐学术的复苏与张扬提供了政治支持。不过,理学因与政治的纠葛,不断经历坎坷与不平。随着赵鼎离任,很快就有陈公辅上疏请禁“伊川学”;此波未平,又有秦桧专权时期对洛学的打击,故呈现出复杂的发展轨迹。
与理学相比而言,文学自南渡之后踏上一条相对平稳的发展路子。官方禁令取消后,苏、黄文学重获自由,社会上兴起了苏、黄文学热。曾在民间私相传习的江西宗派诗人,南渡后命运发生重大改变,或被朝廷委以重任,或声名远扬。关于《江西宗派图》的写作年代,目前学界尚无定说,但直到南宋初年才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故南宋人多认为《宗派图》为南渡后所作。江西宗派之所以在南宋盛行,离不开官方推崇元祐的政治文化取向这一根本原因;朝廷改变对元祐诗歌、诗人的态度,本来就是官方推崇元祐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南宋后期郑天锡对于江西诗人盛名南宋的现象看得很透彻:“人比建安多作者,诗从元祐总名家。”⑯“诗从元祐总名家”,凡是沾溉元祐诗歌遗泽的诗人,总会“名家”的。在江西宗派诗人中,徐俯荣登执政大臣之位。除了徐俯之外,吕本中也是被宋高宗称赏的当下诗人。就诗歌写作实际及影响力来看,徐俯与吕本中称得上南渡初年诗坛的领军人物。而在“最爱元祐”的语境中,作为元祐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苏轼文学更备受青睐,社会上掀起了“崇苏热”。陆游说道:“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⑰甚至有“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⑱的说法。除了苏、黄文学之外,南渡文人还在其他领域有意推崇元祐文章,如汪藻痛扫“崇、观词臣以扇对全语为高”之弊,“尽复元祐之旧”,表明南渡之后元祐之学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其影响力。
三、文化统绪的承续
自南宋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导向后,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与官方构筑正统的努力形成了有效呼应。尤其是活动于这一时期的元祐子弟,在构筑文化统绪时,无论是理学,还是文学,都将元祐之学作为文化传承系统中的关节点。
1.理学统绪的承续
政和二年(1112)七月,程端中在程颐文集的序中说道:“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后,天下学者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⑲明确指出程颐直承孔孟不传之道。程端中的说法较早,不过,随着杨时、尹焞、胡安国等人大力阐发,到了绍兴初年,也就是程门弟子们的晚年,道统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已经无可争议:二程以承接千载断绝之“道”,成为孔孟精神的直接承传者。绍兴六年(1136)朱震论二程得孔孟之真传,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他说:“臣切谓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后无传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于千有余岁之后。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其高弟曰谢良佐,曰杨时,曰游酢。”⑳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理学统绪中的整理中,杨时的道南一派被凸显,其中隐含着深意,体现了道统的政治文化功能。元代杨维桢所上《三史正统辨》表中,有这样一段话:“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㉑杨维桢这段话本是为了强调元朝的正统地位,但他的证据中明确地指出杨时道南一派与宋室南渡之间的关联,即“道统”乃“治统”的合法性依据。
2.文学统绪的承续
在北宋文学史上,欧阳修将“斯文”授予苏轼。苏轼不负其托,后又将其交付黄庭坚。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传承的脉络非常明晰。吕本中在《宗派图序》中说道:“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祕,亡余蕴矣。”㉒认为黄庭坚承继元和以来衰落的诗统,意在确立黄庭坚→江西诸派为诗歌的正脉,黄庭坚“遂为本朝诗家宗祖”㉓。在两宋之际的文学叙事中,有一种说法,即“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㉔,将苏、黄分别作为文、诗的宗主。
苏文、黄诗并立,是后学基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重新定位:苏轼的文章更适合作为科场应举、制策时的范文,黄庭坚的诗歌为学诗者提供了“规矩”和“法度”。而且,将苏文、黄诗并立,并没有将苏诗排除在外。对于学诗者来讲,那就是要以苏、黄诗作为范式。陈与义的诗学主旨可为代表,他说:“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近世诗家知尊杜矣,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㉕将苏、黄同树为范式,精研他们的诗歌,知其“为”和“不为”。
论文者宗苏,言诗者以苏济黄。他们绍续的都是元祐之学的精髓,也就表明南渡后的文学,无论是诗,还是文,都源于正脉嫡传。不论苏轼还是黄庭坚,都是植根于北宋文化土壤,代表着文化的正脉,同时也是文化传承中的关节点。而对于南渡文人来说,他们更直接的任务就是绍述北宋文化的正脉。
南宋初年,无论是理学还是文学,在构建统绪时,统绪中的核心人物如二程、苏轼、黄庭坚等,均为元祐之学的主力人物。北宋后期,虽已有江西宗派的诗学在民间承传,但南渡后元祐学术全面解禁,朝廷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无疑为统绪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元祐学术为承接点的统绪构建,既是学术整理,同时也是文化接力。士人将丧家亡国的耻辱和伤痛,转化为文化承传的动力。实际上,这已是一场文化拯救运动。
综上所述,南渡初年宋高宗君臣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确立了“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此导向的作用下,北宋后期作为禁锢对象的元祐之学,此时得到官方的推崇,苏黄文学、二程理学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终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就政事而言,取元祐而舍熙、丰的基本导向并没有改变;元祐之学也成为南宋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承传元祐之学,推动了文学、理学的更新与发展;此后的中兴文人深受南渡文人的影响。他们追慕元祐文化,并确立了文学中兴的使命。南宋前期的文学中兴与理学兴盛,都导源于这一历史语境。
注释
①③④⑫⑬⑳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 年,第1289—1290、1296、1413、316、361、1660—1661 页。②⑩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424、367页。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6页。⑥⑨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第103、185页。⑦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⑧葛立方:《韵语阳秋》,载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524页。⑪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 年,第482 页。⑭袁桷:《书黄彦章诗编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丛书集成初编本。⑮胡寅:《斐然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404页。⑯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188页。⑰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 100 页。⑱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⑲程端中:《伊川先生文集后序》,《二程集·目录》,中华书局,1981年。㉑杨维桢:《正统辨》,《东维子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㉒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244页。㉓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山谷》,丛书集成初编本。㉔马端临:《经籍考六十三》“黄鲁直豫章集”条,《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六,万有文库本。㉕晦斋:《简斋诗集引》,《简斋诗外集》卷首,宋集珍本丛刊影元钞本。
I207.22
A
1003—0751(2011)03—0208—03
2011—01—10
王建生,男,郑州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郑州 450001)。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