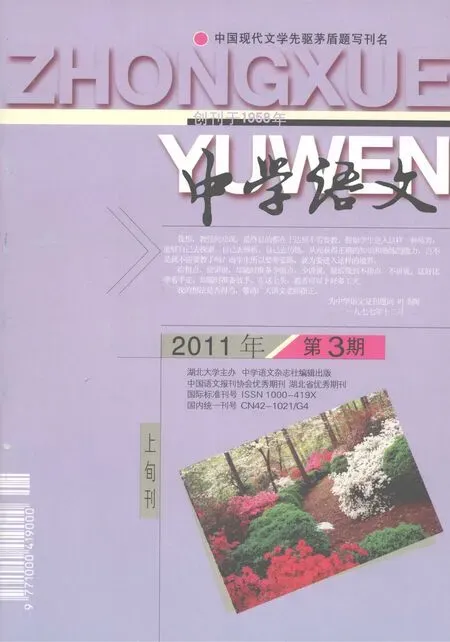傩送会回来吗?
——品读《边城》的悲剧结尾
胡承英
没有结局的故事总是令人伤感遗憾的,但也就是这种伤感和遗憾给了我们更广阔的空间去神往想象。沈从文先生在《边城》的结尾,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让人感伤的疑问:傩送会回来吗?
“到了冬天,那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
小说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我们几乎要责怪作者的残忍了。这么美丽的爱情,这么善良的人物,为什么却是那样的感伤,隐伏着那样剧烈的悲痛?
在此我们应分析酿成这场悲剧的深层原因。
结合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其他题材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创作《边城》的用意在于要跟两种现实进行“对照”:一是用“边城”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相对照;二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在这两种对照中,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所以《边城》这部作品,它以“牧歌”即乡土抒情诗这样一种抒情方式,充分展现了传统和乡土这种诗意之美。它以最贴切生动的形式,把30年代的中国想象、中国形象凝聚成了一个可感的艺术造型,他通过造型化、具体化,把它提炼出来、整合出来,塑造出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这是《边城》最大的贡献,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小说描写了一幅民情淳朴的风俗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他把这个世界写得这样美,他把这里的山、水、人,这里的爱情写得那样的优美,那样纯净。他就是要用这美来唤起人们心中那一点美好的感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人民就十全十美,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
其一就是边城人民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民族心灵的痼疾——宿命的迷信观念。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傩送面对哥哥的死亡,负气地只身下了桃源,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也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
其二,从现实的角度说,傩送的爱情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义和利的选择、金钱和爱情的选择。表现在作品中即是碾坊和渡船的冲突。王乡绅的那座大碾房是一个象征,它时时威胁着翠翠的小渡船。碾坊代表了一种实用的、功利的,以金钱地位为标准的婚恋观;渡船所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出于心灵相互吸引的传统古朴的爱情观。这两种爱情观发生了冲突,二者的取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傩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小小渡船,正因为他坚持了民族的义利取舍标准,所以他在作者心目中成了民族优秀品德的象征。所以他的出走,也就具有了象征的性质,它暗示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失落。
“边城”是作者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在牧歌声中渐渐远去的时代。这可以用沈从文的另一作品《长河》的题记中的一段话来说明:“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而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个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自然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于工作见出在变化中堕落的趋势。”这种变化,尤其是民族优秀品德的失落使作者感到深深的痛惜和忧虑。所以《边城》,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总感到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之不去的阴湿与愁苦,总隐隐地感到作者有点强作欢笑。
严家炎先生曾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从象征层面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桃花源的迷失这样一种图示,我们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的具体背景就是在湘西,桃花源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乐土的形象。但是这个理想的乐土的形象是无迹可寻的,他误闯进去出来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实际上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是一个虚幻的、不可捉摸的,是一种忧伤的印象。而《边城》它的背景是在湘西,他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所叙述的乐园图景给具体化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实际上也是有悲情成分的,这个可遇而不可寻、两岸扑朔迷离的桃花源和再次踏访时寻而不得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亦真亦幻、宛如梦境引出的是一种感伤和惆怅。而《边城》的这种情调可以说也是如此,所以它的象征层面上展示了一个“失乐土”的精神原型。
沈从文为人性的善与美深情地唱了一曲 “牧歌”,但又唱出了特有的忧郁、哀婉的气氛,我们不应该把这首“牧歌”和这种忧郁悲伤的情感或者说悲剧截然的分开。“牧歌”不纯粹是喜乐,它甚至可以更多的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劳伦斯曾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座庙供奉的是‘人性’。”但《边城》结尾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更是精神寻觅不可得的悲剧。
那么,傩送会回来吗?
我想,当正直和热情的民族精神回归的时候,当迷信观念的束缚被层层冲破的时候,当重义轻利的民族品德重新塑造起来的时候,当人们“世外桃源”般的精神欲求能够实现的时候,傩送就会回来的。翠翠的等待正是对这种民族优秀品德的一种呼唤,也是人生精神家园的一次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