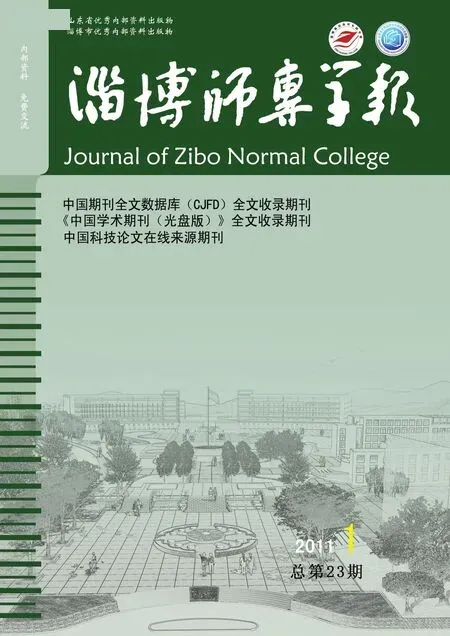最是人间行路难
——析静安词之精神境界
刘远鑫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开宗明义地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1](P2)自杀不仅是对个人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对世界的舍弃,其背后隐藏的疑问就是:世界和人生究竟有没有终极的意义?如果没有,那便是不值一过的。但是,肯如此认真且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并不多见。常人对人生总是得过且过,沉迷于其表象之中,而不肯去深究其根底。诗人、哲学家之异于常人之处正在其对人生之谜的不停追问以及生活态度的严肃不苟且。静安先生则一身兼具诗人之锐感多情与哲人之深思冷静。他所生活之时代又不幸经受了三千年未有的巨变,传统崩溃、文明冲突、价值失范,这对人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世界是否有秩序和正义?人生是否有意义和根据?静安先生终生都为此一世纪末的虚无悲观之思绪纠缠束缚而不得解脱,最终只能举身赴清池,以死亡来结束残破而痛苦的人生。人生对于静安先生而言并不是烛光笑语之温情,亦非醇酒妇人之放荡,而是荒寒孤寂的精神炼狱。之所以如此者,除却客观之历史、社会原因,更多的是静安先生之性格使然,其人生悲剧谓之性格悲剧可也。虽然,其中也沉淀了传统文化的基因,陈寅恪先生便以殉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来解释静安先生之自沉,可参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叶嘉莹先生曾对静安先生的性格特点有过深刻而细腻的分析,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悲观忧郁的天性;“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2](P4-20)笔者认为,静安先生精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困苦在其早年所作的词作里均有极深刻的体现。下面我们顺着叶先生的思路,来探讨静安先生词作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
一
静安先生尝自谓:“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可见,人生问题在静安先生早期的精神生活中确实占据于重要乃至核心之地位。而困扰静安先生之人生问题已不是传统思想中的气质偏暗、私欲害理之类的性气道德问题,而是对人生在世根本意义的形而上追问。这也是他为何对德国古典哲学情有独钟,并沉迷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因。哲学可以引领他深入地观察世界、思考人生,而文学则能宣泄其内心的种种烦闷忧郁之情。静安先生本具此种忧郁悲观之气质,故而其对叔本华哲学的喜爱,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共鸣,定有其已先获我心之惊喜。叔本华悲观哲学的熏染则进一步加强了其对世界人生的悲观看法,使其将世界看作是一个你争我斗的战场,充满了残忍和邪恶,如《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词中乌云密布的天空、寥落凄清的江湖、无时不在的危险正显现出世间的险恶危机,以及生存于其间之痛苦。在这个世界里,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完全隔绝的,你的痛苦之于他者只不过是其盘中美味。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天地不仁的感叹以及透彻骨髓的悲凉。生活在这样的人世间,只会让锐感的词人倍觉压抑。静安先生词里只要提到人间无不带有深深的失望和厌倦:“陋室风多青灯灺,中有千秋魂魄。似诉尽、人间纷浊”(《贺新郎·月落飞乌鹊》);人间乃是作为一种与高远境界相对立的意象出现的:“窣地重帘围画省,帘外红墙,高与银河并。开尽隔墙桃与杏,人间望眼何由骋”(《蝶恋花·窣地重帘围画省》);人间充斥着难防之暗箭和销骨之毁谤,更是令高洁坚贞的词人不堪且不屑:“手把齐纨相决绝。懒祝秋风,再使人间热”(《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在这污浊险恶的人间,只有大自然才是唯一的安静有情之存在:“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入闲庭户。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踏莎行·绝顶无云》)。
人世之污浊冷酷,自古皆然,所谓三代之民正道直行,风俗淳美只不过是后世儒者的美好想象。但正是这种对人类生命之美好的坚信和理想才支撑起人性的尊严,点亮人类的希望。古人之所以将修身作为根本,正是因其怀着天下之风俗系于一人之本的信念,不降志不辱身,在困境中完成自己生命的美好。但人类的生命之花能敌得过时间的侵蚀和无常吗?只有死亡才是必然,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逃不出这个吞没一切的黑洞。静安先生的悲观便在此显现出来,如《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只此一句便写出了生命的悲剧和无奈。静安先生所写者虽为一己之遭际,而能“因个人身世普及于普遍之人生,因一时之感而及于永恒之忧”,此实为静安先生之高于自诉己悲者之处。静安先生精熟历史,早年便曾以《咏史诗二十首》见赏于罗振玉,故能由现实之人生推向深远之历史空间,较之纯为一时感发之作,境界情感更为深沉,如《青玉案》:
姑苏台上乌啼曙,剩霸业,今如许。醉后不堪仍吊古。月中杨柳,水边楼阁,犹自教歌舞。野花开遍真娘墓,绝代红颜委朝露。算是人生赢得处,千秋诗料,一抔黄土,十里寒螀语。
人类之生命无论何等绚烂辉煌,但终究只是光阴之过客,终将归于消歇沉寂,只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若以此种眼光观之,则人类之一切执著,即便是对理想的执著也皆为徒劳无益之举。身为海宁人的静安先生,发现家乡那壮观的钱塘大潮的命运竟然只是终古不息地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努力:“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而民间传说伍子胥的冤魂每日乘着素车白马,随潮而至来看夫差的结局。这种震撼天地的悲愤在静安先生看来也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世事沧桑,你所执著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蝶恋花·辛苦钱塘江上水》)。
人生至此,已经一切皆是无常、虚幻,不值得留恋、执著,那么也就是完全没有意义可言的梦幻泡影了: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高城鼓动兰釭灺》),“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鹊桥仙·沉沉戍鼓》)。可以说整部《人间词》就是静安先生杜鹃啼血般唱出的一曲曲对人生和人世的哀歌挽词。
二
对世界人生持悲观虚无态度之人多矣,但不一定都如静安先生这般痛苦。因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已经认定世界为无意义,便不会对其有任何渴求和期望,反而可以弃之如弊屡,超脱出来,如佛家之视人世为幻影,进入涅槃寂灭之境。静安先生虽能以其清明睿智之理性洞察到人世间的种种罪恶以及人生的空虚,知其不可亦不足以有为。但在感情上,他又对世界人生抱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明知不可而不得不为,于是“常徘徊于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矛盾痛苦中”。[3](P10)盖静安先生感情之热烈执著,真挚笃厚似屈子,而其思想之深刻,透彻人世之无常又似庄周。这种感性和理性兼长并美而又相互冲突的性格,乃是静安先生陷入痛苦的自身根本原因,使其不能学庄生之高蹈遗世逍遥尘表,而只能如屈子之困顿彷徨,忧伤终老。静安先生尝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知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可见,其对自己感性与理性相冲突之矛盾性格亦有清醒之认识。上文提到的“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诸句皆以深邃之理性直透人生之无常荒谬。若能由此更进一步,临崖一跃,正可进入佛家涅槃之境。然静安先生肫挚之情感,其对人生人世不能自已之关怀使其不能完成这最后一跳,还是固守在此无望之人世,勉为其难为人生寻求意义。然此种意义既早已为其理性所否定,因而愈追求,愈怀疑,也愈失落,但还是要继续追寻下去。“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点绛唇·屏却相思》),这已经成为静安先生无法摆脱的宿命。
静安先生虽能在理性上透视人间之苦难,有一种超出常人之清醒,但在感情上也像芸芸众生一样都被人世洪流裹挟而不能自由。故而其虽能以一种超越的高度来俯瞰世间众生之无明,但不像他的精神导师叔本华那样对众生有一种轻蔑和优越感。而是知道自己之命运与众生无异,均为尘世间可怜存在,所以更多的带有一种病痛相关、悲天悯人的情怀。正如这首《浣溪沙》所展现的: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上阕展现出一个高远宁静的境界,但词人能够以一种超越的眼光俯瞰世间时才发现自己心在天上而身却在红尘。清醒的理性带来的不是解脱,而是更深的痛苦和绝望。
由彻悟之智可产生遗世之情,而由大悲之心往往能生出济世之志。静安先生兼具二者,既渴望遗世远遁保全真性不受世间污染,同时又希望能尽到自己对世界的一份责任,尽一己之力去唤醒昏迷众生。静安先生有两首词分别咏梅花和水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既欲独善又欲济世的矛盾:
人间圆·梅
天公应自嫌寥落,独自着幽花。月中霜里,数枝临水,水底横斜。
萧然四顾,疏林远渚,寂寞天涯。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
卜算子·水仙
罗袜悄无尘,金屋浑难贮。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却笑孤山万树梅,狼籍花如许。
梅花在严寒寥落之际开放,担负起唤回春天的使命,但要忍受孤独寂寞和先期零落的悲哀。水仙则完全是一副出世绝尘之姿,不受任何人间的污染,保持着自身品性的高洁。对于栖栖世务而损伤自己的梅花,投之不以为然的一笑。个体自由与社会关怀之间如何获得平衡,是中国士人永恒的矛盾,也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中国文学之真生命在于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对社会大群的关怀之中,在尘世中建立天国,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一体不二。明知入世之苦,而仍不舍世间;深知自得之乐,又难以高蹈独善。所以,静安先生必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方能心安理得。静安先生早期的一首题为《杂感》的诗便能说明这一点:
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
在静安先生的词作里,这种对人间既超脱而又难以舍弃,对人间之苦难充满悲悯,极欲救赎的感情随处都有显露。此乃静安词最为可贵之处。于此,最能见静安先生之人格。如下面这首被誉为其压卷之作的《蝶恋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如此窈窕幽美之人,居于百尺楼上,本可以抚明月、摘星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但她却难以忘怀楼外风尘之中的行人,最终只能与其共老尘寰。静安词之真精神是直通中国士人心灵最深处的。
三
静安先生性格中还有一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心目中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有一种宗教般的执着,并用毕生精力黾勉以求,至死不悔。至若静安先生之理想究竟为何,殊难将其具体指实。盖理想之为物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和对至高境界的追求,静安先生常常称其为“宇宙之真理”、“万世之真理”。静安先生是一个极其纯正的理想主义者,对真理的追求乃是出于不得已之天性,尝谓:“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价值不存于实际而存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耑耑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彼牺牲其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叔本华与尼采》)但是生活在传统文化崩溃、价值观破碎的时代,静安先生已经难以找寻到足以让他既信又爱的真理来安抚自己的心灵。所以,静安先生的追求从一开始便注定要落空,如《减字木兰花》:
皋兰被径,月底栏干闲独凭。修竹娟娟,风里依稀响佩环。
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依旧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
那理想中的宇宙之最高真理如同钧天之乐一样,只有在梦中才能仿佛得之,梦醒之后仍然要面对这苦闷的人间。尽管追求的结果只是惘然,但追寻本身便是这种真理存在的体现,已经成为生命的意义所在,如《鹧鸪天》: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空馀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
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
周策纵评曰:
此咏无尽追寻之作。较李清照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悱恻优美不如,庄严深远则过之。盖静安所云攀跻摸索,尤具有《浮士德》浮士德“上穷碧落下黄泉”永远追求之意境。妙在不言所追寻者为何,故主题乃在永远追寻之本身。[4](P151)
静安先生用以表达其追寻理想的题材主要有两个,一乃游仙、二为爱情。游仙取其境界之高远,爱情取其感情之缠绵。二者又多以梦境表出,尤具一种迷离恍惚之感,象征理想之渺茫难寻。游仙之作如《点绛唇》:
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
波上楼台,波底层层俯。何人住?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
再如《蝶恋花》:
忆挂孤帆东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见。几度天风吹棹转,望中楼阁阴晴变。金阙荒凉瑶草短,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
此等词作皆借寻仙受阻来表达理想杳不可寻的痛苦。爱情之作则更多,也更为优秀,如《蝶恋花》: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这首词借男女相合之困难象征理想之幽渺难寻、情辞兼善,那目成心许的激动,转瞬即逝的怅惘,恒久相思的痛苦,表达得极为真切,富于感发人心的力量。静安先生不仅表现出了理想追寻之艰难以及难以达成之痛苦,更为可贵的是还表现出一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以及独自承受痛苦而不改初衷的坚贞,如《临江仙》:
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不知今又过辽西,千屯沙上暗,万骑月中嘶。郎似梅花农似叶,朅来手抚空枝。可怜开谢不同时,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
就现实而言,静安先生追求理想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终其一生都未能将自己从生命虚无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但静安先生在追求理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民胞物与、坚贞不悔、热烈执著的人格力量才是静安词的真精神之所在。
注释:
①周策纵语,引自叶嘉莹,安易(编著).王国维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6年.此词乃是静安先生在妻子莫氏病危时所作,乃是感叹夫妻聚少离多,方聚变成永别之痛苦。
②静安词中记梦之作达23首之多,其梦境大多是一种美好而又容易破碎之境界的象征,如“可堪今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鹧鸪天·列炬归来酒未醒》),“风枝和影动,似妾西窗梦。梦醒即天涯,打窗闻落花”(《菩萨蛮·红楼遥隔帘纤雨》)之类皆是。
[1]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3]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4] 叶嘉莹,安易(编著).王国维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