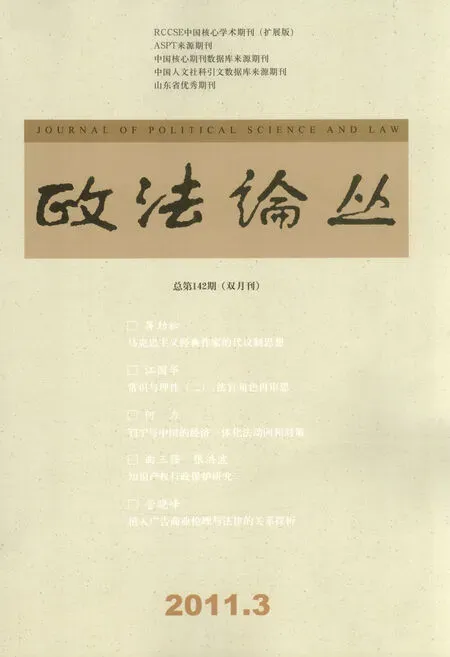我国反酷刑问题成因分析
唐艳秋
(山东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我国反酷刑问题成因分析
唐艳秋
(山东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禁止酷刑行为是当今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要求,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持续努力的一项共同任务。我国自签订反酷刑公约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反酷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公认的进步,在国际反酷刑的人权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司法环境的影响、实体法配置的欠缺等因素,致使我国反酷刑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探究我国反酷刑问题的成因对于有针对性地加强反酷刑工作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环境 诉讼制度 实体法配置
禁止酷刑行为是当今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要求,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持续努力的一项共同任务。1984 年12 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下文简称《反酷刑公约》),1988 年10 月4 日我国庄严地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这标志着我国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道在反酷刑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正式态度。我国自签订反酷刑公约以来,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努力,反酷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公认的进步,在国际反酷刑的人权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反酷刑工作虽在理论认识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框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现实的司法工作当中各种酷刑现象仍屡屡发生,为了达到杜绝酷刑的目标,我们有必要探究我国反酷刑问题的成因,以期有针对性地加强反酷刑工作的开展。
一、思想根源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司法中实行纠问式诉讼,“这种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的核心在于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客体化,人之为人的权利没有受到尊重,也就是说人权观念的淡漠,才导致了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合法化,被告人成为了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一种手段。”[1]P353在纠问式审判的不良影响下,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的理念不能确立,为了追求所谓的实体的正义而在程序上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地推定为有罪,“口供”系证据之王,刑讯逼供是合法行为,受法律保护。可以说,这是刑讯逼供等酷刑现象存在的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等酷刑现象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有的司法人员凭借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时,往往凭个人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一旦不遂愿,就动用刑讯逼供等手段来达到目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的法制相对己经比较健全,但人们的头脑中重人治、轻人权的思维仍旧无法彻底改变。”[2]P136
对人权的忽视,除有历史上的封建纠问式诉讼、文革时期“左”的思想的影响等原因之外,也有现实的因素——我国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承认和接受的时间不长,有关人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宣传、教育开展不久,这也是造成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淡薄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在当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仍然存在着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而忽视其人权保障机能的思想。立法者和司法者力图通过刑罚权的动用来惩罚犯罪,以刑罚这种不得己的“恶”否定犯罪之“恶”,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加之一部分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还存在着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罪从供定的陈腐观念,在犯罪嫌疑人否认罪行时,主观上便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在狡辩,力图采用一切手段逼使其供述罪行,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极易出现漠视人权、实施酷刑的现象。另外,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有深刻的思想渊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商君书·赏刑》)以及“治乱世用重典”等,重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要通过重刑的威吓作用使民众不敢以身试法,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刑事政策仍在较长时期内强调“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且没有科学地认识到并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辨证关系,轻视程序及司法的过程而注重结果,以为只要有效地惩罚了犯罪,就实现了保护人民的目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安状况的严峻和各种严重性犯罪的凸现,重刑主义在立法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3]究其原因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刑法的目的和刑罚的功能,刑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保护人民,也包括犯罪嫌疑人和己决犯的保护;刑罚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分子,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和挽救犯罪分子。在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直接后果便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受程序控制者进行“法外用刑”,实施刑讯逼供等形式的酷刑,认为受刑者也是“罪有应得”;间接后果就是对我国反酷刑立法产生影响。如刑法对酷刑罪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过于严格、刑法中规定的酷刑罪有漏洞和对酷刑犯罪规定的刑罚较轻等。[2]P343-346
二、司法环境、氛围的影响
我国反酷刑问题的成因之二是司法环境、氛围的影响。比如上级往往有破案指标、破案限期、命案必破等要求,而这些内容又往往比较集中地存在于各地司法机关的管理中,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考评晋级制度的不合理。各地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进行考评是管理中比较流行的做法,其考评的内容往往包括办案率、破案率、结案率、羁押率等量化指标,但类似此种内容有违司法理念和司法规律之嫌,反而容易促成酷刑现象的产生。
首先,过度提倡和要求案件数量的增长,将案件数量的多少和增长率(尤其破案率)的高低作为评价工作尤其是侦查工作优劣的标准,这种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司法人员积极性的发挥,但违背了司法工作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秩序状况相适应的规律。案件数量的多少、 破案率的高低、结案率等等,往往不是以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治化水平,司法技术水平、司法人员素质、国家工作人员数量等等因素。过分强调案件数量及破案率等,会引导司法人员单方面追求单位时间内的效率,并可能违反诉讼规律,盲目压缩办案的时间,这就常常导致案件质量得不到保障,最终以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违反诉讼程序为代价,极易导致酷刑行为的产生。如,侦查中被告人沉默不语会激发侦查人员的急躁心理,实施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就会变得理所应当。其次,虽然量化管理的可行性较大,但司法工作的相当内容是无法量化的,数量的追求也是导致酷刑的重要因素。如强调追赃数量、破案的数量、查处的数量等,会直接刺激司法人员采用不同形式酷刑的积极性。再次,对工作成绩的考评太注重结果,而忽视工作的过程,并往往把结果作为晋级的依据。这种评价标准,还是只注重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违反了诉讼的基本规律。诉讼的过程关注的是公正,而对数量、结果的过分追求,势必会鼓励司法人员淡化诉讼的过程,对于诉讼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缺乏重视,严重影响相关司法理念的培养和形成,造成恶性循环。
三、对执法人员反酷刑教育和培训不足、司法人员的素质欠缺
就我国的司法实践看,酷刑的主体往往是执法或司法人员,他们的素质高低与酷刑问题的存在有直接的联系。司法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司法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还应当具备优良的专业素质。换句话说,执法、司法人员的素质不仅应包含专业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应包括以人权保护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理念。没有相应的现代法治理念,再好的专业文化素质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而仅有法治理念,没有相应的专业文化素质,同样保证不了案件的质量。有效反酷刑需要司法人员具备相应的综合素质,但据有关人员针对司法人员对《反酷刑公约》的认识问题的调查表明:在6347份问卷中,半数以上被调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和普通公民没有看过《反酷刑公约》,因而其对《反酷刑公约》的性质、地位和约束力等具体问题的认识较模糊,主要表现之一是:只有54.24%的法官、36.96%的检察官、52.31%的律师、44.10%的警察、31.46%的普通公民知道该公约是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性公约,其余近半数或超过半数的被调查的职业群体要么错误地认为这是欧盟通过的地区性公约,要么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的公约,或者干脆不知道公约的存在。这表明,半数左右的公安司法人员和大多数普通公民并不大注意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也不大注意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4]P127有报道称,1997年云南省某市的两名警察接到有人被盗70元人民币的报案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名16岁的中学生活活打死,其理由仅仅是因为这名中学生曾经与3名被怀疑偷钱的人说过话。在法庭上,这两名分别从警13年和8年的被告人居然不能回答什么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应该具有哪些权力和责任以及在接到报案后应该遵守哪些办案程序等基本问题。[5]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酷刑行为将不足为奇。《反酷刑公约》第10条要求:“一、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在可能参与拘留、审讯或处理遭到任何形式的逮捕、扣押或监禁的人的民事或军事执法人员、医务人员、公职人员及其他人员的训练中,充分列入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教育和资料。” “二、每一缔约国应将禁止酷刑列入所发关于此类人员职务的规则或指示之中。”除此以外,联合国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司法、执法标准的文件,其中也再三强调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必要的教育、培训和宣传工作。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很重视对于国家司法人员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和培训。以丹麦为例,“凡从事警察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三年半的专业教育,第一年在警察学校学习专业课程,第二年到警察局去实习,边实习边学习,第三年又回到警察学校再接受专业教育,最后半年又回到警察局从事特种技能学习。只有经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被录用从事警察工作。”[6]P135-136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丹麦,警察具有很高的素质并受到公众的极大信任。在一次民意调查中,90%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对警察持信任态度。”[7]P149经过如此严格的培养和训练,丹麦警察的各方面素质都很高,“在丹麦,受到民众最高等级评价的,恰恰是警察及其行业。”[6]P136应该说,我国对于司法人员的教育、培训也是比较重视的:国家在1952年即建立了专门的政法学院培养专门的法律人才,而且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律专业教育;尤其是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对加强我国司法人员的相应素质有重大的意义。如前所述,我国的诸多立法,如1995年制定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其中系统地规定了法官、检察官及人民警察的任职条件和资格考试制度以及法官、检察官及人民警察的职权、应承担的责任、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他们的监督措施和违法的法律责任等。但是应当看到,相对于现代法治水平的要求来说,相对于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人员素质来说,我国的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陈卫东教授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司法官的比较研究之后,对我国司法官遴选制度做了理性反思,精辟地指出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初任司法官资格要求较低。表现在专业化知识要求低和法律职业要求低两个方面。第二,司法官选拔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表现在:司法官选拔体制的多元化,导致司法官的地方化;司法官选拔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司法官的缺乏同质化;司法官的选任按选任一般公务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进行,有违司法官选任制的科学规律。第三,缺乏司法官逐级晋升机制。[1]P151-153这些制度问题的存在,在实践中带来的问题就是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司法工作的应有需要,加之现实中受这样那样条件的限制,使司法人员仅在来源方面就存在问题。以法院为例,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基层法官队伍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或非法律的毕业生……这类人数都不到10%;二是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这类人数约30%;其他则是复转军人,大约超过50%。”[8]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应付培训。有些培训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要求,过程流于形式,走过场的成分较大,学员并不能真正地接收到系统的专业培训。二是因为真正接受过系统学习或者培训的司法人员多数集中在上层或者中层司法机关中,而广大的基层司法机关中,很多司法工作人员既没有专业的受法律教育背景也未曾接收系统培训,而这些基层司法机关恰恰是各类酷刑行为的多发地。三是在这些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上,专业设置过于简单,内容陈旧,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严重,很难适应法律发展的新潮流。而且培训内容的全面性关注不够,人权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培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司法工作人员并没有树立牢固的人权保障意识,这也是目前发生酷刑行为的原因。所以,加强对司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和反酷刑教育不但必要而且现实意义十分明显。
四、相关刑事诉讼制度不完善
我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酷刑行为多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其是刑事侦查活动中。而刑事诉讼相关制度设计上的失衡或缺位是导致司法实践中酷刑存在的现实原因。择其要者如下:
1.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也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贝卡利亚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9]P27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这一规定虽然法学界认识还不很统一,但可以说它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0条、第162条的规定,针对证据不足的情况,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分别可做出撤消案件、不起诉的决定和“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都体现着无罪推定的精神。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反映了我国法治的进步, 但这些规定离无罪推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无罪推定的全面贯彻在立法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对司法人员现代法治理念的形成、相关诉讼制度的设计具有根基性的作用。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我国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并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还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一如实陈述的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进行交待的权力。因为判断是否“如实”、是否“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自由衡量,一旦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回答不符合其预先判断,自然易于暴力相加,产生酷刑行为。
3.其他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酷刑存在的重要原因。与酷刑问题较为密切的制度,如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等等。侦押分立制度,是指侦查和关押犯罪嫌疑人由不同机构或人员负责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侦查和关押机构之间互相监督,防止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的发生;人身检查制度是由法定的机构或人员定期依职权或应被羁押者的请求对其进行人身检查,以防止侦控机关的暴力行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通知其律师到场,没有律师到场时侦查人员不得进行讯问的一种制度;警察出庭制度则是指警察也必须像其他普通证人一样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于通过当庭质证揭露并证实警察的非法取证,包括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以上制度是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些制度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有效反对酷刑和推进刑事诉讼的文明化及民主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制度在我国却处于缺失状态,这无疑也成为助长酷刑现象的制度上的重要原因。另外,讯问程序规定不足:一是对于两次传唤或者拘传的最小时间间隔没有进行规定、对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时间没有进行规定等,导致实践中出现较短时间内的数次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的变相连续传唤、拘传现象及对在押嫌疑人的讯问持续12小时以上情况的存在,产生隐形酷刑现象;二是对讯问的地点规定太随意,使得侦查人员的讯问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导致酷刑现象的发生。
4.权力制约机制欠缺尤其是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制约与监督不够。孟德斯鸠曾言:“当一个公民获得过高的权力时,则滥用权力的可能也就更大。”[10]P14权力制约是现代法治的精神之一。我国在传统上是个人集权制的国家,缺乏权力制约的优良传统。从现行法律层面看,根据现行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各自独立的机构并且各自有着不同的权力和责任,在工作中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在实际中,在“重刑主义”及“重实体、轻程序”思想指引下,这三个机构关系往往过分注重相互配合,而忽视了相互制约,这种缺乏制约和监督的状况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酷刑的孽生。“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对待我国比较普遍、严重存在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为和现象,部分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对司法权缺乏严格的监督而导致司法权的行使失控乃至被滥用。”[6]P130事实上,“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不仅在法理上存在缺陷,违反公、检、法尤其是公、检之间由诉讼规律所确定的“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且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同时检察官又在这一统一体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双方存在不同分工但彼此不是独立地各负其责的关系;反映在刑事司法体制中,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上命下从’的关系。”[1]P235而且,使侦查程序呈现出严重失控状态,“这不仅分散与削弱了司法力量,同时,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如果这股恶风再进一步滋生蔓延,我们整个刑事司法体制就有可能丧失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法律制度本身就对侦查程序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形式,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有其名而难存其实,难以保障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有效性及合法性”。[1]P236-237而从控辩关系看,我国没有真正建立“辩护权”与“追诉权”的对抗机制,“辩护权”的制约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使“追诉权”失去了最直接的制衡。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还显得过于简略。在实践中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常常无法见到自己的律师。虽然目前《律师法》得到了修改,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但对遏制酷刑最有效的权利即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仍没有赋予律师,这些都给酷刑的产生以可乘之机。
5.缺乏相应的证据规则、证明责任不科学。众所周知,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令严禁,但实践中仍得不到应有的贯彻执行,尤其是在基层司法机关的刑事侦查过程中,类似的酷刑行为不在少数。而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宣告无效,因此,要想制止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宣告司法人员通过刑讯获取的口供不具有可采性。可我国刑事诉讼法缺少一套可操作的宣告无效的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否排除,法律未做规定。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较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这一证据排除规则也仅仅是将言词证据排除在外,要真正达到遏制酷刑的目的还是远远不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有待于深化。因为酷刑行为的范围不仅仅限定在刑讯逼供,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问题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当立法上明文规定刑讯逼供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控诉的根据和证明的手段时,如何对刑讯逼供等诉讼中的酷刑行为进行举证,就又成为反酷刑的重要问题。当然,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显然有失公正,而事实上不论何种形式的酷刑,只要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死亡后果,是否有酷刑行为就难以证明。正因为难以证明,也就导致司法人员在难以取得其他证据突破案件的情况下就会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形成了所谓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定模式之外的刑事诉讼实践模式:一方面是各部门大力宣传文明执法,一方面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长盛不衰。[11]P132所以,在法律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科学确定酷刑行为的举证责任十分必要。
6.刑事审前程序设计有违诉讼本质规律。我国的审前程序中,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决定、批准、及执行均由侦控机关负责,缺少中立的机构介入,特别是对刑事拘留、逮捕的规定和适用,缺少司法审查和救济。“而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于解决争议必须有代表理性和正义的中立的第三者存在,由第三者在纠纷当事人之间做出判断。”[1]P105在审前程序中,也必须具备诉讼的基本特征,必须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裁决。否则,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与代表公民权利的辩方之间的纠纷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违背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权和拘留条件,由于缺乏制约,公安机关往往无视适用条件的法律规定,对其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人无一例外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滥用刑事拘留权。讯问的程序设计粗略,讯问的条件、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缺少法律的明文规定,讯问的环境封闭,导致讯问的随意性。又如,《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第142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权力,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对“批捕权”、“不起诉权”进行滥用的现象,对逮捕和起诉审查不严,当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法庭审理无法定罪时,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做出“罪轻不起诉决定”,对其“错捕”行为加以掩盖,等等。审前程序的设计缺陷,使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得不到理性的授权审查;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使非法取证等行为得不到及时的预防和制止,从而间接鼓励了各种形式的酷刑行为,导致刑事审前阶段酷刑频发。
五、酷刑的实体法配置不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于1988年正式加入《反酷刑公约》,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反酷刑的法律承诺,并在国内司法中予以执行。我国有关酷刑的实体法配置主要体现在《刑法》中,当然,在《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安全法》、《监狱法》中也对禁止酷刑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同时还以《国家赔偿法》对遭受酷刑对待的受害者做出了国家赔偿的法律规定。可以说,我国已经有了反酷刑的实体法配置,建立了反酷刑的法律框架。但仍存在着酷刑的禁止范围不够全面等突出问题,表现在:
1.反酷刑立法还比较粗略。由于立法受过去宜粗不宜细精神的影响,反酷刑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够具体,造成实施的困难。如究竟什么是酷刑,哪些行为构成了酷刑犯罪等都还停留在学术的研究上,现行刑法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追究酷刑行为虽有法律依据,却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及时、有效追究酷刑实施者的法律责任。就酷刑的典型形式刑讯逼供来说,我国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刑讯逼供的概念、范围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47条的刑讯逼供罪只笼统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同时司法解释也未对刑讯逼供的概念和范围做过明确的规定。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标准的规定》解释:“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而何谓“肉刑”、“变相肉刑”仍无明确界定,只是笼统地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一、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二、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三、造成冤假错案的;四、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五、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虽然,2006 年7 月2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当中,对刑讯逼供案的8种立案情形做了详细的规定,新的立案标准比以前显然更加详细了,“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等情形也被增加进来。但从上述的规定我们似乎可以推出如下结论:除上述法定情形之外,其余的行为均不构成刑讯逼供罪。而实践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却远不止这些情形。这样的法律规定配之警察等司法人员现行的综合素质而言,有利于警察在讯问过程中,采取规避法律的手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但不利于对酷刑行为的认定,不利于司法裁判的统一,影响反酷刑的效果。
2.反酷刑立法不够全面。如前所述,我国酷刑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而酷刑实施的主体也不仅仅限定于刑事司法人员这个范围,一些酷刑行为还未被明确纳入现行实体法中禁止性规定之列。当前酷刑的主体大多仅限于警察、法官、检察官等执法、司法人员,而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施用酷刑的犯罪,则未纳入法律制裁的范围。又如作为酷刑重要形式之一的精神酷刑,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实体法中对此却没有规定,等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曾说:在实体法上,我国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在程序法上,《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但在刑讯逼供构成要件上,涵盖面较窄,1979 年刑法对于刑讯逼供罪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1996 年刑法则仅限于司法工作人员;对象也偏窄,未包括治安管理处罚对象等同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群。处罚也较轻,法定最高刑才三年有期徒刑(当然致人伤残、死亡的除外)。[12]由于立法者对酷刑犯罪的法制破坏作用认识不够,对酷刑犯罪规定了较轻的刑罚,导致酷刑犯罪在罪、责、刑上的错位,对遏制酷刑产生了负面影响;司法上,除因受害者举证困难等原因导致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难于被认定外,即使对己经认定的酷刑犯罪,在法定刑偏轻的情况下,仍然从轻处刑,导致刑罚的正常功能在酷刑犯罪领域难于实现。可以说,这种实体法配置状况无疑间接怂恿了酷刑行为的发生。
3.办案机关经费不足。据统计,一般发展我国家维护治安经费的占财政收入的9%。而在我国仅占2.9%。[5]经费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执法机关的能力,直接导致司法机关的侦查设备陈旧,侦查方式落后,技术水平低下。这种状况与现代犯罪手段呈现出越来越先进的趋势,高科技犯罪层出不穷的犯罪特点的要求却不相符合,使案件的侦破变得愈加困难,产生了技术设备的落后与先进的犯罪手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必然导致各种滥用职权和违反人权等酷刑现象的发生。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状况令人堪忧。这也是酷刑问题存在的较为明显的现实原因。
以上对我国目前酷刑存在的原因做了简略的分析,当然这些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侦查、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时常要面临着各种利益的权衡,是保护人权还是打击犯罪,是坚持公正还是注重效率,具体到破案则是保护人权(包括保护罪犯的人权)而延迟甚至搁置破案,还是为了尽快破案而使用酷刑。现实中的酷刑实施者也正是基于种种的利益衡量,如为了破案、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侦查设施差迫于无奈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而做出了实施酷刑的利益选择。酷刑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而且是多元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不仅应具备现代法治理念,也应动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杜绝酷刑行为的发生。
[1] 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 赵秉志主编.酷刑遏制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3] 张智辉.重刑刑事政策对反酷刑立法的影响[J].刑事法学,2004,6.
[4] 中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及人权保护项目课题组编.刑事诉讼中若干权利问题立法建议与论证[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5] 毕小青.我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与反酷刑制度[EB/OL].中国法学网,访问时间:2010-04-26.
[6] 陈云生.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毕小青.丹麦被关押人的权利保护和酷刑预防[A].夏勇,默顿·凯依若姆等主编.如何根除酷刑——我国与丹麦酷刑问题合作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 云剑,张志英.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与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2.
[9]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高一飞.人权公约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完善[A].证据学论坛(第二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12] 宴向华,柴春元.如何应对‘酷刑’这道世界性难题[N].检察日报,2006-08-16(003).
AnalysisontheCauseofChineseAnti-torture
Tangyan-qiu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
prohibit acts of torture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s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is also continuing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 common task. Since China signe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fter 20 years of efforts, the anti-tortur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ti-tortur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the lack of substantive law targeting such factors, China's anti-torture work of the problems is quite severe, anti-torture is still very arduous task. China's anti-torture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is very necessary, in a targeted manner to strengthen the anti-tor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nvironmental justice;Litigation;Configuration of substantive law
DF718.2
A
(责任编辑:孙培福)
1002—6274(2011)03—092—07
唐艳秋(1966-),女,山东烟台人,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学报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文献计量学。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