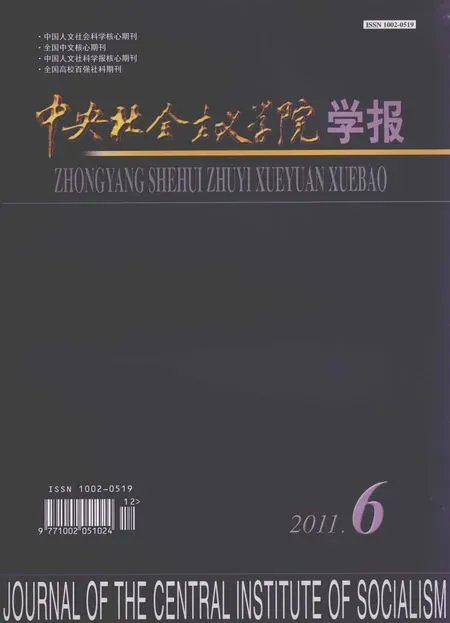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路径选择及其启示
张友国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民族问题研究·
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路径选择及其启示
张友国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诸项公共政策议程中,语言问题一直是民族统一构设进程中需要处理的重大课题。语言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族际和谐与民族统一构设进程。在这种背景下,当代多民族国家分别遵循一元化、双元化和多元化三种路径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无论是单语政策、双语政策还是多语政策,都需要权衡语言政策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共同语言的获得将需要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自然融合过程,需要在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审慎地对待。
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官方语言
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建国后都需要进行民族统一构设。从传统上讲,如果民族概念与现代国家概念,或与任何已建立的国家之居民概念等同划一的话,那么民族统一构设这一概念仅是指现实的国家控制和公众服从的政策;如果民族概念是文化共处或种族特征的一种表述的话,那么,民族统一构设即意指向一个语言、宗教或者种族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民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1]527。语言政策作为民族统一构设的重要一环,在那些具有不同传统、宗教和种族集团的国家当中,尤为紧要。因为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一种语言化活动,语言又关涉到整个民族的利益。语言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因此,关注语言问题,制定妥善的语言政策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目前,关于语言政策的研究,或者以国别为基础进行阐述,或者侧重于语言的发展与政治,而对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路径取向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探讨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制定之背景、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之路径选择等问题,同时阐述笔者对当代中国国家统一构设中语言政策之若干思考。
一、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背景
多民族国家建国以后必须面对“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是指在国家政治、公务、教学、广播、出版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语言问题处理不当,会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统一构设产生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如下:
第一,不利于族际和谐。这一影响取决于语言的民族性和交际性。语言首先具有民族性。语言的民族性与语言的承载主体密切相关。语言作为民族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往往就是语言的分界线。何谓“民族”?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民族”定义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2]。这一定义将语言作为民族特征的重要权衡因素。此外,许多著名的民族研究专家,如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和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等,都将语言提升到民族身份的主要支柱的高度[3]46。为何语言的民族性受到如此重视?语言值得重视,是因为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历和价值观,是因为它与人类的思维,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人类不仅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也生活在由语言所构成的观念世界里[4]299-301。文化观念的传承与传播都靠语言文字。正如格尔茨(Califford Geertz)所指出的,文化是指导人们行为的符号体系,认识一种文化就是对其意义进行层层递进的挖掘、描述和解释。这样挖掘下去,最终会涉及该种文化负载者(民族或族群)的观念世界,而语言则是认识文化核心即观念世界的重要途径。
上述语言的民族性仅仅展示了语言以民族为范畴的社会边界。事实上,在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世界,民族与民族之间很难固守各自的语言边界而不发生语言的互动。这是因为语言本身还具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交际性。这从一些学者、政治家的论断中可窥见一斑。赫尔德(Herder)声称语言是最基本的社会联系、人们之间联系和交流的唯一的手段。语言表达了群体的集体经验[3]45。斯大林则认为:“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5]20“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5]20-21因为语言是存在于交谈双方头脑中的那套包括语音、词法、句法和语义在内的,组织、传递和复原意义的规则,或曰结构。它与指导人类行为的文化规则颇为相似,是隐藏在言语背后的一套抽象系统,是个人在学习语言时所消化了的东西。语言约定俗成并属于全社会,使同一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能交流思想[4]296。但不属于同一语言共同体的民族之间却往往因为这套复杂的抽象系统而产生沟通失谐。因此,可以说,在多民族国家,如果不注意民族统一构设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当语言的民族性叠加语言的交际性时,不同的民族将会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族际关系失谐,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
第二,不利于统一构设。语言既可以有助于、也可以有碍于国家的统一构设。1918年以后,语言的一致性为一些欧洲政体(如波兰、匈牙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诸国)的组成或重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基础,尽管其中一些国家仍保留了主要的、语言方面的少数民族。1945年以后,在殖民统治的解体和新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过程中,语言常常是一种分裂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一种或几种官方语言的选择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1]424。为何在国家统一构设的进程中,语言扮演着如此至关重要的角色?“语言是存在的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不是人的工具,语言的本质即是存在的本质。美国学者格尔茨(Calliford Geertz)指出:“语言问题”实际上是“民族问题”的缩影,语言是一个民族宗教、艺术、文学和哲学传统的载体。在现代世界,如果说主流语言代表一种所谓的“时代精神”,那么,民族语言则代表一种“本土生活方式”。而代表本土生活方式的母语,相对于只有“外语”才能进行的思维活动,往往更能赋予个人以某种思想的力量,“不管他如何粗糙或者微妙”。此外,母语因为在心理上更为接近自身,它也就成了民族国家最为广泛的文化群体的表达工具。任何语言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正是通过语言,人们才参与到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社会中来[6]。因此,特定的语言决定着特定社会中人们不同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甚至对世界意义之理解的独特性。社会内部由于语言因素导致的分裂界定了语言群体的核心信仰和身份认同,阻止他们与来自其他群体的人们进行合作,即使这些群体在其他问题上与他们有同样的关心。正因为如此,一些民族在进入现代化阶段之际,不断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这些民族的成员对自己的民族语言产生强烈的归属认知和感情。民族语言成为保持民族一体感和认同感的标志。民族思想和感情往往聚焦于语言,人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是民族特性和民族价值的体现。在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革的条件下,语言权限与民族关系相伴而成为社会的现实问题[7]186。“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8]这种文化保守的心理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构设有着不利的影响。
另外,语言的政治意义也往往影响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构设。语言的政治意义与现代化背景下语言之间争夺符号权力及其背后所附着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的分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统一构设进程中,语言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符号权力,影响这一进程。
二、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路径选择
针对上述语言问题,多民族国家基于各自的哲学理解,遵循不同的路径分别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语言政策“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调整与社会语言关系相关的活动范畴。语言政策也指发展社会语言关系的战略方针,该方针通常在宪法和国家专门法规中得到强化。与其他政策一样,语言政策的中心是权利问题或权利的获得、构筑和应用。”语言政策的许多目的非常抽象,它们是民族政策的一部分[7]150-151。随着民族意识的普遍提高,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越来越大,逐渐演化为一个敏感的领域。除本身的工具价值外,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在有些国家,语言的意义被提升到一个民族的高度,可能引起冲突,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因此,慎重选择语言政策,是保持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状况分为以下三类:其一,一种语言占支配地位、并有一种或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国家;其二,两种或几种语言同时并存的国家;其三,语言种类异常多样化的国家。在使用多种语言的政治体系中,语言的使用及其权利则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课题。这些抉择可能通过立法或规则来做出,因而是高度制度化的,或者大部分留给习俗或司法决定;它们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权力下放或根据特殊的情况而集中化或分散化。次要的和主要的群体常常在规则的适当形式和调整的程度上存在意见分歧。规则的基础可因语言的地域分布不同而不同:属地原则(territorial principle)规定在一特定地域或地区所使用的语言,而属人原则(personality principle)却将语言权利和义务赋予一个规定的政治单位内的法人或自然人。实际上,当代许多语言政体都结合了上述两种原则[1]425。多语言国家为了创造一个“交流共同体”,将在如下三个方面作出选择:第一,清除所有的语言,而不是使用最有影响的群体的语言,这将导致所有的语言少数群体融合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第二,不允许少数群体的语言在正式场合,如教育和政府机构等地使用,这将导致少数群体的语言被边缘化;第三,在法律上承认所有语言并发展所有的语言,尤其当这些语言有地域背景时,这将导致语言多元主义,承认无数语言的并存[9]199。
因此,综合多民族国家的上述语言状况,以国语①国语(nation language)是一个统一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范围内起到一体化和团结作用的语言,它是该国家的象征之一。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是国家管理、法规和公文的使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为衡量基准,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大致有三种路径:
第一,一元化路径。在这一路径下,语言政策规定国家只能使用一种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比如美国曾经盛行的独尊英语(English-Only)运动和原苏联强化俄语政策。受到西方单一语言模式的影响,一些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文章认定语言的多元化是一个障碍,要想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必须消除语言的多元化。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由于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纷纷宣布一种民族语言为国语,企图以此树立所谓国民的团结精神。还有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一些有名分群体想让他们的语言保持唯一的官方地位,作为新近巩固的国家完整性的标志,并以此证明比起本国其他成员们来他们的合法性更高[10]。因此,一元化语言政策通常在确定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前提下,着重关心如何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的语言。当然,公平必须与支配性民族集团的态度和少数民族的愿望相联系。作为这种关注的结果,这些国家一般允许独立或成立地域性的自治政府。此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分离但平等”或“不分离但自决”,即彻底将某一民族及其语言分离出原在母国,或建立自治区域并将自治民族的语言设定为“第一语言”。
第二,双元化路径。这一语言政策首要关心的是维持各语言集团之间的均衡和政治稳定,因此,采取双重官方语言的办法解决语言问题。譬如,哈萨克斯坦政府于1996年11月颁布《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基本构想》,其中强调:“语言政策应该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和睦与协作”[7]165,规定哈语和俄语都为官方语言。这是一种比较策略性的做法,有利于多民族国家不同语言集团之间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多元化路径。这一语言政策鼓励多民族国家采取多重国语或官方语言制。多元化的语言政策最为典型的是瑞士的语言政策。瑞士的语言政策建立在语言平等的基础上。在瑞士,19%的人讲法语,10%的人讲意大利语,近1%的人讲一种古语,即东部拉丁方言。尽管有这些多样性,瑞士人却成功将这些不同民族群组成一个国家实体。根据瑞士宪法学者对语言条款的阐释,不管是旧宪法的第一百一十六条还是新宪法的第七十条款,都衍生出两大原则:语言的平等原则和语言的个体性原则。四个官方语言居于平等地位。“语言的平等原则”表示,瑞士联邦的宪法法定及规范条文具有同等的价值内涵;“语言的个体原则”则指,任何瑞士公民可以依据任何官方语言与联邦行政单位接洽。同样的,联邦当局各单位的人员也可援用任何一官方语言表达[11]。这种语言上的平等代表对现代瑞士最稳定最和谐的一个影响因素[12]。
以上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三种路径选择仅仅是基于普遍性的标准进行分类。在语言政策的实施中,路径的选择可能会伴随地域或者时间的转换有着某种特殊性或者综合性,这要视多民族国家自身的需要而定。
三、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路径选择的启示
厄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曾经断言:“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倾向于说同一种语言,而且随着民族精神向深度拓展,共同的语言对民族国家的精神统一越来越有必要。”[9]193共同语言下各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将会剥离各民族狭隘的民族认同,增强对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习性的了解,形成共同的心理空间,增加民族融合的因素,从而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总的来说,拥有共同语言对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而言,当然是最佳的结果。但从前述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路径选择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都属于多语言国家,因此,在民族的范畴内讨论语言政策,往往涉及语言的统一或分裂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的关系。因为语言因素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与族性和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这也是人性的一个方面。”[13]在某种意义上,语言问题最容易调动起民族内各个层次人员的情绪。因此,语言问题很容易引发民族问题,继而导致政治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无论是单语政策、双语政策还是多语政策,都需要权衡语言政策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语言充满矛盾,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既稳定又流动。它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社会现实的创造者。在社会动荡的时代,人们热烈地讨论它。实际的语言实践彼此渗透,难以分开,显示了无限的变易性和突变性[14]。同时,语言与人类意识的活动和发展是一个整体。因此,它是行动的一种形式,并不仅仅是记录和标识外部物体,相反它扮演的是本质的角色。语言共同体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连续统一体[15]。语言使用方面的统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愿接受“族际共同语”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双语或多语是解决目前传统与现代化矛盾的钥匙,它能使民族杂居地区的人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人。第二语言可以使人开阔眼界,可以使人接受更多的人类文明成果,可以启发人们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可以形成一个平等使用各种语言的文化氛围[16]。它们作为解决语言问题的相关政策,只有坚持平等、自愿、互学的原则,才能确保语言政策有效得到实施。经济是决定语言传播能力的首要因素。在语言竞争上,一个民族经济的发达与否是决定该民族语言传播能力的首要因素。目前,从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势看,语言种类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7]185-186。因为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载体和交际的工具。在知识更新频率加快、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有科技资料和知识信息翻译成各种少数民族文字。语言趋同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坚守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斥其他的语言,否则,自身传统也同样会失去发展和创新的活力。正如格尔茨(Calliford Geertz)所言:“是否、何时以及为什么使用一种语言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在何种程度上根据自己的精神取向来建构自我的问题,和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时代要求来建构自我的问题。”[17]如果说前者代表自我,后者代表他者,显然,一个民族也只有在这两个向度上维持一种平衡,它才有可能在不迷失自我、维护民族自我认同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并与世界平等地共融为一体。
从现实情况看,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应用性和象征性经常处于矛盾中,即语言的理解需要和认同需要是对立的。一些国家或地区施行的双语或多语政策,即是将语言的实用性与象征性融于一体的满意选择[7]178。
[1]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11.
[3]Anthony D·Smith.The Ethnic Revival in themodern worl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0.
[6]特蕾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M].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74-276,80-81.
[7]张宏莉.当代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8]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361-362.
[9]T·K·Oommen.Citizenship,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Reconciling Competing Identities[M].Polity Press,1997.
[10]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M].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526.
[11]施正锋.各国语言政策:多元文化与族群平等[M].北京:前卫出版社,2002:400.
[12]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5-37.
[13]James·G·.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M].St.Martin's Press,1998:279.
[14]Laada Bilaniuk.Contested Tongues:language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rrection in Ukraine[M].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23.
[15]Andrew Vincent.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it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83-184.
[16]廖冬梅.新疆民族双语发展历史现状与成就[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202.
[17]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27.
责任编辑:杨 东
Choice of Language Policy in M ulti-Ethnic Count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ZHANG You-gu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89
At present,amongmany public policies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language has been a major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Inappropriate handling of language issuemay affect interethnic harmony and the progress of nation building.Under such circumstances,themulti-ethnic countrieswould respectively choose to implement unilingual,bilingual ormultilingual policy.Nomatter what kind of language policy to implement in amulti-ethnic country,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stability must be balanced.It will be a slow and gradual process of natural integration to acquire common language and requires cautious action in formulating the language policy.
multi-ethnic country;language policy;official language
D633
A
1002-0519(2011)06-0048-05
2011-10-07
张友国(1971-),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