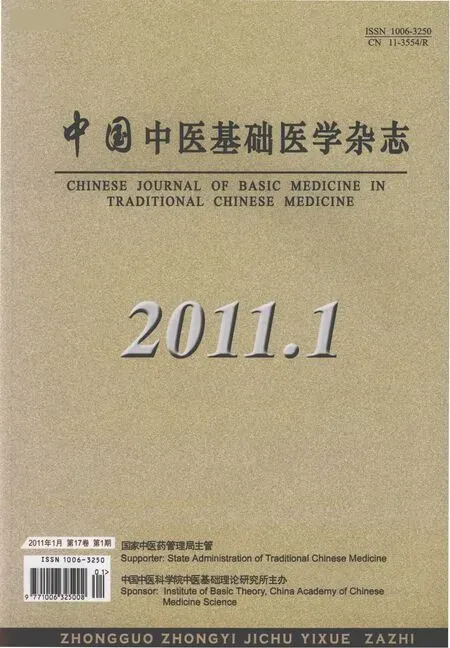数术——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架构
卓廉士
(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重庆 401331)
《素问·上古天真论》论及养生之道时说:“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将数术与阴阳并举,可见其在古人眼中的重要地位。今天,现代中医将阴阳誉之为“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对数术却不置一词,其原因可能与学术界曾经倡导的“继承精华,剔除糟粕”有关。然而,无论其为精华或糟粕,数术却是中医典籍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理论体系,它贯穿于《黄帝内经》的始终,无法绕过,只能面对,所以甚有系统研究使之呈现的必要。
1 什么叫数术
数术,又称术数,意谓数中有术,数字背后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在古代人类的思维中,数字并非仅仅是对现实的抽象那样简单,其中隐藏了事物的规律和宇宙本体的秘密。数字的大小奇偶、对之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揭示事物、现象的生成、变化及其内在原因和规律性。
《易·系辞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数术是一套涵盖宇宙时空的整体学问,象由数定,数不离象,它与道相通,是道的体现,阴阳感应、五行生克制化等理论皆出乎其中,故而数术乃学术之本源,学问之基础。古希腊亦有类似的思想,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 572 BC ~497 BC)学派曾将“数”当作宇宙的本体或始基,认为“万物都是数,万物是数的摹本,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的一切现象”[2]。
数术之学在秦汉盛极一时。据《汉书·艺文志》载:“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可谓卷帙浩繁,对照区区“《黄帝内经》十八卷”(同上),则可以想见当时数术是怎样一种显学了!数术的原则为秦汉各家所共用,它渗透到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自然,医学也无例外。《素问·三部九候论》曰:“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古人用数术原理架构中医理论,用以说明人体脏腑、经脉、气血的性状与天道的符合度,以及人体各种生理指标的内在联系,其体系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从一到九的数字
法国著名人类学者列维·布留尔(Levy-Bruhl,Lucien,1857~1939)认为,在古人那里,“每个数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个别的面目、某种神秘的氛围、某种‘力场’……这样被神秘气氛包围的数,差不多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3]。在古代的不同民族之间常常会有相似的思想。中医也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素问·三部九候论》)。”从一到九这几数字为“至数”,差不多每一个数字都具有特殊的意义。现简介如下。
2.1 一
《说文解字·卷一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人视“一”是宇宙本源,是“道”的体现,被认作“大一”、“太一”(或作“泰乙”),受到古人的祭祀和崇拜。“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史记·孝武本纪》)。道家学说很强调“得一”。如《老子·第三十九章》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得一”则能与道相合,中医也是如此。凡诊数治疗符合于道,称为“得一”。如论及诊断时说,“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素问·玉机真脏论》)。切脉注重“得一之情,以知死生”(《素问·脉要精微论》),针刺强调“治之极于一”(《素问·移精变气论》),认为医生和患者的神气合一,最合于道,因而最能发挥疗效[4]。
2.2 二、三、六、九
《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之数为一,一分为二,判为阴阳,所以“二”代表了阴阳双方。现代中医理论关于阴阳的阐述极多,此不多赘。“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阴阳二气的运动一如雌雄相合,能够产生出新的生命,即所谓“三生万物”。三而三之,生生不已,万化繁荣,所以古人认为“物以三生”(同上),将“三”作为物质在时空之间运行的基数。如在时间上有“天地迭移,三年化疫”(《素问·刺法论》);空间上有“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灵枢·五十营》),由三寸累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经脉之气一天运行的长度。古人的诊疗活动亦是如此。如诊断上“诊有三常”(《素问·疏五过论》),刺法上“三刺而谷气至,谷气至而止”(《灵枢·终始》),将“三”作为针刺得气的基础数。“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而三之倍数六、九均被视为三的延伸和发展,如六气、六经以及九脏、九气、九窍等,且六乃阴数,九乃阳数,六与九的倍数,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都被赋予了解释天人关系的特殊意义。
2.3 四
《淮南子·天文训》:“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故举事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数字四是“阴阳相错”产生的。天地有四海,“海有东西南北……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海,以应四海也。”一年有四时、人有四肢以应之。
2.4 五
《易经·系辞上》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五为天地之数,在中医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如五行、五季、五脏、五官、五色、五音、五体、五志、五乱,其倍数则有“二十五阳”(《素问·阴阳别论》)、“二十五变”(《素问·玉机真藏论》)、“二十五穴”(《素问·气穴》)、“二十五腧”(《灵枢·本输》)、“阴阳二十五人”(《素问·阴阳二十五人》)、“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灵枢·营气生会》)、“三百六十五节”(《素问·六节藏象论》)、“三百六十五络”(《素问·针解篇》)等。
2.5 七、八
女子数七,男子数八,这是古人观察男女生、长、壮、老、已这一自然生理过程所获得的发现(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如男女之道有“七损八益”。这一自然过程又代表了某种周期规律,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有“七日以上自愈”,《灵枢·热病》则有“热病七日八日”一类说法,常指一个阶段的时日。
3 中医理论的数术架构
数术之学可溯源于河图、洛书。朱熹《易学启蒙》引孔安国语:“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河图、洛书是由数字组成的奇妙图案,据认为是远古人类对于天地人以及宇宙万物的终极认识,亦为《易经》的源起。《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的生成数为十,而洛书“有数至九”,而《内经》用到的数术“始于一,终于九”,或者与洛书的渊源较近。
天地人之间,即宇宙与生命之间,天然具有某种对称性,这种对称性是天人相应的基础,亦为中医理论的本源。人体的阴阳消长、气血环流与天体运行相对应,生命与宇宙相互印证,因而古人将“弥纶天地之道”(《易·系辞上》)的数术与人体结合,使“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用以解释、说明天人关系和生命现象。
数术有其数学层面的计算——较准确地说叫做“推演”。《内经》常用到的有五与六的倍数或公倍数、三和五的倍数或三五相乘、六与六相乘、九与九相乘,将这类结果固定下来作为某种常数,并将其视为天人联系的纽带。
“五”与“六”春秋以来就是一对神秘数字。《易·系辞上》有“天五地六”的说法。据此,唐·杨上善《太素》说:“天地变化之理谓之天道,人从天生,故人合于道。天道大数有二,谓五与六。故人亦应之。”这是五脏六腑的数理基础,也是原始十一脉的数理基础。而五与六的两倍分别为十和十二,其公倍数为六十,是六十甲子和五运六气的数理基础。
十二经脉的数理来源于“三”的倍数。三的两倍为六,故天的六气,人有六经,六经分为手足共十二条。有人认为十二经脉之数来自“三”和“四”相乘。三为生生之基数,四为四方之数。清代学者周学海云:“以天地四方之象,起三阴三阳之名,因即以其名加之六气,因即以其名加之人身。[5]”人有四肢,肢体内侧与外侧分别有三条经脉,为数十二。
“三”是万物产生的基数,“五”是天地之数,受古人的尊崇,称之为“三五之道”。《史记·天官书》就有“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的说法,认为“三五”内涵宇宙时空的至数,极具神秘性。《汉书·律历志》曰:“数者……始于一而三之……而五数备焉。……始三五相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其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三五之道”就是天人“上”“下”交通之道,天人之间的联系常以三五的数术形式。大约为了与天地交通,古人在其所厘定的经脉长度中隐含了“三五之道”。据笔者研究,《灵枢·脉度》所记载的各条经脉的长度(除足阳经取古制八尺之外)均为三五的倍数,手足阴阳经脉之差也是三五及其倍数[6]。显然旨在说明“人数”符合“天数”,人道合于天道。
“天以六六之节,人以九九制会”(《素问·六节藏象论》),天数六六三十六,人数九九八十一,是一套天人交通的数术。如为了与“宿三十六分”的天数相应,人体经脉则须符合九九之数;经脉左右各一,共长十六丈二尺(81×2=162),人体一侧经脉为八丈一尺,为九九之数。又如营气的流注数始于三,然后根据“物以三生”的原理,以三的倍数递增,“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灵枢·五十营》)。”气行一周二百七十息,十周二千七百息,合于三九之数。气行五十周(16.2×50=810),共为“八百一十丈”,正合于九九之数[6]。数术在天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同构关系。
4 藏象乃数术与理、象之结合
台湾著名学者唐君毅说:“中国先哲以数由理象而成,不离理象而独立,故数之结合即象之结合,与理之感通互摄。[7]”如果将这一观点具体到中医理论则应该是:“象”,藏象中的各种征象;“理”,脏腑生理病理以及治病之理,在“理”与“象”的背后有一套作为支撑的数术体系。
如阴阳之数为二,应象于天地、日月、水火,隐迹于静躁、寒热、生长,理同于纲纪、父母、男女;阴阳合而为一则近于道,故谓为“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而治病求诸理,实则求诸道,即所谓“治病必求其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如,五行之数为五,应象于五星、五官、五体,隐迹于五味、五臭、五季,理同于五脏(脏腑功能)、五志、五变;五与五之和为天干之数,运行称为五运,即五脏生理病理要受到“天地之理,胜复之作”(《素问·五运行大论》)所形成的生克制化的影响。
《素问·六节藏象论》首论数术,三分之二篇幅之后才及于藏象,盖象因于数,数术乃藏象之源,所谓脏腑功能实为数与象之结合。如肝属于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尚书·五行志》),故肝在数为八,应象于岁星、青色、草木,与春季、东方、酸味相感通。木气疏泄则“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素问·五常政大论》)。又如心属于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尚书·五行志》),故火在数为七,应象于荧惑、红色、谷黍,与夏季、南方、苦味相感通,火气炎热则“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同上)。这就是五脏生成之道(参看《素问·金匮真言论》)。不仅如此,中医以数识象,因象求理,以象类症,故认症识脉、诊断治疗的思考皆由此而发,所以说数术是藏象学说的核心,也是传统中医临证的思维方式之一。
5 摒弃数术对中医的影响
古人相信数字由“道”衍化而成,是道之显仁藏用的具体体现,医学体道载道,数术的渗透无所不在。在传统中医的理论里,数术与阴阳一样是理论框架的核心构件,它支撑着脏腑、经脉、气血理论以及临床治疗的多个方面,如果完全抽掉这些构件,中医的理论大厦将会轰然倒塌。
古人“循经守数,循按医事”(《素问·疏五过论》),按照数术的原理从事医疗活动。如明·徐凤的《金针赋》论刺法云:“一曰烧山火……凡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二曰透天凉……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三曰阳中隐阴……以九六之法……四曰阴中隐阳……以六九之方……五曰子午捣臼……针行上下,九入六出……六曰进气之诀……亦可龙虎交战,左转九而右转六。”摒弃数术会使中医失去千百年来的经验积累和行之有效的临床技能。
数术架构了一个以不同数字(或数理)为横向,以相同数字为纵向,上与天通,下联人体,旁及万类的认知体系,凭借这一体系能清楚地了解到世间万物因“数”之不同而分类,又因“数”之相同而相符合的普遍情况,因而数术是古人探索、获得知识的指南,行事的圭臬。如干宝《搜神记》云:“五月丙午日午时铸为阳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时铸为阴燧。”又如李时珍:“艾叶……皆以五月五日连茎刈取,暴干收叶。”(《本草纲目·草之三·芳草类》)都是对数术原理的应用。摒弃这一内容,也就部分抛弃了传统中医的认知方式,其中利弊学术界尚无定论。
数术架构是“象”思维的基础,古人依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如《抱朴子》云:“仙方有合离草(天麻)……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以仿十二辰也”,能除十二经之风痰而止痉。这种因数以比象、因象以明理的方法,尽管结果具有或然性,但辅之以生活的感受,物情的体察,再加以经验积累,亦能洞察物理,具有一定的确准性,医学就在这一模式中逐渐发展,在比较、试错、筛选、积累中寻求药物,发现方剂,探索疗法和认识疾病。如上所述,肝脏、草木、酸味、青色之“数”相同,根据同气相求的原理可以寻找青色、酸味的物质来治疗肝病,据此发现药物,总结疗效。而治疗心病的方剂可用红色、苦味的药物进行组合,可见,数术实乃格物致知之引导,由此引导的缘物求类的方法可以经推演、补充而永无止境,这无疑给中医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创造空间,明清温病学说的发展即是一有力的证明。因此,摒弃数术的中医将会失去传统的认知方式,失去自我发展、完善和创新的能力。
然而,现代中医完全删除了有关数术的记忆,数典忘祖,茫然于这一学术传统向我们昭示的存在意义:那是基于生存的原始动机,基于对世间万象的比类和参照,基于对自然的沟通、关怀、融入和契合,基于对日月、星辰、风雹、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的敬畏和崇拜,基于对土、石、草、木、禽、虫、鳞、介的熟知和了解,基于对众生怜悯油然生出的大悲恻隐之心!——这就是医道的本源。
因此,中医要走的路似不在于声光电气之现代化,不在于实验室中的复制、还原和实证,而在于回归自然,师法自然,倾听天籁,俯察万类,在天地间上下求索,去生活中涵咏体会,而医道之振兴或在于此!
[1]印会河主编,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1.
[2]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
[3]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2.
[4]卓廉士.感应、治神与针刺守神(J).中国针灸(J),2007,27(5):383-386.
[5]清·周学海.读书随笔[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61.
[6]卓廉士.从古代数术看经脉长度与营气流注[J].中国针灸,2008,28(8):591-595.
[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