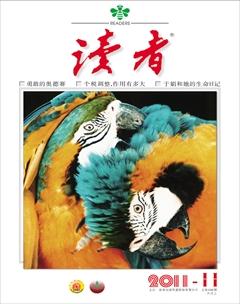瑞士人
龙应台
市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60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只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处,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指手画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经过,妇女买菜的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并热情地致意:“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用瑞士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沓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沓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里嘟噜说着流利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哪一种语言应对。我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用标准的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掌心中有几个钱币。渐渐地,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地丢进机器里,车票“咔”的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3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10月,距离3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4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做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说:“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竟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的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5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时10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人喝着各人的咖啡。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10点整,在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您居然等了15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15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说:“让我瞧瞧——对,明年7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7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姚远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看世纪末向你走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