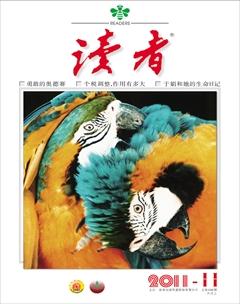朴实的水手
在船上,二十多天的水上旅程,沈从文和水手们有了特殊的感情。南方的雪阴柔,给人缠绵的思念。天寒地冻的季节,不管在什么地方,自然是孤独而又寂寞的。况且船上的沈从文,归家的心急切切的,早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毕竟离开多年,这是第一次回家。
雪落了很多,水上不能行船,船停到曾家河。这一夜沈从文睡得不好,被冻得多次醒来。清寒中他无法正常入睡,时常擦燃火柴,看小表上是几点钟。在不长的假期中,船窝住不动,时间在一点点地耗掉。在这多待一会儿,就意味着在家中少待一会儿。沈从文焦急之中,买了几斤鱼,和水手们沟通感情,“这几斤鱼把船弄活动了”。吃完鱼后,为了答谢客人的盛情,水手们不顾严寒的封锁启船。水上的潮湿气被冻得锋利,无孔不入。沈从文围坐在被子中,不能画速写,只能以膝当桌子,给妻子写信。船上没有火炉,没有煮一杯热茶的闲情逸致,只能选择在纸上写文字,把内心的情感和对天地的感受写出来,托付给邮路,让妻子理解他的心境。
从15岁离开家,在漂泊的生活中经受了太多的生死,沈从文对底层的人充满了爱。他从来没学会城市人的坏毛病,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歧视的眼光看人。在沈从文的眼中,水手也是人,人与人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他们也是个人,但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一看到这些人说话,一同这些人接近,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想好好地写他们一次。”水手是船上的灵魂,在沈从文的眼里,他们清澈透明,富于灵性,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地生活。水手们生于大地,长于大地,性格山野般朴实,敢恨敢爱。水手们的生活,水一般地随意。船一停下,水面缭绕的歌声悦耳动人,打消了他们一天的劳累。一只只船在暮色中聚集岸边,听得清竹篙在水中撞击石头的声音。河滩有了歌声,有了野骂,这些情景和声音的纠缠,使清冷的滩上充满了生气。沈从文被吸引住了,爱生长出来。他理解水手们的言行,在他们的打骂中,有着独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行船不是游山玩水的观光,水手们的生命系在水上,拴在船上。日复一日单调的劳作,磨去了他们皮肉的光泽,耗尽了他们的体力,榨干了他们生命的血脉。桨橹是手中的琴弓,他们在水的琴弦上,拉响苦难的乐声。水手们通过橹歌表达内心的向往,在真实的生活面前没有退路。摩罗说:“一个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深深伤害过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而不会成为作家,因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作弄和折磨造成的,一位伟大的作家几乎非得以心灵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残缺为代价不可。”沈从文在注视,在思考。他记住了水手的身影,一打一骂的“见面礼”。沈从文在写给三三的信中说:“你不要以为就是野人。他们骂野话,可不做野事。人正派得很!船上规矩严,忌讳多。在船上,客人夫妇间若撒了野,还得买肉酬神。水手们若想上岸撒野,也得在拢岸后。他们过的是节欲生活,真可以说是庄严得很!”
沈从文对“小人物”充满了关爱,这不是矫情的表演,这是从心灵中淌出来的。李扬在《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记录道:“1975年夏天的一件事让王亚蓉终生难忘。北京的夏天极其闷热,有一天王亚蓉高烧不退,因而也就没有到沈从文家里去。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无法临时通知。在午后的睡意蒙眬中,婆母正在问一个人,听口音很耳熟,好像是沈先生。她强支病体来到门外,‘真是他老人家,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是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从文見王亚蓉没有到自己这里来,以自己对这位姑娘的了解,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她不会不来的。沈从文买了些水果、鱼肝油等补品,顶着烈日来到了王亚蓉在海淀区的家。要知道,老人的这一趟横跨了北京的几个城区啊!从此,王亚蓉再也没有缺过勤。即使后来调到考古所,每天下班后,都要到老人的那间小屋,协助老人工作。”
黄永玉在怀念表叔的文章中说:有一个年轻人时常在晚上大模大样地来找他聊天。这不是那种想做思想工作的人,而只是觉得跟这时的沈从文谈话能得到凌驾其上的快乐。
他很放肆。他躺在床上两手垫着脑壳,双脚不脱鞋高搁在床架上。表叔呢,欠着上身坐在一把烂椅里对着他,两个人一下文物考古,一下改造思想,重复又重复,直至深夜。他走的时候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唉!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青年,十分愤恨,觉得好像应该教训他。表叔连忙摇手轻轻对我说:“他是来看我的,是真心来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
沈从文对小人物充满了同情,在他们的身上,他发现了人性的美丽。通过手中的笔,沈从文挖掘了对理想和未来的希望。一只船,一条河,一座山,构成了神圣的殿堂,沈从文倾心地雕塑水手们的形象。把水手们天真、质朴、健康的天性,塑造成一个个自然天成的生命。
水手们在沈从文的文字中不是提味的调料,给读者新鲜的刺激,而是灵魂的船帆,在文学的大河上,溯水行走。沈从文并不是在所谓的“审丑”中,剥出生活里丑陋的一面,放大渲染,而是以一颗慈悲的心,关爱着日夜在水上漂泊的水手们。他把在这条河上唱歌的人,比做是吃歌长大的。
(李力摘自新浪网高维生的博客,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