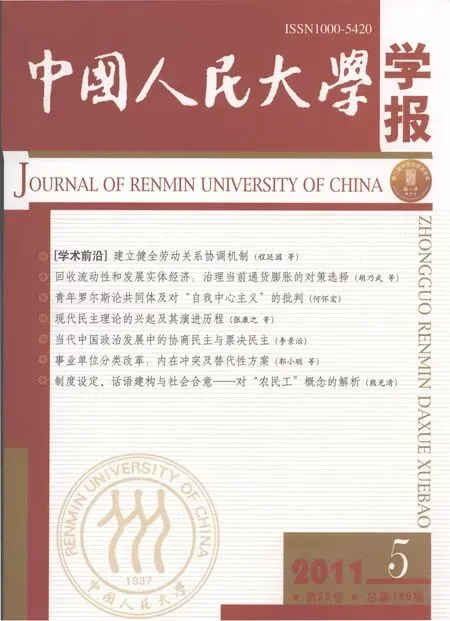青年罗尔斯论共同体及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
何怀宏
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编辑整理的、也许是罗尔斯著作系列中的最后一部专著:A B rief Inquiry into the M eaning of Sin and Faith:w ith“On M y Religion”。这本书的主要文本是罗尔斯的本科毕业论文《论罪与信的涵义》。他那时的思想自然还不是成熟的思想,是在他形成后来著称于世的理论贡献之前的思想。罗尔斯后来有一个巨大的思想转折,即他放弃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很难预测,如果罗尔斯后来仍然一直遵循他在这篇带有神学伦理学色彩的论文中的运思方向会取得怎样的成果,但恐怕很难超过他现在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然而,我们从这篇论文中已经不仅可以看到年轻人思想的锐气和爆发力,也可以看到思想天才的萌芽了,两位导师给这篇学士论文“98分”的高分是有道理的。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个天才的作品——不是说这部作品已经达到了天才炉火纯青的水准,而是说我们用心观察,已经可以发觉作者具有思想天才的潜质。而且,比较这篇论文和他后来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等巨著,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在思想理论上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成分。罗尔斯的这篇本科毕业论文虽不是一部成熟的理论巨制,却已表现出一个具有思想天才的作者的巨大潜能,表现出一种思想的青春锐气以及一种深沉而又超越的信仰关怀。这些在他后来的哲学著作中是不容易看到的。
笔者在这里仅试图分析和评论青年罗尔斯在这篇论文中所表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对共同体的重视与强调和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而前者尤其是由后者来彰显的。在罗尔斯看来,对共同体最大的危险还不是一种冷淡的、各自追求自己的欲望(常常是物欲)的“利己主义”(egoism),而是一种热烈的、似乎是追求理想的“大我”、但本质上却还是一种以一己之“小我”为中心的政治上的“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或者说是一种“伪共同体主义”。这种“伪共同体主义”似乎也强调共同体,但这是一种封闭的、自视优越的共同体,而不是开放和流动的共同体。它总是把一些人排除在外,看起来是排除少数,却终归要排除多数,即不断排除最有活力的、最可能对“自我”构成威胁的少数,最终也就排除了多数。这样,它实际上是用其自我构想的“大我”去实现“小我”、供奉“小我”,从而造成对共同体的最大伤害。
一、神圣和有机的共同体
青年罗尔斯在其本科毕业论文中认为,伦理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或者公共性的问题。伦理学应该研究共同体和人格的本质,人类主要的道德问题就是如何生活及与人相处。[1](P114)他批评“自然主义伦理学”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无法解释共同体和人格,从而丧失了世界的真正内涵。他还确信,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个人主义之后,时代的风尚将会指向“公共性”思想的复兴。[2](P108)但他后来并没有走向作为社群主义的共同体主义,或者说,他是强调政治上最广袤的社群,是强调国家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且是强调这一社会的基本结构。
罗尔斯对共同体的强调和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人即共存性。什么是人?他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共存性的存在,并因此而具有了人格。人区别于世间其他存在的不同之处不是他的理性能力、审美能力等,而是他生而为了共同体、并且是必然与共同体相连的一种人格。那时,罗尔斯还虔信传统的基督教的上帝,认为人类与上帝的相似之处就在于进入共同体的这种能力,因为作为三位一体之神的上帝,其自身就是一个共同体。基督教道德就是共同体中的道德,不管它是尘世的共同体还是天国的。总之,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者,因为他是一种共存性的存在。人类生来就是一种共存性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表明了人类绝不可能脱离共同体,他总是带有责任且一直背负着义务。所以,他批评逃避社会的伊壁鸠鲁学派、呼吁人回到森林中去的卢梭以及敦促人们进入一种宁静“空灵”状态的瑜伽哲学,呼吁在共同体之中来实现人的本质。[3](P121)
罗尔斯强调共同体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个性。他也同样拒斥那种寻求排除了一切特殊性的一致性并意图消除所有的差异性的神秘主义。他说,我们将会带着自己全部的人格和特殊性被复活,上帝的拯救是要彻底复原整个人,而不是要消除个体的特殊性。[4](P126)
罗尔斯甚至也以他那时所具有的有机和神圣的共同体的观点,反对后来在《正义论》中用作其思想理论主要资源的社会契约论,认为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也必须被拒斥。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一个人并没有为社会带来任何东西,在进入共同体之前他什么也不是。[5](P126)罗尔斯无疑认为具有共同体的人格是人的先定本质,这和是否订立契约无关,而且共同体不能建立在普遍利己主义或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在他看来,霍布斯和洛克政治理论中的正义观念,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自利是我们对待他人最好方式的思想,都是对共同体的误解。任何一个依据普遍利己主义解释自身的社会都会走向毁灭,而所有的社会契约论都遭受到这一根本性缺陷的影响。[6](P189)他后来在《正义论》中所设计的抽象的契约论,的确是指向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而非任何功利原则,但他也对过去对社会契约论的认识做出了调整,因为建立保障生命、自由、平等的传统社会契约论也不宜单纯从保障利益的角度去理解。
另外,罗尔斯在这篇论文中或许还给出了一个对笔者长期困惑的问题的解释,即他的《正义论》虽然继承和抽象地发展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传统,却仍然把霍布斯看做“特别的”而排除在外的原因。这原因或许就在于,在他看来,霍布斯是特别激进的个人主义。他说,霍布斯的基本预设带有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色彩,即认为社会是原子式的,是个人的集合体。人并不是天生就适合社会的动物,人本身并不具有社会性。人不是出于社会自身的缘故而寻求社会,而是为了免除恐惧和从中获取荣誉和利益而结成社会。正如威廉·坦普尔所言,恐惧是所有情感中最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另外,协议式的契约社会并不构成一种共同体,因为它是把社会看做一个互惠互利的体系,把社会仅仅当做手段来利用。[7](P229-231)
罗尔斯论文中“罪”与“信”这两个关键词的含义,也是通过共同体来得到界定的。他说:“罪应该被界定和解释为对共同体的破坏和排斥,信仰则被视为充分融入共同体、并与之紧密相连的某个人的内在状态。”[8](P113)。或者说,“罪就是否弃共同体”,“信就是构建共同体,包括上帝或者说上帝作为根源的共同体”。[9](P122-123)
在罗尔斯看来,既然罪就是对共同体的破坏、毁灭和否弃,那么,任何破坏共同体的活动都是一种有罪的活动。信仰在于以某个人格的全部精神品质充分融入共同体,因而能够深植于供养它的根源当中。信仰是人与人之间最完美的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将共同体连接起来的纽带。拥有信仰就意味着使自身奠基于共同体之上,这种共同体支撑着人格并且是精神才能的来源。[10](P123)正如罪是对共同体以至人格的疏离与毁坏,信仰则是融入并重建共同体。罪是结出恶果的封闭性,而信仰则是开放性,会开出共同生活的绚丽之花。那么,有罪之人如何转变成信徒呢?这就牵涉到救赎的问题。当我们问“人怎样能得到救赎”时,只是在问人怎样才能回归共同体,怎样才能赢得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以及可见的人类共同体如何才能作为部分进入天国的共同体。[11](P214-215)
如何建立一种理想的或者说神圣的共同体?或者说如何拯救或解放人类?近代以来出现了种种世俗的救世理论,其中有一些还期望建立人间的天堂。罗尔斯主要批判了立足于经济的、生物性的救世理论。他说,自洛克将订立社会契约的主要目的视作是保护私有财产以来,一种将社会的主要目的看做是经济目标的观点就经由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科布登而不断发展,到了马克思那里,经济更是被视作一切事物的基础。然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虽然清楚地看到了剥削在社会体系中的猖獗,杜威也敏锐地发现了智识合作和知识产业的匮乏,但它们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即建立共同体的问题。[12](P217-218)罗尔斯并没有仔细区分这一重视经济观念中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他所注意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共性,即都将经济提到首位。而他认为,这些观念都还是肤浅的,因为“关于拯救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共有性和人格性的问题,因此,究其核心,拯救是一种精神性的过程”。[13](P214)
另一种肤浅的近代观念是生物学的观点,即认为人从生物学上讲是一种动物,而救赎就是要使人更具动物性。罗尔斯认为,宣扬“适者生存”的科学理论给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优生计划”更是其中最肤浅的一种。纳粹主义就是德国人糅合“自我中心主义”、绝望的思想与情感的蒙昧主义以及优生学的产物。
有意思的是,罗尔斯认为,纳粹主义相比于其他许多肤浅的现代救世论,倒的确是一种关于人的深刻理论,它在对人性的理解上“远远超出了经济人理论和生物人理论”。因为“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明白,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纯粹的生意人”,因而提出了“人是英雄式的,是圣人、得胜者、勇士和斗士”。“它认识到人是有灵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纯粹嗜欲性的动物。”这个事实解释了纳粹运动展现出巨大能量的原因。然而,罗尔斯强调,纳粹主义虽然是深刻的,但它之深刻乃是从魔鬼是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它的诉求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它意识到了人的灵性,但它只是看到将招致共同体毁灭的自我中心主义之灵。[14](P218)
二、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
笔者之所以聚焦于罗尔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因为这一批判最能彰显罗尔斯早年共同体理论的特色,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罗尔斯认为,损害以致毁灭共同体的主要的罪还不是利己主义,而是自我中心主义。①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立己主义”,对这种“立己主义”的界定与分析可参见拙作:《面对死亡的立己主义》,载《道德·上帝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中国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载《生生大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罗尔斯在这方面自认借助了英国哲学家菲利普·利昂的思想资源。利昂在《权力伦理学》中已经仔细区分了他所称的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其中利己主义的含义同罗尔斯所称的“自然关系”中的欲望的含义近似。对利昂来说,利己主义指的是为了某个特定对象或者事态所做的生物学方面的努力;自我中心主义则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如渴望权位、追求名望和无上权力等。自我中心主义不仅对物欲漠不关心,甚至还常常极力地反对它。自我中心主义者追求这些事物也往往只是作为他优势地位的象征,是为了满足他的优越感。这样,利昂关于自我中心主义的定义,就接近于罗尔斯所说的“人格关系”中的骄傲了。罗尔斯指出,利昂非常正确地看到,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乃至放弃生命来维护和保存他的至上权威,这时,“野心凌驾于欲望的暴政就会是最为极端和最为明显的”。另外,罗尔斯也同意利昂所宣称的并不是欲望引起了自我中心主义。“欲望本身并没有导致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但是,欲望能够限定、有时甚至是决定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定表达方式,因为有时它就是这些表达方式的工具。[15](P150-151)
正如上述,罗尔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利昂的论述稍有不同,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发展。他对利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区分是承续自然关系与人格关系的区分而来,认为人在自然关系中对具体对象或客体关系的欲望是利己主义的,而人格关系则被自我中心主义或者友情和爱所驱动。[16](P118)罗尔斯特别强调自我中心主义是对共同体的主要犯罪。自我中心主义是主要的罪,构成恶的根基,其他所有次要的恶都来源于它。“罪就是对共同体的破坏”,罪有两种类型:一是自我中心主义,一是利己主义。但两者相比,自我中心主义的行动在本质上就是对共同体的破坏。他为了达到目的将会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使用正大光明的手段还是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利己主义如果限制在自然欲望之内,本身其实并不是一种罪,只有逾越这个界限才是一种罪,它往往是被自我中心主义所蛊惑而逾越这一界限的。换言之,如果人的自然欲望将人格性和公共性的关系转变为自然关系,它就变成了一种罪。[17](P122-123)
罗尔斯分析并指出了自我中心主义的五个特征:(a)自我中心主义拒绝与人分享。自我中心主义者想把一切据为己有,这样做不是因为他需要一切,也不是因为他的欲望要求他这么自私,而是因为他把独占一切看做是自身优越性的标志。(b)自我中心主义力图发展封闭性群体,而理想的封闭性群体就是一个人自己的自我,因此自我中心主义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不惜损害共同体。(c)自我中心主义无法容忍自我批评,因而总是设法怪罪于他人。(d)自我中心主义具有一种不寻常的、狡猾的隐秘性,它使得灵魂败坏了自身中最好的部分。(e)归根结底,自我中心主义仍是某种反叛与否定,尽管它采取的策略往往是秘而不宣且谨小慎微的。[18](P203)
罗尔斯说他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分析远说不上完备,就像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的,“人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的能力尚不足以使我们探测这深渊的深度。但这五个特征还是为弄清罪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提供了一条线索。共同体遭到破坏并非缘于具体的欲求或利己主义的满足,而是缘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满足。简言之,共同体是为全然扭曲的自爱所毁。自我中心主义者只爱自己,彻底围绕自身打转并沉浸于洋洋自得的自我崇拜,其他人要么变成纯粹的手段,要么变成他的崇拜和仰慕者。[19](P203)罗尔斯的分析给出了一个20世纪极权主义的统治者的传神画像。
由于权力是占有其他一切东西的前提,所以这里的不肯分享或者说独占,最重要的自然是对权力的独占了。而最核心或最小的封闭也就是一己之自我,故而最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政治上的独裁者或者说“独夫”了。自我中心主义者是缺乏反省精神和自我批评意识的,因为,他对权力和荣誉等资源垄断到这一极端地步,一旦自我批评就可能是崩溃的开始。然而,他虽然瞧不起所有其他人,但对战略策略又是极其重视的,是极其狡猾和相当大胆的,这样,他就往往能胜过对手,取得莫大的世俗成功,达到权力的巅峰。但是,由于其精神根本上是否定性的,所以他不仅会损毁共同体,而且自己也将变成孤家寡人,站在最高的权力和荣光之上,但也陷入最大的孤独之中,乃至最后毁灭自己。
三、自我中心主义与利己主义之比较
我们可以从罗尔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我中心主义比利己主义更危险、更不道德。虽然它常常有比利己主义更辉煌的形式,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和“魅力”,而且这种大罪往往是由才华出众者、“卓越者”犯下的。这里的一个鲜明对照仍然是自然欲望与骄傲野心、利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对比。罗尔斯认为,在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两种罪的形式中,一切重大之罪都归为第一类,自我中心主义者是“卓越”的犯罪者。“最危险的自我中心主义将出现在我们所获得的最高成就中,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佼佼者身上。”[20](P201)因为,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指的就是异常地追逐至高无上并罪恶地渴求自我崇拜。利己主义者只是利用他者,即“你”,而自我中心主义者则凌辱“你”,想要把“你”置于他之下,并使“你”转变成他的崇拜者。[21](P193-194)自我中心主义者看来是属于少数人的,多数人会追求物质和经济利益,却不一定会费力追求野心和荣耀。而在自我中心主义的内部,也有隐秘的与显明的之别,有主要寻求自我或同行的小圈子的崇拜和寻求几乎所有人的崇拜或至少畏惧之别,有有所节制的和毫无节制的之别,后者尤其危害共同体。
这里特别需要警惕和防范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以所谓“大我”为掩护甚至为旗帜来实现“小我”的权力、荣耀或者“理想”的自我中心主义。最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有时可以以最极端的共同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如果能在“大我”或整个社会的层面实现一己之“小我”的“理想”,自然是最大的成功和自我实现。这种“理想”往往是政治社会的理想,所以说,最需防范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因为它能够最有力和最广泛地影响社会和人际关系。罗尔斯写道:“我们不会把一个具有强烈的欲望的人称为罪人。当一个人无比饥渴时,他并不是在犯罪。我们不会对艺术家或形而上学家冠以这样的名号,也不会把一个无法欣赏美的人或一个弱智的人叫做罪人。我们几乎在直觉的意义上使用‘罪’这个词专指恣意滥用或破坏人格关系的堕落行径。”[22](P186)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共同体来立己。罗尔斯说:“利用共同体来追逐自我利益是罪的一种主要形式。”[23](P189)
罗尔斯对满足自然欲望的、活动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利己主义其实表现得相当宽容,虽然他也承认从这些欲望中并不能自行产生出友爱,不能将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这种自然欲望之上,但他认为自然欲望并不会引发使共同体分裂的自我中心主义。自然欲望毋宁说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支持或反对共同体自身的因素,也不具有任何反社会的因素,同样也不具有任何亲社会的因素。[24](P186)罗尔斯甚至认为身体或者说身体的自然欲望反而有可能限制自我中心主义的大罪。他说,身体也是对罪的某种限制。正是因为身体的存在,才使得人类之罪免于沦为纯粹的邪恶。“如果人不是一个受制于饥饿和饥荒的受造物,他还会回头吗?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假设他具有魔鬼那样的力量,能够免于这种极端生物性的制约,他还会悔过吗?……因此,身体远不是罪的诱因,在无数情形当中,正是我们身体的因素击败了我们的自大,使我们更加清楚我们的罪过,并引导我们去悔过。这样,自然宇宙就得到了辩护。”[25](P156)罗尔斯告诉我们,比起物欲流行来更可怕的是一种心灵之罪。这种心灵大罪往往是少数具有某些潜能的人才会犯下的,而多数人出于身体的自然欲望反而有可能限制这种心灵大罪,从而有可能使之不致酿成毁灭共同体乃至人类的大祸。也就是说,多数人通过对自然欲望的合理诉求,或者对强行禁欲的抵制和冷淡,反而遏制了掌握权力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任意妄为。
罗尔斯批评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追求生命意志的利己主义的观点。他说,叔本华的错误就在于他未能意识到,动物层次上的生命意志,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更高层次的生命意志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叔本华没有认识到自我中心主义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是对荣誉和荣耀的渴求,为了它们有人甚至会乐意放弃生命。[26](P146-147)
自我中心主义之罪将导致怎样的后果?罗尔斯认为,如果说人是生存于共同体并为之而存在的受造物,如果罪就是对共同体的破坏,那么罪的后果就是孤独。孤独是人类可能陷入的最可怕、最痛苦不堪的状态。[27](P206)罗尔斯通过对尼采权力意志论的批判描述了自我中心主义膨胀最后的结局:“强力发疯似地自我旋转,灵魂在自造的孤独中疯狂地耗尽自身精力。这就是罪的结果,也即本真意义上的罪。这样一种灵魂状态拉开了死亡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序幕。结局已然可见,冲撞渊底之后的毁灭正迅速袭来。孤独以死亡而告终。”[28](P213)
罗尔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一个深厚的背景是他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观察和思考。他对政治上狂妄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描述,相当接近于像墨索里尼、希特勒这样善于蛊惑人心的“元首”形象。他还谈到自我中心主义拒绝分享、共享的另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封闭性群体的产生。在大学社团、男性俱乐部、竞技组织、民族群体与种族群体中,我们都能发现那种在一个“优越的群体”中获得自我中心主义的满足感。罗尔斯指出西方文明封闭性群体发展的几个阶段是:(a)宗教领域的封闭性群体,如罗马教会把除它以外的所有人称为异教徒;(b)文化领域的封闭性群体,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团体;(c)经济领域的封闭性群体,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一个人所归属的群体由他的经济地位所决定;(d)最后,生理因素成为封闭性群体的决定因素,其当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血统论的纳粹思想。[29](P197)这最后一种群体的封闭性具有铜墙铁壁般的特征,故其成员的自我中心主义就比容易流动的群体更为全面彻底。罗尔斯批评了纳粹官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精致的唯我论神学,认为在其著作中封闭性群体作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工具这一点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总之,无论这个封闭的群体是“优秀种族”还是“先进阶级”,甚至是相当广泛但却含义模糊的“人民”,它们总是要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而罗尔斯在其后看到了一种“领袖”或者“元首”的自我中心主义。
罗尔斯的这些思考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及根源的一个深刻反省。这种极权主义初看起来是大众主义的、民众主义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独裁主义、专断主义,一种最终导向孤独和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有可能构成对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共同体的最大危险和伤害的不是一般人的自然欲望的利己主义,也不是一般观念者的“立己主义”,而正是这种政治行动者的立己主义,亦即一种走向极权政治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物质利益乃至生命,而且很可能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对人类、大我的理想混合在一起,但他无论如何还是以自我及其理论观念为中心的,为此将不惜把人们投入血泊。这种政治上的立己主义者是一定要利用他人的,而且经常是利用多数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由于他和所有其他人处在一种极度不平等的关系之中,由于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惮采用暴力和欺骗等不正当的手段,所以他并不能建立一种真正和谐的共同体,而只是毁坏共同体。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Thomas Nagel(ed.).A B rief Inquiry into the M eaning of Sin and Faith:w ith“On M y Relig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